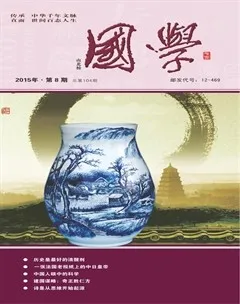江南味道依舊如初
諸榮會(huì)
“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印象中的江南,是杜牧筆下的小橋明月,柳永詞中的煙柳繁華,絲管悠揚(yáng)處的歌喉婉轉(zhuǎn),小庭深院里的幾盞清茶……杏花煙雨,粉墻黛瓦,這些江南獨(dú)有的韻味,令人心馳神往。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zhǎng),雜花生樹,群鶯亂飛。”那時(shí)的江南,每一個(gè)角落都彌漫著花的芬芳和草的清香。“江南路,云水鋪,出門進(jìn)門一把櫓。”那樣的江南,四季的清風(fēng)中都裹挾著雨的清涼和水的腥臊;還有那粉墻黛瓦的素淡,吳儂軟語(yǔ)的甜糯,春茗佳釀的醇香……
這一切正是江南的味道——不但浸透在陽(yáng)光中,飄蕩在晨風(fēng)中,彌漫在暮雨中,而且還婉轉(zhuǎn)于梁祝化蝶的優(yōu)美旋律中,氤氳于湖筆宣紙制造的淋漓水墨中,縈繞于每一個(gè)中國(guó)人都必定會(huì)做的江南夢(mèng)境中。
江南的味道遠(yuǎn)不止這些!那一座座石拱橋,馱走了江南多少風(fēng)雨?那一條條小河,流去了江南多少歲月?江南的味道中,也沉淀著風(fēng)雨的凄楚、汗水的苦澀和歲月的艱辛。
我很小的時(shí)候就知道自己的故鄉(xiāng)在江之南岸,也在很小的時(shí)候便在“樣板戲”中學(xué)會(huì)了一個(gè)形容江南美好的詞——“錦繡江南”。只是那時(shí)我除了在作文中常用這個(gè)詞大唱那些只不過是人云亦云的贊歌外,說句實(shí)話,生活中反而常常想:連吃飯都常常成問題,自己天天生活的這塊土地又如何能算得上是“錦繡”呢?有人告訴我,這是因?yàn)槲业墓枢l(xiāng)并非正宗的江南,正宗的江南并不是這樣。于是從那時(shí)起,我的心中便有了另一個(gè)江南——既在心中,又在遠(yuǎn)方。
從此,我之于江南,如同一個(gè)癡情少年,終日遙望著自己思慕已久的人兒,卻又不能與之相交相知,而她對(duì)我只是“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那杏花、春雨、油紙傘,那粉墻、黛瓦、石拱橋,仿佛走在大街上突然映入眼簾的是一個(gè)曲線優(yōu)美的朦朧背影,令人心旌搖曳而又茫然悵然……
我自稱是半個(gè)江南人。與此同時(shí),我也越來越熱衷“江南游”,尤其是近年來,我?guī)缀踝弑榱苏麄€(gè)江南。要說究竟走過了多少小橋流水人家和稻花香里阡陌,走過了多少個(gè)杏花春雨的清晨和落霞孤鶩的黃昏,還真是說不清楚。說得清楚的是,我因此而寫下了幾本有關(guān)江南的小作。
寫下的這些有關(guān)江南的文字,我只希望它能為故鄉(xiāng)和江南留下一份昨天的記憶、今天的印痕和明天的期待,只因?yàn)樯钪形页3B牭竭@樣的話:江南文化已經(jīng)被毀了,江南味道已經(jīng)變了。
是的,今天的江南,“小橋流水人家”變成了林立的高樓大廈,“古道西風(fēng)瘦馬”變成了高速公路上車流如水如電,夢(mèng)里水鄉(xiāng)變成了人頭攢動(dòng)的旅游勝地……這樣的江南還是江南嗎?這樣的江南還有江南的味道嗎?這樣的疑問聽得多了,我便想用自己的文字告訴人們,江南的這一切都不是憑空產(chǎn)生的。那一座座高樓大廈,實(shí)際上都只是那粉墻黛瓦馬頭墻長(zhǎng)高了而已;那一條條高速公路上風(fēng)馳電掣的車流,只不過是那曾搖晃著夢(mèng)想的烏篷船搖快了而已;還有那今天所有用多媒體包裝過的繁華、熱鬧和喧囂,只不過是昨天那小巷深處討價(jià)還價(jià)的市井聲放大了而已……
其實(shí),江南改變的只是她的外形,而她的味道一點(diǎn)兒也沒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