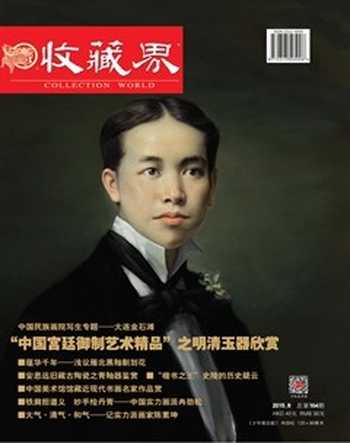蘊華千年
李君



兩宋以及遼金時期是中國瓷器發展歷史上的頂峰,山西作為中國華夏文明的主要發祥地之一,成為我國北方重點產瓷區,其中雁門關以北的廣大地區所生產的黑釉剔劃花作品,又是中國西北地區最具特色的瓷器作品(圖1)。
所謂的雁北黑釉剔劃花,就是先將瓷土用手工轉輪拉坯成型后,再施含有高鐵質的黑釉,最后用工具刻劃紋飾,有些紋飾還要剔去背景并一次燒成。因此具有雄健厚重、酣暢淋漓、黑白分明的風格(圖2)。
雁門關以北,在兩宋期間曾經長時間被遼所控制,后來又為金所有。盡管遼金統治期間,這一帶戰爭頻繁,但是在民間,由于文化紐帶和血緣的關系,其商品交換、工藝交流卻從來沒有間斷。因此,遼金時期雁北的制瓷技術與其相鄰的河南、河北各窯口的關系十分密切。甚至在近、現代較長一段時間的鑒賞中,曾一度把這些作品歸入到磁州窯之中。但是,隨著科學的考古工作不斷地深入和發展,這種頗具雁北特色的黑釉剔劃花作品,由于個性突出,風格鮮明,最終呈現出與眾不同的韻味來。
事實上,雁北地區生產瓷器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以前。其胎土基本上和北方各大窯口一樣,都是一種被稱為大青土的瓷土,只是胎土顆粒通常被淘練得比較粗一些。器物黑色的釉面也和北方各窯作品大略相似:大部分像鏡子一樣的光潤細膩,其中也有一部分釉面較粗,顏色發褐不亮。一直到了遼金統治時期,雁北黑釉剔劃花的風格和北方各窯作品出現了較大不同:雁北地處三晉北方的苦寒之地,由于宋遼金之間戰爭不斷,因此民風強悍、樸實,然而這一地區的歷史沉淀卻又十分深厚。雁北作品,不像一般北方的剔花作品那樣,是在白色化妝土上先畫黑色的紋飾,再在黑色的紋飾上剔刻(圖3)。雁北的作品索性是整個先上黑釉,晾干后就直接刻劃上強勁準確的線條,有些再把紋飾的背景底子剔去,露出黃白的胎,最后進爐一口氣燒成。少數一些特別精細的作品,還要在黃白胎體上涂一層稍白的化妝土,增強了紋飾的浮雕感(圖4)。此階段雁北的黑釉剔劃花作品造型常見有碗、盤、吐魯瓶、玉壺春瓶、大罐、帶系罐等。體形高大的器物一般有兩層或三層裝飾帶,紋飾題材有各式花卉、花鳥、嬰戲、人物、魚紋、兔紋等。紋飾之間還常常用弦紋或者反“S”曲帶紋相間隔,其中最常見的是纏枝花卉和折枝花紋飾。這些圖案一般都是裝飾在立件器物的肩腹部,其花卉往往是被刻劃得葉肥瓣厚、充滿生機。同時,作品使用的線條細勁簡潔、堅定酣暢,使得這一類作品呈現出一種特別大氣的磅薄氣勢(圖5、6、7、8)。
遼金統治階段作為雁北黑釉剔劃花的鼎盛時期,生產的有渾源、大同、懷仁等窯口,其中又以渾源所作的黑釉剔劃花最為精美。1955年山西天鎮夏家溝出土的金代黑釉剔劃花瓶(圖9)和英國大英博物館收藏的“大德八年”銘吐魯瓶(圖10)等等,就是這一類作品。
筆者曾應邀去德國收藏家艾克夫人的寓所,在她滿架珍罕的中國古代藝術品中,一只典型的雁北黑釉剔劃花玉壺春瓶(圖11),引起了筆者的注意。但見此瓶釉面烏黑光潤,頸部纖細挺拔,腹部卻豐滿圓潤,造型婀娜多姿。瓶通高約29厘米;底足內外滿釉,足端左右斜削;淘練得比較細的胎土呈淺黃色、手感輕巧。剔刻在瓶體肩腹部的紋飾疏密有致,線條生動流暢而且毫不含糊:先用雙弦紋把肩腹部分成兩個區域,并且用勁挺有力的細線在上下兩個區域中分別刻劃出纏枝紋輪廓,再把纏枝紋的背景底子剔去,露出胎體,最后在露胎處加上適度的白色化妝土后入窯燒制而成。在瓶體圖案中,盈細剛勁的線條和肥大厚拙的花葉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同時整個瓶體黑白對比醒目,具有厚重的浮雕立體感。這種藝術處理大大增加了玉壺春瓶的豐滿生動之美,也使此瓶整體給人呈現出婀娜而簡潔、明快而渾厚的觀感。這種效果正是雁北黑釉剔劃花所具有的清新厚健的特點,它較之其他瓷器品種,更具備了獨特的審美情趣,因此受到了眾多資深收藏家的喜愛,特別是歐美、日本等大藏家往往對此情有獨鐘。他們常常會在各類大拍上不惜一擲千金,就是為了奪得這種心頭之好。
有著濃郁特色的雁北黑釉剔劃花作品,經過千年沉積,無論是在藝術成就上還是工藝技術上,都充分反映了兩宋遼金時期中華民族的文化高度,也為那個時期陶瓷生產中風格的多樣性研究,提供了十分有價值的資料(圖12)。應該說雁北黑釉剔劃花作品,是中華民族陶瓷大家庭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奇葩。她那獨特的審美風格,為中國的陶瓷藝術史增添了極其光輝的一頁。其間蘊涵的深邃歷史、文化和人文精神,是十分值得今天的我們去品味。(責編:雨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