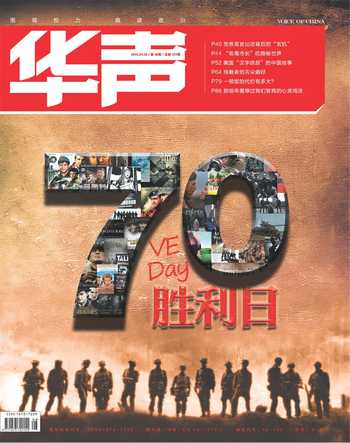會有“奧巴馬主義”嗎
曉岸
奧巴馬拒絕在“保守的現實主義”和“激進的干涉主義”之間作選擇,但他無法超越霸權思維定式,必須與美國延續200多年的傳統和慣性達成妥協。
每一任美國總統都希望青史留名,他們默許人們給自己在世界上的所作所為貼上“主義”的標簽,夢想成為某個時代的締造者。這種“主義”往小了說是發動海外戰爭的指導方針,往大了說是對外戰略的階段性特征。
多數美國總統提出了具有歷史性影響的“主義”,各種“主義”串接起來,代表了美國影響力興衰成敗的歷程,拼出了美國在世界上行為方式的意識形態全圖。
再過兩年,奧巴馬總統的任期就將劃上句號,他的“主義”又是什么呢?
奧巴馬被擾亂的“主義”布局
2009年1月20日,奧巴馬在歡呼聲中出任美國總統。他的就職演說宣告了與“布什主義”分道揚鑣的決心,表示要充分運用“智慧的力量”樹立“謙遜和克制的典范”。執政頭兩年,奧巴馬確有建樹,在力推國內醫保和金融監管改革取得進展的同時,從伊拉克撤出戰斗部隊,制訂從阿富汗撤軍時間表,與俄羅斯簽署新版《削減和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同中國把酒言歡,為重啟以巴和談不惜對盟友猶太人過度施壓,還向伊朗伸出了橄欖枝。
2010年5月,奧巴馬政府發布任內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明確提出尋求“安全”、“繁榮”、“價值”、“國際秩序”四項“持久的國家利益”。但這份報告主要還是對“布什主義”的修正和揚棄,包括棄用“反恐戰爭”表述、將美國反恐戰略的重心由全球回縮至本土、更多強調國際合作、指出需要對中國等新興大國崛起“做好準備”等等。報告并未完全摒棄單邊主義和“先發制人”,而是強調在使用武力前要窮盡其他選擇,動武須遵守國際標準。
時間還未出2010年,現實的骨感就開始沖擊奧巴馬的外交理念。這一年11月,民主黨在中期選舉中失去國會眾議院控制權,奧巴馬施政空間嚴重收縮,所受質疑猛增——共和黨指責奧巴馬對外政策不切實際,朝野擔心太多的妥協將削弱美國的領導地位。更重要的是,國際形勢的變化將過于復雜的線條注入美國的全球戰略運籌,讓奧巴馬希望堅守的路線在實際操作中變得支離破碎、自相矛盾。
首先擊碎的是奧巴馬的“和平總統”夢。
2011年3月,利比亞內亂升級,北約發動“奧德賽黎明”軍事行動,以保護平民安全、保障人道救援為名行顛覆卡扎菲政權之實。美國參與了行動,卻沒有沖在前頭。3月28日,奧巴馬發表電視講話,就這場軍事行動的目的和美國緣何把指揮權交給北約作出解釋,堅稱美國“沒有采取單邊行動”,指出美國介入海外沖突的最低標準是“美國國家安全并沒有受到直接威脅,但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受到了威脅”。
西方主流媒體和戰略學界由此掀起對“奧巴馬主義”的最初討論,紛紛把講話解讀為“奧巴馬主義”形成的標志,認為奧巴馬“在發生沖突的國家或地區奉行實用主義的、有選擇的干涉政策”,試圖在美國的核心利益和非核心利益之間劃出明確界線,對涉及前者的威脅采取單邊行動,對只涉及后者的挑戰負責指揮多邊行動。
接著嘲諷的是奧巴馬維護“美國第一”的誓言。
奧巴馬迄已發表六次國情咨文,每次都要提及“美國的領導力”,一再強調“美國沒有理由被其他國家趕超”,“問題并不是我們是否還能領導世界,而是我們如何領導”。這固然是冷戰后美國一以貫之的“使命”意識、霸權意志的延續,卻無法回避美國領導力賴以存在的實力基礎正發生歷史性變化的事實。美國已在奧巴馬任內連續將制造業規模、進出口貿易總額、吸引外資數量、按平價購買力計算GDP規模等世界頭把交椅讓給中國,經濟總量被追平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而歷史上任何一個大國的盛極而衰都是以一個接一個摘掉頭上的“世界第一”桂冠為序曲的。
同時挑戰的是奧巴馬政府重新布置全球戰略重點的意圖。
奧巴馬對外戰略的主打牌是“全球再平衡”,也即重新配置美國的戰略資源,形成反恐與應對新興大國崛起并重的態勢,加速全球戰略重心從歐洲、中東一線向太平洋地區轉移的進程。然而,兩場危機的生成和兩線矛盾的演化分散了奧巴馬政府的精力,使其如意算盤很難一打到底。兩場危機分別是“伊斯蘭國”興起和烏克蘭問題激化,兩線矛盾則是西方世界與伊斯蘭世界的文明沖突和美國與前蘇聯繼承者俄羅斯的戰略緊張。
亞太是奧巴馬政府對外政策最能體現進取性的方向。 “重返亞洲”、“亞太再平衡”成為奧巴馬政府最可炫耀的資本和最承期待的“遺產”,但這些“收益”以損耗中美互信為“成本”,使中美關系這一亞太戰略環境的中心關系發生冷戰后少有的波折。盡管奧巴馬政府保持著維護中美關系穩定發展的基本態度,但無法收斂、掩蓋防范中國的布局意識。
2012年9月12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白宮就美國駐利比亞大使遇襲身亡事件發表譴責聲明后,與時任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一道轉身離去。
或成泡影的“奧巴馬主義”
如果確有“奧巴馬主義”,它將是多線索的。奧巴馬修正了布什政府對全球反恐的過度強調,實施了自伊拉克、阿富汗分階段撤軍計劃,終結了美國深陷海外兩場戰爭的危機,這應是“奧巴馬主義”的中心內容。奧巴馬團隊推崇“巧實力”和“聰明外交”,抵制美國在世界上過度擴張的危險,更多依靠盟友和合作的力量促進美國戰略目標,只作“世界警長”不當“世界警察”,志在重塑美國的全球領導力,這符合財政緊張、影響衰減時期的“行動主義”,是“奧巴馬主義”的處事準則。奧巴馬調校全球戰略焦點,在打壓俄的同時把對華關系提升到更重要位置,這是“奧巴馬主義”在地緣政治層面的“積極作為”。
但以上線索的實施效果無論如何都談不上卓著,相反正陷入混亂,被美國國內越來越多的人批為“不作為”、“不愛國”、“逃避責任”、“模棱兩可”、“缺乏一致性”。更有言論指奧巴馬的外交路線實為一種“應付戰略”,沒有為美國在全世界的目標提出積極的設想,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美國面臨的安全挑戰,因而也就沒有什么“奧巴馬主義”。
奧巴馬的任期剩余無多,恐已來不及完善其“主義”,更注定不能在任內獨樹一幟如愿締造“新美國夢”,但他仍可抓緊時間推動經濟復蘇——這是反駁“美國衰落論”的最有力武器,推出新的外交政績——比如與古巴、伊朗和解,并利用各種機會進行自辯。
2015年2月,奧巴馬政府發布任內第二份《國家安全戰略》,奧巴馬在序言中強調了美國保持“戰略耐心”、外交“不做蠢事”的必要性。這份報告將美國面臨的主要安全威脅歸納為暴力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氣候變化及其災害、網絡攻擊和日益增大的流行性疾病,指出使用軍力不是美國介入海外事務的主要手段,也不總產生最好效果,發揮主要作用的仍然是外交。
奧巴馬拒絕在“保守的現實主義”和“激進的干涉主義”之間作選擇,但他無法超越霸權思維定式,必須與美國延續200多年的傳統和慣性達成妥協。
需要從美國大戰略的角度理解奧巴馬的歷史地位。我們對美國政治的了解還談不上深入。如果確像某些傳聞所說那樣存在民主黨大佬對克林頓家族重掌政權的長線安排,曾作為國務卿與奧巴馬通力合作推展“聰明外交”和“重返亞洲”的希拉里·克林頓能夠入主白宮,那么美國“大戰略”從一個“克林頓主義”邁向另一個“克林頓主義”的色譜就會變得明朗,而所謂“奧巴馬主義”不論虛實有無,都是已隱約可見的“新克林頓主義”的先期準備。
摘編自2015年第6期《世界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