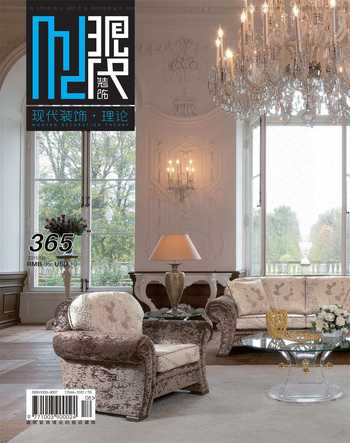探析中國傳統園林中的“空靈”思想
王小同 覃慶貴
本文從中國傳統美學思想中的“空靈”思想出發,分析“空靈”與禪的聯系,進而概括總結出中國傳統園林設計手法中所體現的“空靈”思想以及營造“空靈”的手法,希望對中國現代審美和設計作品的創作起到啟示作用。
現在說的“空靈”蘊涵的是禪宗的“悟”的文化內涵,禪宗所講的“悟”或“妙悟”實質上是對宇宙本體的體驗、領悟。在大自然的景象中,去領悟那永恒的空寂的本體,形成一種令人喜悅的領悟和體驗,這就是空靈。“空”是空寂的本體,“靈”是活躍的生命。宗白華說:禪是動中的極靜,也是靜中的極動,寂而常照,動靜不二,直探生命的本源。禪宗就是要人們從宇宙的生機去悟那本體的靜,從現實世界的“有”去悟那本體的“空”,也就是在現實生活中體會、零領略和感悟,又超脫于現實,形成一種詩意,進而達到“空靈”的境地。
空靈是藝術精神的兩元之一。美感的養成在于能成空,對物象造成距離,然后孤立絕緣、自成境界。就拿古人詩句中描繪的場景如黑夜籠罩下的燈火街市、明月下的幽淡小景、雨后煙霧迷離的景致,這種邊界迷糊的間隔和距離產生的情景都是耐人尋味的,都是美的,是富有詩意的,是動人的。古代文人書畫家董其昌曾說:攤燭下作畫,正如隔簾看月,隔水看花。由此可以看出“隔”在中國古代審美中的重要性,這是形成美感的重要條件。中國傳統園林在造園中大量使用“借景”、“分景”、“隔景”、“框景”等藝術手法,豐富了園林的空間美感。頤和園在造景時把園外的風景也“借”進來,無形中擴大了頤和園的范圍,如從魚藻軒向西可以眺望到玉泉山的塔和香山。窗子在園林建筑藝術中起著很重要的作用。有了窗子內外就發生交流。透過窗戶望去,窗外的景物就被“框”在一個框里,形成了一幅幅優美的、形態各異的自然風景畫,人由此獲得了美的視覺享受。這就是所謂的“框景”手法,這是中國古人造園時無處不在的設計手法。頤和園的長廊將其南側的昆明湖和北側的排云殿、佛香閣等建筑分隔開來,從美學角度分析是把自然景色和人工亭臺樓閣相分離,無形中產生對比,起到“分景”作用。中國傳統園林中的空靈還體現在對虛實的處理上,對虛實的處理在中國傳統繪畫、戲劇和書法中都有體現,舞蹈的動作和場景都彰顯著虛靈的空間。這一點從臺灣著名編舞家林懷民編排的舞蹈中可以看出來,在空虛幽暗的背景的襯托下,演員的舞動的姿態映入眼簾,讓人物充分的表現劇情,正所謂“實景清而空景現”。正如宗白華所說,藝術家創造的形象是“實”,引起我們想象的是“虛”,由形象產生的意象境界就是虛實的結合。中國古代“虛實相生”的哲學思想也要求藝術創作要虛實結合,方可描繪有生命的萬物。中國傳統園林在造園時就是把實景和虛景結合起來,營造出豐富的空間效果。拙政園中的實景與遠處借來的虛景、院中水中的倒影相結合,建筑堅硬結實的棱角與被樹木“軟化”了的建筑部分無形中形成一種虛實對比,這種虛實結合的手法在園林中應用還有很多,處處體現著造園者的智慧。
當然,這只是依靠外界物質條件造成的“隔”,更重要的是心靈內部的“空”。精神的淡泊是藝術空靈化的基本條件。陶淵明的《飲酒》一詩中“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體現的胸襟和氣魄是十分難能可貴的,“心遠地自偏”到“悠然見南山”,再到“欲辨已忘言”,從中看到的是內心境界的提升和升華。中國傳統園林是有自然美、建筑美、文化美三部分構成。文化美是園林內在精神的一種體現,園林的文化主要體現在楹聯、匾額、碑刻、書畫題記以及民間流傳的與此相關的傳說和典故等,從園林中亭、臺、軒、榭、堂等建筑形式名稱以及相應的對聯可以感悟到園林主人寧靜致遠、淡泊名利的精神氣質。其中拙政園很好的體現了這一點,如拙政園的一個臨水建筑名為“與誰同坐軒”是來自蘇軾的詞“與誰同坐?明月清風我。”,由此可見中國傳統園林提倡情景交融、寄情于景,由此我們可以聯想到園林主人坐在園林亭廊中,與朋友吟詩暢談的畫面,這也從側面提升了園林“空靈”的藝術氣質、使園林更加富有意境。天壇是古代皇帝與天進行對話的地方,祭天的那個臺面對著的是虛無的蒼芎,人在此放空心靈與天對話、進行心靈的溝通,這暗含著中國古人對于“空靈”之美的追求。
中華民族千百年來形成的審美思想在世界上獨樹一幟,其中“空靈”是藝術心靈所能達到的極高境界。空靈的作品帶給人的感受是美的,是有意境的。“空靈”的園林設計才會擁有靈魂和意境,才會讓人“一見鐘情”。當代藝術從業者在進行藝術創作時要多考慮并注重體現中國傳統美學思想,創作出更多有靈魂的、“空靈”的作品。
(作者單位:東北大學藝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