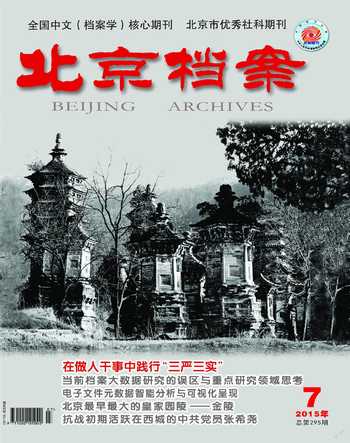開啟塵封檔案 辦理移民手續
任曉爽
一切要從一個電話說起……那是一個工作日的上午,我在閱卷室接待著一名當事人查閱案卷,這時導訴臺給我打來電話,告知我有人調卷。
“您好,請問您知道案號嗎?”我問道。
“什么案號?我不知道。”
“那您告訴我是哪年的,什么案子?”
“好像是五幾年的,離婚的案子。”
“當事人本人來了嗎?”
“這是我母親的案子,她去世已經三十多年了。”
“您告訴我您母親和對方當事人的名字?”
“我的母親叫生某,對方好像叫趙某。”
“請您稍等,在您前面還有一位調卷當事人,給他辦理完畢,我就出去接待您。”放下電話我就在想,這是什么人呢?怎么會連自己父親的名字都不確定。心里雖然這么想,可手上的工作一刻不停。
接待完正在調卷的當事人,我就通過查詢系統查找歷史檔案,可是查了半天,仍然一無所獲,怕外面的當事人等急了,我就趕忙到南大廳將當事人帶到閱卷室,細細詢問。
“您好,剛才通過您說的姓名,查詢檔案系統,我查不到您說的案卷。所以需要您給我更多的資料,我才能幫您查找,您再想想具體是哪年的?”
“我母親的這個案子我具體一句半句也說不清楚,您給我點時間,聽我慢慢跟您說。”當時手表的指針已經指向十一點三十分,看到他真誠的樣子,我輕輕地點了點頭。
“我的母親生前是咱們區王平村的干部,她在1951年生下了我的姐姐,之后和第一任丈夫離婚了,姐姐由我母親撫養,也就是我今天需要調的這份判決書。過了幾年,我的母親認識了我的親生父親,和我父親結婚后生下了我的哥哥和我。但在我四歲左右的時候,我的母親和我的父親也離婚了,我的哥哥由爺爺奶奶撫養,隨父姓,而我和姐姐由我母親撫養,改隨母姓。通過區檔案局,我查找到了我父母的離婚判決書,但我查不到我母親第一次婚姻的判決書。我的哥哥已經在美國定居三十余年,他希望我和姐姐也可以移民過去,和他在美國生活,現在美國的一個辦事機構需要一個手續,證明我姐姐和我哥哥的同母異父關系。”
聽完了他的講述,我知道這份判決書對他的意義重大,拿起他母親第二段婚姻的離婚判決書,我認真地看了一遍,其中提到,他的母親和父親于1954年結婚,“您確定您的母親是在生下您姐姐后不久就和第一任丈夫離婚的嗎?”我問道。
“是的。”
“通過您母親的第二次婚姻判決書和你的陳述,您母親的第一次婚姻判決書應當是在1951年到1954年之間,我從電腦上再幫您查查。”
通過檔案系統的檢索和掃描室電腦里的掃描原件搜索,我都沒有找到這個案件,而且很奇怪的是電腦里竟然沒有1950年到1954年的案卷材料。
這時手表的指針已經指向了中午十二點。剛才給這位當事人做閱卷身份登記的時候,我留意到他的家住在東直門,大老遠地來一趟不容易,我是真心想幫他找到這份判決書。
可是作為一名檔案室的新人,我已經窮盡了自己的查卷方法。正在苦無辦法之際,我看到中午下班經過閱卷室的老檔案員老李,他不僅是我院的“元老級”法官,也是檔案室的“百科全書”,工作上有什么不明白地問他準沒錯,此時我的心情就像陰霾的天空中透出的一米陽光。
我把當事人的情況簡單地向老李陳述了一遍,老李看了看焦急的當事人,對他說,“您也別太著急了,您的心情我們能理解,現在電腦上查不到您需要的判決書,我們會用最原始的索引卡片查找您的案件,請您留下聯系方式,我也把我辦公室的電話寫給您,一旦查到判決書,我們會立刻給您回復,今天您就先回去吧,大中午的,先去吃飯吧!”當事人得到答復后滿面愁容地離開了法院。
待當事人走后,我問老李,“您說他這判決書能找到嗎?連年份都沒有,而且我的電腦里還沒有1950年到1954年的卷宗。不是院里所有的卷宗都經過掃描存入電腦了嗎?”
老李說:“曉爽,你剛來,從前也沒碰到過當事人調取年代這么久遠的卷宗,但你只需要明確一點,就是只要能確定案子是在咱們院審的,卷宗就一定可以找到。但是你剛才提到的這個時間段的卷宗,前幾年我院銷毀過一批。”一聽到這兒,我剛露陽光的心情又烏云密布了。老李又接著說:“但是……雖然卷宗銷毀了,但判決書一般都有所保留,你盡力去查查吧。”此時我心中希望的小火苗又燃燒了起來。
由于當天下午閱卷的其他當事人較多,直到第二天上班我才有時間仔細查找這份塵封的檔案。
1951年到1954年期間,我院審理的案卷說多不多,但說少也不少,在檔案室陳少忠的指導下,我第一次學會使用卡片查找案件。看著那一排排落滿塵土的有些掉漆的綠鐵皮柜子,我知道它承載著當事人的希望。那小小的發黃卡片,以當事人的姓氏拼音的第一個字母分門別類,由于當事人姓氏并不多見,經過半個多小時的翻查,我才查到了這個案件,編號為:1952年民判字第76號。我給自己暗暗鼓勁,找到了案號,就離找到判決書不遠了。
我院的檔案庫有兩個,一個是存放1980年以后的卷宗的大檔案庫,也就是現在我經常可以去查卷的檔案庫。還有一個是存放1980年以前卷宗的小檔案庫,要不是因為這次當事人調卷,我一次也沒有去過。
一進入小檔案庫,給我的第一感覺就是昏暗,也許是檔案柜太多、太高,擋住了燈光;也許是因為來存取卷宗的人太少,缺少了人氣;我頓時就感到卷入了歷史的漩渦。檔案庫內都是清一色的舊式綠色鐵皮柜子,柜門上的卡片槽內手寫著卷宗的年份,通過之前查找到的案號,我一排一排地檢索著卷宗的年份,二十分鐘后,我終于看到了“一九五二”四個大字,心中為之一振。我快速地打開柜子,將1952年有關的四大本卷宗判決書全都抱出來。
小心地打開第一本法律文書檔案,秀氣的字體浮現在我的面前,當年的判決書都是手工刻寫蠟紙印刷,要不是身上還肩負著為當事人查找判決書的重任,我還真想把每一份判決書都細細研讀,把每一個字都認真看一遍。盡管當年所有判決書都已襯紙,但我還是小心翼翼地翻查著,伏案細查一個小時后,我終于查到了76號判決書,心中的成就感油然而生。
待我小心翼翼地將發黃發舊的判決書復印后,便立刻聯系了該名當事人。他見到我后,止不住地道謝,“真是太感謝您了,辛苦您了,沒想到六十多年前的判決書,您不到二十四小時就找到了,真是幫了我大忙了,這份判決書連我姐姐本人都沒有見過,這下我們可以辦理移民手續了。之前我從來沒和法院打過交道,總是覺得法官是高高在上,不可親近的,沒想到你們真的和新聞報道的一樣親民、為民,想群眾所想,急群眾所急,太感謝了!”
由于年代久遠,有些字跡已經看不太清楚,根據當事人的要求,我又將判決書反復復印了三四次,這期間他又跟我聊起了他母親的生平……
這次的調卷工作對我的影響很大,使我對檔案工作有了更深刻的認識,送走當事人后,撫摸著厚重的歷史卷宗,我陷入了沉思。
法官在審理案件的時候,就案件的本身辨法析理,看到的只是當事人人生中的某一階段。我作為一名檔案工作者,打開塵封的卷宗,透過這兩份判決書,我看到了調卷當事人母親坎坷的一生,看到了他的兒子、孫子是如何的自強不息,通過知識改變命運,那一本本落上塵土的卷宗不再是死氣沉沉的紙張,而是賦予了鮮活的生命,將案件事實活靈活現地展現在我面前。通過這次的調卷,我看到了檔案塵封的歷史,看到了它的價值所在,作為保存歷史的“蘭臺人”,我感到了責任重大,無比光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