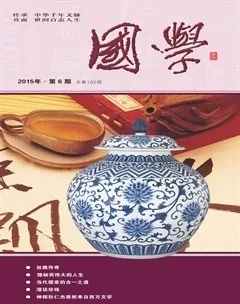歷史辜負了乾隆,還是乾隆辜負了歷史?
鄭渝川
人們普遍認為,18世紀是世界經濟中心發生轉移的一個世紀。當時的中國正在經歷至今仍為國人津津樂道的康乾盛世。
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政治學者們都傾向于認為,康乾盛世實乃古代中國盛極而衰的節點,中國因而錯過了向近代和資本主義轉型的最寶貴機遇。在這個世紀里,統治中國長達64年(1736~1795年),退位后仍以太上皇身份專權的乾隆皇帝弘歷也因此成為受到批評最多的歷史人物之一。
很少有人會將乾隆與16~19世紀歐洲一些大國的帝王進行對比,比如彼得大帝、葉卡捷琳娜大帝、路易十四、腓特烈大帝、伊麗莎白一世,甚至是拿破侖。但在漢學家、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及歷史系講座教授、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歐立德看來,乾隆的歷史地位長期以來受到了不公正的低估。在他眼中,弘歷各方面都并不亞于同時期的歐洲君王,甚至更為杰出。
乾隆為何熱衷個人崇拜
乾隆時期,中國的西部、北部版圖獲得擴大,奠定了今天中國的遼闊版圖。歐立德在其《乾隆帝》中盛贊皇帝保護和擴張清帝國領土的“十全武功”,指出乾隆平疆并非窮兵黷武,這些軍事行動震懾了正在極力向西伯利亞和中亞擴張的沙皇俄國,奠定了兩國近一個世紀的和平。
但歐立德也指出,由于乾隆皇帝好大喜功,平定西域(新疆)的功績被界定為他這個偉大君王的,而不是清帝國這個國家的功績,當時的漢族知識分子也沒有意識到平疆的歷史意義。因此,在皇帝和滿漢大臣、知識分子的共同疏忽下,清帝國的邊疆治理仍主要沿用唐宋以來的松散體制,與漢族人口占多數的中原本部形成兩套截然不同的安排。
由此固然可以凸顯乾隆“天下共主”的尊崇地位,卻使得邊疆地區人民的國家認同感相當微薄。這項失誤帶來的后果異常可怕,20世紀初清帝退位后,革命黨人曾經打出“驅逐韃虜”的旗號,傳播擴散的速度甚于“五族共和”,邊疆地區居民的國家認同降到了冰點,加之沙俄的蠱惑,引發了一連串邊疆分離和叛亂運動。
歐立德指出,乾隆的合法性來自于上天,這就要求他必須將自己扮演成儒家圣人、士紳士人、藝術鑒賞家、精明政客,還要承繼中國古代史上若干英明君王的傳統;基于清帝國的特殊性,“他又將自己塑造為滿洲勇士的典范,精于騎射……一個掌握部分佛教教義智慧的虔誠者”。
此外,歐立德還認為乾隆的文化成就遠遠勝于其失誤。他歷數了作為藝術家贊助者、收藏家、書法家、詩人的乾隆皇帝對文化藝術以及相關工藝的終生摯愛。有趣的是,歐立德還提到了乾隆對歐洲畫師、繪畫技法及西洋鐘表的喜愛,反駁了近代以來對乾隆閉塞守舊的指責。
為什么乾隆注定不能成為改革者
歐立德還探討了乾隆時期的中國錯過歷史轉型機遇的原因。他認為,清帝國與歷史上以往的羅馬帝國、奧斯曼帝國、莫臥兒帝國有相似之處,更具有兩大不同:
首先是清帝國作為中國中原正統王朝的繼承者,必須在體制與結構上承接漢唐以來的傳統,皇帝事實上不可能隨意開展大范圍的創新,乾隆注定不能成為另一個彼得大帝。
其次是這個帝國的統治者是少數民族,必須時時刻刻注意人數和知識權力占優的漢人的反撲,也就是說,無論是乾隆,還是之前的康熙和雍正,都必須力促滿漢融合,圍繞這個政治正確主題行事。
錯過轉型的另一項主因是清帝國的統治集團沿用的特殊體制,使其越來越難涌現出可堪大用的文武人才。清朝一統中國前,皇太極就曾發出警告,要求皇室吸取金朝教訓,避免滿族健兒被漢人腐朽的官僚文化和脂粉氣所腐蝕。為此,滿族子弟被限制從事軍政之外的職業,由國家供養,還實行統一居住。這本是為了確保滿族子弟特別是皇室子弟具備尚武精神,但事實上卻加速了這個特殊利益集團的腐化和衰敗。
乾隆登基后,曾進行了50余次圍獵,還曾多次下旨要求滿人官員講滿語,這些努力收效甚微。滿族集團人才稀疏(傅恒、福康安父子是乾隆年間極其少有的宗室英才,屬于孤例),漢族知識分子又深受傳統之困,這就使得已經擁有“睜眼看世界”條件的乾隆無法做到以一己之力推動國家的轉型。再者,乾隆本人也是在清代皇族“圈養”體系中長大的,所參與過的競爭僅僅是幾個親王、貝子之間的奪嫡爭儲競爭,沒有壓力也沒有必要去睜開看世界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