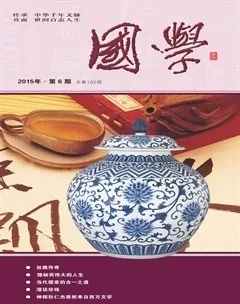久立行人待渡舟
張洲
“秋江一望淚潸潸,怕向那孤篷看也。這別離中生出一種苦難言。”
昆劇《玉簪記》里,《秋江》一折是經典,亦是劇情發展的高潮。潘必正被姑姑遣去赴考,不及向情人陳妙常道別,便登上了飄飄搖搖的小舟,蕭然而去。
妙常追至江邊,眼前是浩浩難以逾越的江水,內心糾纏著猜疑與焦慮,身后有道姑們的蜚短流長。而她還是決定雇漁舟追逐情郎。二人終于在江心會面,潘唱出了上段傷感的【小桃紅】,接下來的【醉歸遲】更是纏綿悱惻:
想著你初相見,心甜意甜。
想著你乍別時,山前水前。
我怎敢轉眼負盟言,我怎敢忘卻些兒燈邊枕邊。
只愁你形單影單,只愁你衾寒枕寒,哭得我哽咽喉干,一似西風斷猿。
凄涼總是別離時,古人送別的場景也總定格在山前水前。對于當時的人而言,山水,既是有情風景,更是無邊的阻礙。沒有便捷的交通工具,重山如天障,闊水若天涯。然而,山行雖艱,猶可送完一程又一程,五里亭飲過幾盞,十里亭下勸君再添一杯。相送的除了酒肴,更有一路牽動衣袖的風、半天亦步亦趨的云,每個流動的場景都能裁成記憶的扇面,在今后回望的夜里搖搖曳曳。
而水路則不同,行到水前,即須止步。所謂“云去云來山色,潮生潮落江沙。斜日系船渡口,短籬沽酒人家”(明·劉嵩《題秋江待渡》)。渡口的酒家,便是為離人而設的。“楊柳岸下,曉風殘月”,江畔餞別是一種定格的別離,水涯是一個斷點,江面流轉的漣漪,皆為惱人的深圓句號,此后,彼此都要展開不同的畫面,需要謀求另外一條出路,尤其是心路。“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波濤深處的孤鴻片帆,帶走的不只是內心的牽念,還是一種過去。
因此,江岸之悲使“渡江”成為了古代藝術重要的母題。在繪畫中,則多以“待渡”的題目呈現。“待渡”本已惶惶,畫上若再著一層秋霜,散幾陣雪霰,則在哀愁之外,更增蕭瑟之意,使“渡江”這個文化符號別有寒氣。而這些水前的吟詠與筆墨,當然不止于描繪類如潘、陳二人的離別,還潛藏著文人的寄托。
王維含待渡之意的《雪溪圖》,畫面此岸的狀況是悠游的,人在屋檐下,風雪不侵。對岸的樹木房舍影影綽綽,從容安適,類如他對仕途的景愿。而江面已有漁舟一艇,向自己劃來。因此,這是從容而入世的待渡圖。而元代錢選的《秋江待渡圖》,其自題云:
山色空蒙翠欲流,
長江清澈一天秋。
茅茨落日寒煙外,
久立行人待渡舟。
畫面對岸是青翠蔥郁的深山,代表著無法抵達的理想,自身久立于寒煙籠罩的此岸已多時,代表了無奈的現狀與內心的虛況,而中間橫亙的是一條暮色蒼茫的秋江,江上小舟似去未去,似來未來。這種空間對比感則生動地展現了元代文人的隱逸之心。
橋是對溪與河強勢的跨越和征服;舟楫則是對江與湖依順的妥協。小舟渡人,劃動著時光,渡的結果并不確定,注重的是渡的過程。渡也是度,從客觀的擺渡,可提升到精神的普度。佛教里有“六度”之說,度,就是到彼岸,就是解脫。
而解脫即擺脫苦惱,得到自在。元代詩人、畫家倪瓚的筆下,沒有以“待渡圖”命名的繪畫,但其山水畫中程式化的“一河兩岸”式的構圖,也有待渡的意味:畫面近景是此岸的樹石、亭臺,代表了人間的種種;中部的長河,無波無瀾,風平浪靜,恰如對人間種種的抵抗和疏離;而遠景的清凈之山,既不是如王維的入世的茂樹房舍、也不是如錢選的出世的層巒疊嶂。這種最簡潔的彼岸畫面,呈現的是回歸單純的天然,簡之又簡的太初狀態,寓意著生命的彼岸和精神的歸宿。
高濂《玉簪記》原本共三十四出,在第二十三出《秋江哭別》之后,還有《春科會舉》《定計迎姑》《合家重會》等,敘述潘、陳二人如何重聚,又如何皆大歡喜地共結良緣。而白先勇先生的青春版《玉簪記》,則將劇終設在陳妙常在舟中目送潘必正的船漸行漸遠處。最后那一幕,空蕩蕩的舞臺上只得妙常一人,古琴聲響起,如愁緒、如思緒、如江水延綿縈繞。
因渡而度,臺上臺下,那些被超越的秋水長天之外,世人多少情懷得以排遣,又不止于兒女情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