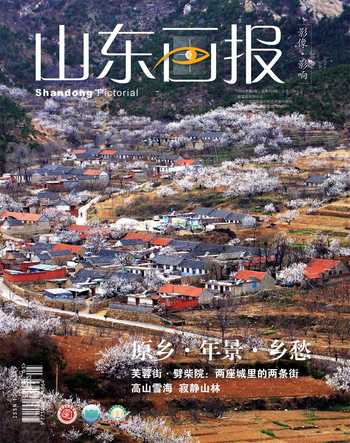望年·思鄉
劉磊



原鄉是此時回不去的家,鄉愁是當下難解的思念。
最這個叫“年”的節日里,總有人因無法團圓而一腔愁緒。于是,所有關于鄉、關于年的記憶也就尤其清晰而深刻。無論身在何處,城市的霓虹與喧囂,
終究擋不住望年思鄉的情愫。
同一時間,現實與記憶,兩條空間線,
串起了作者對鄉的思戀。
臘月二十七,我從潘莊回到濟南,27年來,我有兩次春節沒有在潘莊度過。一次是在2001年,我突發奇想體驗一次在縣城過年的感覺,后來后悔不已,一次是在2013年,我和未婚妻到她家商量婚事。2015年2月18日,農歷大年三十這一天,我的妻子和母親邊忙著照顧4個月大的雙胞胎女兒,邊籌劃著我在異鄉這個嶄新的小家庭的第一次年夜飯。
小時候,我一定是這個世界上最盼望過年的小孩之一。過年意味著放寒假離開學校一段不短的時間,意味著回老家生活一段不短的時間。爺爺和奶奶還會安排我去參與有趣的祭祀儀式,但壓歲錢對我的誘惑不大,因為它們終究會被父母騙走,而即使不過年,只要我回老家,奶奶也總是塞給我百十塊錢零花。我的爸爸有一輛小摩托車,后來換了一輛大摩托車。回老家時,他在摩托車的后座用繩子捆結實一個紙箱,我沒注意過紙箱里是什么,大概是些魚肉年貨。我爬上后座,背倚在箱子上,只等摩托車咯噔一響。從出發地一路向北,平坦幾十里,我龜縮在大衣里,風聲灌耳,忘了冰寒。路過十個或者八個村莊,就到了我特別熟悉的一片地方,那是一個門口總是停著一排貨車的水泥廠,然后再過二三里路就到家了。
就算是我的爺爺和奶奶知道我們會在哪一刻走進家門,他們見我們第一句話總是,哎呀,你怎么回來了。是啊,我們怎么回來了?我們回家過年了。
這是在濟南度過的第一次大年初一,我睡到了上午11點多還未醒來。我的妻子開始催促我起床去給鄰居拜年,睡眼迷蒙的我感覺回到了潘莊。
我們搬來不足一年,和同樓層里的兩家鄰居交往極少,只是經常在電梯里打照面。我和其中的一家鄰居不僅不熟,甚至還紅過臉。大年初一,我們沒有拜訪成幾戶朋友。給同一個小區住的朋友打電話,他們都回老家過年去了。打開手機微信朋友圈,有幾個朋友正實時分享他們的度假旅行。大年初二,我們看電視、吃飯、哄孩子,值得寫下來的是大女兒開始靈活翻身,二女兒可以被大人托舉著做飛行般的動作。我守著未來,想著過去,滿心歡喜。我想,明年一定要帶她們回潘莊過年。
初四,我回到了潘莊,初五就被妻子的電話召回。
下午六點鐘,初春的夜幕顯現,樓下的爆竹聲開始頻繁響起,經世不多的兩個女兒在身邊哭鬧。妻子和母親準備的年夜飯差不多了。
今年春節,我們一家四口和我的母親在濟南度過,我的父親在今天回到了潘莊和爺爺奶奶過年。我突然很羨慕父親,五十八年來,他所經歷的春節都是在潘莊度過的。這個時候,他和奶奶差不多包好了水餃等待下鍋,而爺爺應該已經做好了祭祀準備——備黃紙、請神和擺香臺。我和妻子、母親不用考慮祭祀,她們喊我去吃飯,我終于可以解脫看孩子的繁瑣了。 她們忙碌了一下午,晚飯十個菜品倒是非常簡單,不似我想象的那般復雜。妻子說,廚房里有兩個被她做失敗的菜品沒有出鍋,明天再收拾,我笑了。
爺爺和奶奶說過,過年就是回家,千里遙遠的兒孫也要往家趕,回家就是為了供奉祖先和天地,再吃頓團圓餃子。敬天地、尊祖先、圓人事,即使是在他們所經歷過的最困難時期,年的這種釋義也沒有被人們忘記。
大年三十下午貼好門聯。天一落黑,爺爺就會帶一些黃紙出家門向南去請祖先們回家過年,村南是我家祖墳所在的方向。準備黃紙和請祖先的事一定要家中的男者才能執行,每次爺爺去請祖先,奶奶都要催我同行,要我向祖先顯示禮貌,還有意要我繼承這項“事業”。爺爺背著手,不言不語,并不真的走到祖墳前,而是徑直來到家門南邊的一個路口,點著了黃紙,又用木棍翻了翻確保黃紙燒的勻實,口中念到,老爺爺老奶奶都跟我回家過年吧……
只有我們三個大人守著一桌飯菜略顯冷落,孩子的吵鬧和電視熒屏的閃爍活躍了些氣氛,我喝掉了半瓶紅酒、兩瓶啤酒結束了自己的年夜飯,在11點鐘給奶奶打了電話。奶奶說,他們還沒有吃飯,正在喝酒。我聽她那邊的聲音清切,她埋怨我這邊煙花爆竹聲太吵,我抱怨窗外的聲響嚇壞了孩子。
在潘村,這時候水餃正下鍋,家人先把雞、魚、水餃等貢品擺上香臺,上香磕頭敬酒,然后再把貢品端進屋里大桌上,請祖先魂靈享用,上香磕頭敬酒。香燃盡之后,這各色菜肴才會被端到正式的飯桌上,一年一次的全家團圓飯,正式開始。
將到十二點的時候,窗外彩光電閃,轟鳴陣陣。我住在十七樓,正是聲波影響大的高度,耳朵哄哄響過,腦子還在嗡嗡,兩個女兒鬧覺啼哭,我的妻子和母親各自懷抱著一個在客廳里踱來踱去。我沒有羨慕和欣賞的情思,罵著那些歡樂人家。
奶奶還沒有吃飯是因為還沒有祭祀老天,這段時間人們要在屋子里安然等待上供時間的到來,被稱為“熬五更”,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守歲。等“熬”到凌晨十二點,潘莊的年正式開始。餃子下鍋,盛出來和雞、魚一起搬到院子里的香臺上,點香、焚紙、磕頭,奶奶則會念著各種虔誠的話語,祈求全家人來年平安祥福。
磕頭完畢,一掛爆竹被竹竿高高挑起朝向大門,我總被寄予全家厚望擔起挑桿重任。爺爺一手抓住垂落的爆竹,一手把煙深吸一口,然后把煙頭對向捻子,快步躲開。爆竹捻子起了火星,吱吱燃起,然后是電光閃爍、震耳欲聾……
凌晨一點半的窗外還有煙花閃爍,漆黑的樓群中保留著幾點燈光。我躺在在床上聽著妻子和大女兒的呼吸聲。潘莊的熱鬧在這個時候也該偃旗息鼓了,有的人家或許正在繼續喝酒或者打牌閑侃,他們精力充沛,不擔心天亮以后去挨家挨戶拜年。
潘莊的大年初一,滿是串門拜年的人群。人們早早的起床清掃前夜散落在院子里的爆竹殘屑,在屋里放置好坐人多的長條凳,在桌上擺好趕集買來的糖果和瓜子,打開了迎賓的大門。
上午,老人們在家里守著來訪的客人,年輕的人們則出門去拜年。拜年的人們大多同性結伴而行,男人有男人的幫伙,女人有女人的隊伍,孩子也有孩子的行列,反正不是一幫近門族親,就是一伙志同好友,特別是在外回鄉的人們,正好敘舊同行。在潘莊男女有別的社交秩序在此時可窺一斑,孩子自懂事起就會自然遵行。拜年,是一種特別的社交方式。到了中午吃飯的時候,年輕的人們就逛的差不多了。下午,老人們就走出家門有選擇的去拜年。老人在喜慶的日子里互拉家常,談笑間化解或者緩和兩家矛盾。鄉村社會繼替中產生的尊長權威在此時發揮著重要的社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