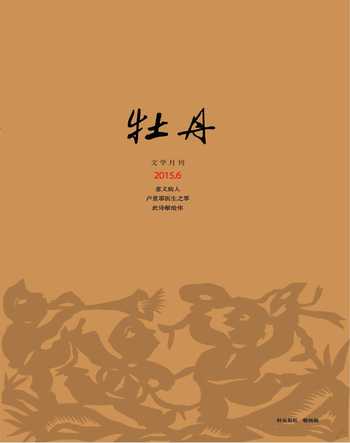外婆
翟柏坡
外婆一輩子沒(méi)生過(guò)大病,沒(méi)住過(guò)醫(yī)院。2009年暮春,布谷鳥(niǎo)歡叫著從村莊上飛過(guò),地里的麥梢已黃。當(dāng)時(shí),外婆已患嚴(yán)重的白內(nèi)障,眼睛幾乎失明,那天早上她摸索著到廚房刷鍋,踩到了臺(tái)階上的一根木棍,一個(gè)趔趄,身子后仰,頭重重地磕到臺(tái)階旁的花池上,不省人事。
這一躺下,外婆沒(méi)能再起來(lái)。零亂的白發(fā)帶著血跡,繞在腦后。她平躺著表情木然,呼吸急促。臨近黃昏,外婆出著粗氣,一陣急喘,嘴角流出黏稠的口涎,等到恢復(fù)了平靜,慈祥的外婆走了,時(shí)年她87歲。輸液的藥滴不再下滴,而我卻雙眼模糊,淚如雨下,握著她瘦削的手,心被掏空了。
我的母親1991過(guò)世,守在外婆床前的是三個(gè)姨和一個(gè)舅,擦洗外婆的身體,她皺巴巴的皮膚像老榆樹(shù)皮,蒼白的頭發(fā)已經(jīng)稀疏,堂屋中,幾塊木板支起一個(gè)靈床,外婆被晾在上面。聞?dòng)嵹s來(lái)的親戚,在院門(mén)口外點(diǎn)燃了紙馬,每個(gè)人手里,拿著一炷燃著的香,屈膝,跪下,伏地痛哭。望著繚繞的紙煙,癡想著外婆乘著白馬,升天了。
外婆的一生,是辛勞的,匆忙的腳步,就像一個(gè)旋轉(zhuǎn)的陀螺,一刻也不曾停下來(lái)。她出生在鄰村一個(gè)貧窮農(nóng)家,自小就學(xué)著做家務(wù),縫縫補(bǔ)補(bǔ),洗洗涮涮都會(huì)。纏腳沒(méi)多長(zhǎng)時(shí)間,就趕上政府命令禁止婦女纏腳,慶幸她長(zhǎng)著一雙大腳板,風(fēng)里來(lái)雨里去,干活賽過(guò)后生。外婆十六歲嫁到我們村,歷經(jīng)兩次婚姻,生育五個(gè)娃,四女一男,母親排老大。外婆三十多歲守寡,面對(duì)尚未成年的五個(gè)孩子,生活的重?fù)?dān),全壓在外婆身上。她忙碌的身影有時(shí)在燃燒著嗆人柴火的灶臺(tái)上;有時(shí)在費(fèi)力推轉(zhuǎn)著沉重轆轤的井臺(tái)上;有時(shí)又出現(xiàn)在坑洼不平的泥路上,任背帶勒進(jìn)肩膀,她依然弓腰前傾拉車(chē);有時(shí)又鉆進(jìn)掛滿(mǎn)蛛網(wǎng)的牛圈,耪著令人發(fā)嘔的牛糞……。年復(fù)一年地播種收獲,捉蟲(chóng)除草,澆水灌園,耙地起壟,經(jīng)常是汗水浸透了衣衫,摸黑才回家。黑燈瞎火,她先到床上摸摸橫七豎八躺著孩子的腿,看看夠不夠數(shù),若不夠,就提著罩燈,喊著名字,四處尋找。有的睡在別人家,有的睡在土堆邊、柴垛下,一個(gè)個(gè)抱回家,直到這時(shí)才松口氣,坐在屋門(mén)檻上,脫掉鞋子,磕掉里面的泥巴,又忙開(kāi)了。晚上有月亮?xí)r,在月底下紡花,洗洗衣服;沒(méi)有月亮,就借著油燈搖紡車(chē)。深更半夜,收拾好填飽肚子的東西,蓋好盆盆罐罐,一天的活才算干完。這樣的生活持續(xù)了五六年,直到母親她們能幫她干些家務(wù),才稍稍喘了口氣。
后來(lái),孩子們一個(gè)個(gè)成家傳人,外婆地里的活也一直沒(méi)丟。外婆五十多歲眼都花了,經(jīng)常叫我?guī)退x針。八十多歲,她的眼睛出現(xiàn)了云翳,視力逐漸模糊。春天到地里拔草,她很少把麥苗拔掉,薅下都是野草,她說(shuō)憑的是感覺(jué)。后來(lái),視力越來(lái)越差,她還常去放牛,好幾次都是別人看到她跌跌撞撞,把她送回家。
外婆不識(shí)字,哄孩子常唱些小曲,“板凳板凳摞摞,里面坐個(gè)大哥,大哥出來(lái)買(mǎi)菜,里面坐個(gè)奶奶,奶奶出來(lái)燒香,里面坐個(gè)姑娘,姑娘出來(lái)紡花,里面坐個(gè)雞娃,雞娃出來(lái)啄食,里面坐個(gè)皮人,皮人出來(lái)射箭,一下射到南院,南院有個(gè)井,井里有個(gè)桶,桶里有個(gè)罐,噗嚓兩半”這個(gè)小曲我們聽(tīng)的最多,我偷懶不想干活,她會(huì)唱小曲“小母雞,噙柴火,一天噙它一大垛。”外婆沒(méi)文化,但心靈手巧。她做的小孩穿的老虎靴,栩栩如生,誰(shuí)家添了娃娃,都上門(mén)要她做一雙。我母親和姨們,穿著外婆做的粗布衣裳,紡布、織布、漿洗、剪縫一樣不落,然后買(mǎi)些蓼藍(lán)、靛紅等染料,和衣裳放到鍋里煮著上色。在那個(gè)單調(diào)灰色的年代,幾個(gè)姊妹,皆紅衣綠褲,花枝招展,煞是招人喜歡。
上世紀(jì)五六十年代,正是生活最困難的時(shí)期,餓死人的事也不算新鮮事。外婆為養(yǎng)活五個(gè)孩子,絞盡腦汁,生活精打細(xì)算,每天天不亮就在廚房忙開(kāi)了,為了一天在地里忙,給孩子準(zhǔn)備好吃的,或蒸或烙。蒸的有玉米窩頭、虛糕、紅薯、紅薯面饃,或蒸一籠玉米面拌野菜,野菜有榆錢(qián)、槐花、大楊葉、水根菜等。蒸熟后灑些鹽水、蒜汁,幾個(gè)孩子看著都流口水。烙饃主要是鍋盔、野菜饸子、野菜團(tuán)。灶臺(tái)靠邊的墻上,釘著一塊木板,上面放著瓶瓶罐罐,有腌辣椒、腌蘿卜、腌茴椿、腌韭花、腌白蒿等。逢年過(guò)節(jié),蒸一籠白饃,定下規(guī)矩是誰(shuí)最勤快,先吃個(gè)白饃。但重男輕女的外婆常背著女娃,偷著給舅舅饃吃。
我十歲以前,我家六口和外婆家四人,一直合著灶。外婆有些重男輕女,對(duì)我這個(gè)大外孫,有些偏愛(ài),有好吃的,總愛(ài)給我留點(diǎn),或多給點(diǎn),姐姐和妹妹對(duì)此很眼熱。我生日這天,一定要煮個(gè)雞蛋,或用鐵勺就著麥秸火煎個(gè)雞蛋。秋天收割玉米,她總不忘挑些葉黃稈紅的玉米稈,截成一尺多長(zhǎng)的甜稈,帶回家,讓我吃甜稈。入冬,最好的獎(jiǎng)賞是給個(gè)紅透的柿子,軟軟乎乎,皮兒薄汁多,太陽(yáng)光底下,透亮紅潤(rùn),一吮甜甜的柿子汁,甜到心里,嘴唇上的柿汁,也被我的舌頭“擦”得干干凈凈。
外婆去世已五年了。她的形象永遠(yuǎn)刻在我的腦海中,多少次夢(mèng)到外婆,以及月亮、大海、天空、大樹(shù),無(wú)論什么物象,從心理學(xué)上講,都和外婆有著千絲萬(wàn)縷的聯(lián)系。
今年清明節(jié),我又來(lái)到外婆的墳前,墳頭的迎春花在靜靜綻放,質(zhì)樸、美麗、恬靜。“扯倆倆,拉鋸鋸;婆家墁唱對(duì)戲,什么戲。《沙家浜》、《紅燈記》。”我唱著,眼淚如雨飄落在外婆的墳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