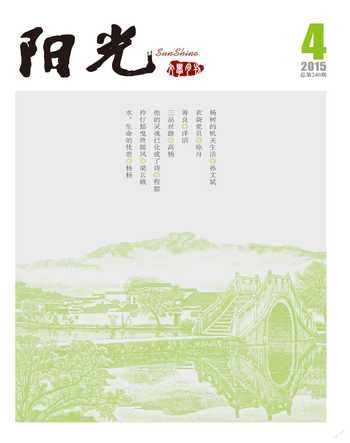高原的矚望與低處的夢想
西北詩人師榕,生活在甘肅平涼的隴東高原,多年來我們神交于詩的領域,至今尚無一面之緣。我與這位詩人的友誼開始于他的詩集《海在山外》,我知道他是在中國一個非常偏遠的地方舉起了詩歌的生命火把,照亮了人生一條不無崎嶇和泥濘的奮進之路。從他的詩中,我認識了甘肅的山野和華亭地層深處的煤,我從文字之上看見了這位詩人許多白天夜晚里那如炬的目光。
這本《師榕詩選》是詩人對自我創作的一次總結,是一個階段詩歌創作的集中展示。西部高原是中國陸地的脊梁,是一個民族棲息生存高度的地理象征。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昌耀為代表的一大批西部詩人,站在高原之上引吭高歌,詩意的風景在幻化中五彩繽紛,形成了一個時代沉雄而悠遠的精神高度。就是在這樣的文化大背景映襯之下,師榕走進了詩歌,成為西部高原眾聲合唱中一位有影響的詩人。從高原的角度說,師榕的詩站在西部高處。高原深處是煤,那里埋藏著火和高溫,于是詩人的心靈便擁有了低處的夢想,就有了一個詩人完整的藝術世界。
著名詩人雷抒雁先生對于詩與社會、時代的關系有著這樣深入的理解:“它是歷史的情感見證。即便不是對一個個偉大事件的述說,也是由那些事件的波動在心靈里留下的擦痕。詩的選擇,不同于歷史。考古學家可以從對一座古廟的分析,一座墓穴的開掘,正面認識歷史。地質學家卻注重從一根草的化石或者冰雪留在一塊巨石上的擦痕證說歷史。詩的細微,常常是一片草葉,一道擦痕,甚或一條逝去的波紋,讓人們認識時間在心靈里留下的真實足印。”(《激情編年——雷抒雁詩選》第1頁,作家出版社2008年9月版)詩歌不是歷史的寫實和記錄,但它要以情感的方式發出歷史的聲音。正如考古學家分析古廟、開掘墓穴,從一個特定的視角去發現歷史,去言說歷史。或者像地質學家從一根草的化石、從“冰雪留在一塊巨石上的擦痕證說歷史”。詩是用微妙的心靈感觸來抒寫世界和人生,是用細節的方式來折射出歷史或“一個個偉大事件”的審美影像。師榕立足在生存現實的土地上,敏銳地捕捉紛擾繁雜生活中的細枝末節,用詩意來提煉具象事物中歷史精神和哲學意義的深度內涵,他的詩是人情和人性感悟的結晶,是人生現實經歷體驗不斷升華的果實。
在《一只鳥逆水而飛》一詩中,詩人這樣寫道:
一只鳥逆水而飛
一場雪在陽光下轉瞬消失
一個人獨自穿過冬天
我走到河邊
卻沒能依水而居
只聽到冰凌斷裂的聲音
我找到了流水
卻無法捕捉鳥兒飛翔的姿態
鳥兒依戀著天空
我追逐河流的背影
詩中的鳥、人、河流構成了一種哲學的思辨意象,深切地表達了生存世界相依相生的微妙性。詩人在描述中有一種自由和率性的情懷,幾乎沒有刻意闡釋的痕跡,但其中富含的深意卻是不難領略的。在人生世界的大天地中,萬事萬物都在一種自然生態中循環運轉,就如詩中所表現的“一只鳥”“一場雪”“一個人”必然存在著一種相互依存的關系,這樣萬物才能有秩序地生生不息。師榕不是在講道理,不是在說教,而是憑借著所創造的情境來說話,可以說,這樣的情境是大于思想的,它有著超出詩人所感受到詩意內蘊的可能性。
師榕的詩追求一種發展中的現代性,他不是一位甘于守成而不思進取的詩人,他的詩有著明顯的探索性,他時刻把握著對于傳統藝術方式的更新式調整。他既不是背離傳統,又不是前衛得出格;他的詩可以讀出非常新異的感覺,但又不乏傳統文化及藝術表達的底蘊。《今冬無雪(之二)》就是一首在表現上很有新意的詩作:
冬天一年比一年暖和
我的目光與雪越來越遠
隴上今冬依舊無雪
誰能滋潤貧血的土地
這個季節的生命都在翹首以待
黃昏一瓣瓣絮狀的云朵
有序舒展著的可是紫色的雪
窗上的冰凌花是不是雪折斷的翅膀
看不到雪的冬天
情人的眼睛布滿血絲
愛情流著被釅釅思念泡軟的淚花
今冬無雪
一位名叫洛夫的詩人
在海峽彼岸說
葬我于雪
這首寫雪的詩構思很有特色,詩人是從“無雪”這個獨特的角度切入,把內心深處的冥思與外在景致中的事物聯系起來,是象征寫意的方式,“雪”作為詩的意象,成為詩人深切關注之后所賦予的更悠遠的意義,是以大自然的物象來表達人間世界情愫的一種糾結。寫“貧血的土地”,寫“隴上今冬依舊無雪”,由“雪”開始把情思拓展開去,到“情人眼睛布滿血絲”,又抵達愛情以及思念的淚水。師榕重視詩的抒情性,把“雪”的詩思描述推進到人性的表現,把直覺的景象和深度的意義溝通融合,把傳統的詠物抒情納入了現代性關照之中。尤其結尾一節寫到“海峽彼岸”的洛夫,時空大幅度的跳躍,使傳統的抒情言志表現出了一種全新的面貌。
說到抒情,我愿意把師榕的詩歸為偏重于抒情的一類,我是說他詩的感性有直抒胸臆的特點。在他的詩中,特別注重表達一種發自心靈底層的懷想和幽思,或者說有許多是與物象有關而難以名狀的東西。他的抒情是自由的,自由而不單一,不無率性的因素,從寫景狀物中來,時而冷靜,時而熱烈,通篇都是心靈真實的顏色。師榕的詩沉穩,讀來沒有虛浮感。不論是抒寫一己愛的情懷,還是面對社會人生實現表達的摯切詩思,都像燃燒的煤,讓人感到一種熱度和力量。在題為《深入夜晚的腹地》的詩中,詩人這樣表達內心愛的沖動:
親愛的 我深入白雪的內心愛你
雪中的火焰
重新喚起我心底的渴望
這是我駐守的最后一個冬天
除了對你的牽掛
活著我已別無所求
我是你虔誠的守夜人啊
還有誰能在這個暗夜默默贈給我
草莓、大海和心靈的力量
我殷切的矚望會不會
幻化成你睫毛上閃爍的淚光
詩是一種較為直接的情感傾訴,借助幻化式的想象來表達對愛人的戀念與神往。詩人注意選擇讓人耳目一新的意象來加大抒情的張力,使情感的表達進入了更強烈但更內斂的詩意境界,意象的新異性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詩的純度和品位。而從這些現代性的追求中,我們不難看到師榕還是不失傳統的表現優勢,盡可能地達成文辭質樸和意義暢達的藝術效果。像“我深入白雪的內心愛你”“愛你的火焰”“還有誰能在這個暗夜默默贈給我/草莓、大海和心靈的力量”以及“我殷切的矚望會不會/幻化成你睫毛上閃爍的淚光”等,在修辭上、在表意上都是在傳統言說的方式上尋求一種突破,使抒情更為趨近于詩化之美。
師榕是一位關注現實人生、擁抱時代和社會的詩人,他把責任和使命化為詩意悠長的慨嘆,他讓心中的悲憫燃起熊熊火焰。他那些寫煤礦的詩,表達了對他所立足的大山和土地的深情,他所寫的關于汶川、玉樹大地震的詩,抒寫了他無比寬廣的愛。作為詩人,師榕是靈魂舒展、心憂天下的歌者。當個人化的風習在詩歌寫作中甚囂塵上、許多詩歌沉迷于一己之私的情感泛濫之時,著名詩歌理論家謝冕先生有過擔心和憂慮,他說:“隨著個人化的推進,以獲得充分的個人寫作空間換來的是詩與社會生活的進一步剝離。大面積彌散的平面化和無深度,極大消解了詩的價值和意義。不僅是崇高的命題受到冷遇,甚至連傳統的優美和抒情性也變得遙遠了。由于眾多的缺失,眾多的詩歌都因而失去了分量。”(楊克主編《1999中國新詩年鑒》第494頁,廣州出版社2000年6月版)這確實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詩人毫無疑問是獨立的生命個體,從常識的角度說,社會應當尊重個人的選擇以及人格存在的獨立性。但我們同時又不該忽略每一個生命的個體優勢依賴時代和社會的基本前提,一個詩人價值和意義的彰顯,就必須關注自己的社會和時代,關注歷史積淀以及文化傳統所形成的詩歌精神。如果不能顧及“眾多的缺失”,個人化就會成為空洞蒼白的外殼而沒有應有的重量。
師榕出生在西北高原,是煤鄉礦區長大的孩子,他寫詩沒有忘記腳下賴以生存的土地,他時刻想著與他相依為命的煤和朝夕相處的礦工兄弟。《隴東的煤》就道出了這種生死牽掛不離不棄的深摯情懷:
大雪已過
太陽
從兩棵老槐樹梢上
蹦出
驅散了楊家溝上空的濃霧
寒霜消融 溫暖撲面而來
兩只長尾藍鵲
歡快地從金色的山岡上飛過
炊煙裊裊
從一排排石頭窯洞上升起
煤的光芒映照著向我走來的
礦工兄弟
紅撲撲的臉膛
我與群山懷抱中的煤鄉
相依為命
我很欣賞這樣大氣舒展的詩意營造,在表現上近于一種散文方式,空間性很大,意象的密度便疏散開來,但境界更為開闊,大雪、老槐、長尾藍鵲、山岡、炊煙、窯洞、礦工等一系列事物自然率性地排列開來,有一種天空高遠又情深意重的感覺。對故鄉土地的愛流溢于字里行間,這是體諒和融入的大情懷,他把個人的抒寫與更大層面的社會人生連接起來,樸素的文字中清新流暢的詩意自然地生長著。
立足于高原的鄉土,又不局限于此。師榕是一位心靈翅膀奮力飛翔的詩人,他舉起矚望和夢想,讓詩意的境界不斷放大拓展,他用腳步和文字去覆蓋更寬廣的山河大地,因此也讓自己和靈魂世界更大幅度地打開。他的矚望、他的夢想都與他所立足的高原和高原以外的世界有關,他向往美麗狂放的大海,他的詩思讓他的生命有了另一番靈動而深遠的意味。師榕用詩意之美營造他的靈魂空間乃至整個人生世界,他在詩中改變了自己的生命形態,從而不斷超越和升華并使人的品位達到全新境界的目標。當詩人與詩歌一起走出西北高原,他的心性獲得了另一種全然不同的空間,在一定意義上拓展了藝術表達的途徑。我從《在云南》一詩中,看出了他與以往不同的心靈天地,詩筆牽引文思,抒情有了更大的自由:
我上午看天
天很藍 云也高
我夜晚望月
月枕在高高的樹杈上安睡
云朵悠悠擦過我的頭頂
我聽見白云飄動的聲音
在云南 我一直琢磨
天與地
哪個距我更近
中秋的午后
我在昆明西郊散步
梅花鵝黃 在輕風中搖曳
園中的蘇鐵與我的肩膀等高
紅土地上 秋紅綠飛
我在陽光下
吃著米線 品著綠茶
翻閱一本名叫《大家》的刊物
對于師榕來說,云南是另一種世界,這里與大西北不同,他看到了滿是新鮮感覺的自然風物。兩相比照,他的想象空間得到了更大的展開,詩意疏放,寫作本身多了幾分從容與自在。這是“天也藍? 云也高”的云南,這是“月枕在高高的樹杈上安睡”的云南,詩人聽見了“白云飄動的聲音”。雖然筆致簡潔,也是平靜地寫去,但超邁之心境卻表現得極為充分。結尾的“我在陽光下/吃著米線? 品著綠茶/翻閱一本名叫《大家》的刊物”,這近于白描的一筆,十分自然輕巧,卻真正是韻味十足的性情之吟。
“鴻雁不來,之子遠行。所思不遠,若為平生。”司空圖在《詩品》中以此來定位“沉著”,幽然之思讓人品之不盡,可謂“絕妙好辭”了。我讀師榕的詩時,這幾句忽地跳到眼前,霜風野草,水天茫茫,時光如流水逝去;面對許多事物,詩人思之愈深,“鴻雁不來”的嘆息也自是一種詩意的悵然。
在《尋找靈魂的歸宿》一文中,著名詩人王燕生對師榕的詩給予了這樣的評價:“師榕的詩以純樸見長,感情細膩,情深意美,纖巧動人。沒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面孔。純樸而有意味,是詩的一種高境界。”此文寫作于1993年,如今已過去整整20年時間,詩人王燕生先生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他對師榕的評論可謂語重心長,“純樸”確是師榕詩歌的一大長處,有意味,有境界,沒有高深莫測的嚇人架勢。尤其關于“剔除一些敘述性的鋪陳,會變得更加精粹”的意見至今仍可作為借鑒。一個詩人要寫下去,提純的工作就不能停止。師榕的詩,散文化的傾向較重,描述的成分較多,隨時都有可能出現雜蕪的問題,對此應當保持足夠的警覺。
《師榕詩選》對于詩人師榕來說是非常重要的,這本詩集幾乎是他近年來為詩而努力的全部心血的濃縮。當我認真讀過這些作品之后,我的感觸很深。一個在人生路上奔走前行的人,他心中燃燒著詩意的火焰,不離不棄、無怨無悔地為詩而奮斗著。幾十年過去了,甚至把一生的矚望和夢想都化而為詩,他的情懷,他的感念沉淀在許多優美的文字之中。我特別看重師榕的追求和選擇,他的生命價值目標是明確的,他要通過詩性精神對人生的現實實現提純和超越。當然,《師榕詩選》也是一次證明,他是用自己的詩來確認靈魂和心性的位置。
我知道這是一條路,這是一條通向未來的路。師榕在《秋天的海》中寫下了這樣的感懷:
在秋天
我多么想對遠方的朋友
傾吐歲月的滄桑
我把心掏給你
你用微笑握住了我的手
秋天在戀人的手掌燃燒
走在趕海的路上
我伸開的雙臂
還沒有觸到澎湃的波瀾
可我的心中一片汪洋
師榕有一顆永遠進取的心,他大步走在“趕海的路上”。他懷里揣著西北高原地層深處的煤,向往著高原以外更廣闊的天地,他有著特別執著的個性和堅定的信念。無論如何,他都會一往無前地走下去,對此我堅信不疑。在《詩化的人生之路》一文中,著名詩歌理論家吳思敬先生說:“我與師榕相識有年,這些年來看到他不管生活多么艱苦,處境多么艱難,但始終與詩相伴,他走的是一條詩化的人生之路。我贊賞他的選擇,愿他在這條路上堅定地走下去,熱愛詩歌,珍視生命,那么他收獲的將不僅是鮮活的詩篇,還包括與詩長相伴隨的人生體驗,這后者也許更為珍貴。”(《海在山外》代序,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2008年1月版)在詩歌和人生的路上,師榕的進取姿態是令人信服的,歲月匆忙,他不斷留下美好的詩篇,人們可以看到一路上的花朵開放,我們祝愿這位詩人努力用心靈的色彩裝點人生世界,這樣的人也一定是幸福的。
邢海珍:男,1950年出生,黑龍江海倫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原綏化學院教授,綏化市作家協會副主席。曾在《詩刊》《星星詩刊》《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報刊發表詩作,出版詩集、理論評論專著多部。曾獲黑龍江省文藝獎等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