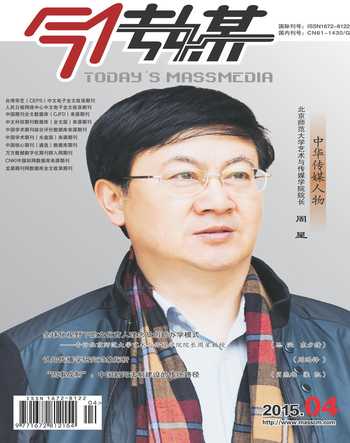費正清歷史視野中的大躍進(jìn)分析
許建華
摘??要:費正清歷史觀下的大躍進(jìn)可歸納為原因、結(jié)果和思考三方面,民眾對中央慣有的遵從是大躍進(jìn)發(fā)生的重要條件,經(jīng)濟(jì)上的人為饑饉和政治上的宗派主義是大躍進(jìn)帶給中國發(fā)展走向的轉(zhuǎn)變,大躍進(jìn)既是突破蘇聯(lián)模式的嘗試,也是延安運動和歷代民眾運動影響的結(jié)果,是歷史和現(xiàn)實的綜合再現(xiàn)。
關(guān)鍵詞:大躍進(jìn);費正清;歷史視野
中圖分類號:G201??????????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文章編號:1672-8122(2015)04-0134-02
歷史視野,即歷史觀、歷史眼光,就是把某一問題置于具體歷史時空中全面審視,既聯(lián)系該問題之前的歷史以探索其發(fā)生的合理性基礎(chǔ),又密切關(guān)注其后的歷史,做到高屋建瓴、客觀評價;既深入剖析其內(nèi)部因素以揭示各個環(huán)節(jié)的互動與關(guān)聯(lián),又重視其外部環(huán)境的影響與作用。費正清作為世界上最負(fù)聲望的中國問題觀察家,始終以歷史的眼光研究中國問題,這在他對大躍進(jìn)的研究中可見一斑。
一、發(fā)動大躍進(jìn)的重要條件:民眾慣有的遵從心理
一切中央的命令必須由地方當(dāng)局付諸實行,而中國民眾慣有的順從性則是推動中央指示順利落實的強大力量。費正清用歷史眼光審視中國民眾的心態(tài),認(rèn)為中國古代的保甲制度培養(yǎng)了民眾對中央權(quán)威的順從情感,并使這種順從情感逐漸固化和沿襲下來,成為中央有效動員群眾的有利條件。
費正清認(rèn)為,在大躍進(jìn)發(fā)動的過程中,一方面,“地方官員的士氣,他們對中央的忠誠,是決定成果的關(guān)鍵因素[1]”在提倡以謙虛的態(tài)度開展工作的背景下,一些地方的干部依然采用諸如報告、請示的機械方法向上級匯報工作,保留著濃重的官僚習(xí)氣,地方管理階層只管發(fā)號施令,而不切實地為人民服務(wù)。一些以政治家起身的官員,甚至只是為了表達(dá)他們的愛國熱情或無限忠誠而向上匯報成績。但事實是,由于急于求成、工作粗糙,很多迅速成立起來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合作社并未有效運轉(zhuǎn)起來;另一方面,地方干部的服從心帶動了群眾的歇斯底里,最終將大躍進(jìn)運動搞得聲勢浩大。費正清認(rèn)為,20世紀(jì)50年代初期,農(nóng)民對中共領(lǐng)導(dǎo)保持著高度的服從性,因為大部分從農(nóng)民積極分子中抽調(diào)上來的黨的干部,狂熱地緊跟領(lǐng)袖前進(jìn),并帶動群眾一起走。這樣,地方上對黨和國家當(dāng)局的服從心,就產(chǎn)生了群眾24小時“連軸轉(zhuǎn)”地工作,幾乎像無政府主義者一樣為追求自由而拋棄了一切束縛。
二、大躍進(jìn)的結(jié)果:開啟了中國經(jīng)濟(jì)和政治的轉(zhuǎn)折
大躍進(jìn)猛刮“共產(chǎn)風(fēng)”的直接后果是中國經(jīng)濟(jì)的滑坡,面對經(jīng)濟(jì)頹勢,領(lǐng)導(dǎo)人在經(jīng)濟(jì)發(fā)展政策上產(chǎn)生了分歧,在一味追求平均主義的風(fēng)氣中,這種分歧被放大為政治上的分野并成為宗派斗爭的開端。
(一)經(jīng)濟(jì)上的人為饑饉
費正清以歷史唯物主義的眼光回顧這段歷史,認(rèn)為大躍進(jìn)起初極大調(diào)動了農(nóng)民生產(chǎn)的積極性,農(nóng)業(yè)收成有所增加,但經(jīng)濟(jì)繁榮只是短暫的春天,隨著大躍進(jìn)運動弊端不斷暴露,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每況愈下。在1952~1957年期間,在農(nóng)村和城市人口分別增加9%和30%[2]的情況下,國家征集的谷物幾乎幾乎完全沒有增加,而又必須償還蘇聯(lián)貸款,犧牲農(nóng)業(yè)來建設(shè)工業(yè)的蘇聯(lián)模式已經(jīng)走到了死亡的邊緣。此外,人口過度集中,甚至超過工業(yè)化程度,帶來了農(nóng)村得不到充分就業(yè)和城市失業(yè)的現(xiàn)象。費正清指出,違背經(jīng)濟(jì)發(fā)展規(guī)律,脫離實際的做法是導(dǎo)致這一現(xiàn)象的重要原因,相互矛盾的指示和過高的積極性,使農(nóng)民筋疲力盡,農(nóng)業(yè)陷于欠收和半饑餓狀態(tài),以致農(nóng)民完全失去了信心。
(二)政治上的宗派主義
無獨有偶,經(jīng)濟(jì)災(zāi)難之后,政治上不妙的轉(zhuǎn)折接踵而來。中央政治局向來堅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制定黨的方針政策,這種民主協(xié)商的辦法具有凝聚各階層力量辦大事的好處,然而,大躍進(jìn)之后,一些領(lǐng)導(dǎo)人逐漸偏離了民主集中制的正確道路,陷入宗派主義的邪路。1959年,生產(chǎn)數(shù)字浮夸、大練鋼鐵運動失敗、農(nóng)業(yè)遭到破壞等經(jīng)濟(jì)弊端日益暴露,在廬山會議上,一些正確的意見被當(dāng)作對個人的非法攻擊而受到批判,黨內(nèi)人士扭轉(zhuǎn)大躍進(jìn)脫離經(jīng)濟(jì)發(fā)展軌道的努力被吞噬了,宗派主義斗爭的大門由此打開,大躍進(jìn)以一種“復(fù)興精神”繼續(xù)開展,廬山會議之后掀起的反右傾運動,使大躍進(jìn)的勢頭更加強勁,從而變本加厲地加重了災(zāi)難性的后果。
費正清將大躍進(jìn)置于共和國成立之初,中國人民社會主義經(jīng)濟(jì)建設(shè)經(jīng)驗不足的歷史時空中進(jìn)行考察,客觀評價這場運動:“盡管大躍進(jìn)未能持久,但在當(dāng)時卻是一場真正了不起的運動。這種動員勞力修建大型公共設(shè)施的做法,不僅僅是中國一種古老的傳統(tǒng),而且是中國為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而做的一種努力。[3]”同時,他指出這場運動存在不足,“使用這種方法需要學(xué)習(xí)電力學(xué)和應(yīng)用力學(xué)”?[3]。這也體現(xiàn)了中共在實踐領(lǐng)導(dǎo)人民探索現(xiàn)代化建設(shè)道路上的曲折性和漫長性。
三、反思:大躍進(jìn)是歷史和現(xiàn)實的綜合再現(xiàn)
費正清將大躍進(jìn)置于歷史的長河中,既在縱向上追根溯源,在以往的發(fā)展模式中尋覓先導(dǎo)性因素,又在橫向上聯(lián)系同時期的蘇聯(lián)社會主義國家的發(fā)展道路,從時間和空間交叉的多維角度揭示大躍進(jìn)的面相。
(一)擺脫蘇聯(lián)模式探索自己發(fā)展道路的嘗試
回顧中國共產(chǎn)黨的歷史,費正清認(rèn)為,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初期的革命活動多數(shù)參照了蘇聯(lián)模式。直到20世紀(jì)30年代和40年代,隨著馬克思主義理論越來越深入具體地應(yīng)用于中國革命實踐,毛澤東等人領(lǐng)導(dǎo)下的民族共產(chǎn)主義運動悄然發(fā)生。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共和國成立之初的八年中,在經(jīng)濟(jì)發(fā)展領(lǐng)域又回到蘇聯(lián)的模式。直到1958年,中共在毛澤東領(lǐng)導(dǎo)之下拿出了通過大躍進(jìn)來發(fā)展經(jīng)濟(jì)的方案。通過比較,費正清認(rèn)為中共在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解決中國問題的過程中應(yīng)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可將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放之四海皆準(zhǔn)的普遍真理,不可不加區(qū)分、一概而論。中共成功地運用馬列主義解決了中國農(nóng)業(yè)問題,但在解決中國工業(yè)化道路時就比較困難;在農(nóng)村工作中積累的經(jīng)驗未必適合城市。大躍進(jìn)開始時,中共中央委員會認(rèn)為斯大林的工業(yè)發(fā)展模式不適用于中國。同20世紀(jì)20年代的俄國相比,1950年的中國,其人口是俄國的四倍,但生活水平只達(dá)到俄國的一半。普遍建立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合作社并沒有帶來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量的增長,因此,當(dāng)時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水平,既不足以為工業(yè)化建設(shè)提供物質(zhì)支撐,也不足以為發(fā)展對外貿(mào)易引進(jìn)機器和供養(yǎng)快速增長的城市人口。經(jīng)濟(jì)學(xué)家提出降低重工業(yè)方面的投資比率(當(dāng)時占到了48%)來解決這個問題,即把一部分投資向輕工業(yè)方面傾斜,增多輕工業(yè)產(chǎn)品和生活消費品,這樣做對農(nóng)民來說無疑提供了一種物質(zhì)刺激,進(jìn)而將提高農(nóng)民的勞動積極性和生產(chǎn)熱情,上級部門也將更好地發(fā)揮作用。這種農(nóng)業(yè)革命“本來是許多經(jīng)濟(jì)不發(fā)達(dá)國家必經(jīng)的道路”[1]。然而,這種主張與當(dāng)時的決策格格不入,領(lǐng)導(dǎo)人試圖通過提高農(nóng)民思想覺悟而不是物質(zhì)刺激來增強生產(chǎn)動力,顯然,這包含了對農(nóng)民心理極大的而且不可靠的推測。這種建立在唯意志決定論之上的發(fā)展之道如風(fēng)中壘沙,必然失敗。
(二)延安群眾運動的復(fù)現(xiàn)
費正清通過對19世紀(jì)50年代至60年代初發(fā)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分析得出,以民眾動員為基礎(chǔ)的大躍進(jìn)是延安群眾運動的再現(xiàn),領(lǐng)導(dǎo)人傾向于通過發(fā)動群眾、打擊官僚主義等延安群眾運動的成功方法實現(xiàn)他們的愿望。延安時代的平均主義理想對農(nóng)民有著極大的吸引力。平均主義意味著可以通過滿足受苦群眾的需求和剝奪富裕人群的財富或權(quán)利,簡單地達(dá)到極權(quán)主義控制的目標(biāo)。但從歷史上看,它似乎也可以代表溝通統(tǒng)治階級與普通民眾,并使之獲取平等地位的一種嘗試。這樣,大躍進(jìn)的最初想法就是降低一部分人的社會地位,考慮到知識分子沒有參加過中共的長期戰(zhàn)斗,他們對社會建設(shè)可有可無,加之當(dāng)時有人宣稱書本是無用之物,知識分子在大躍進(jìn)中首當(dāng)其沖地遭到了無情打擊。
(三)歷代民眾運動的演化
在《觀察中國》一書中,費正清從體制和歷史的角度對大躍進(jìn)作分析,認(rèn)為首先必須從研究與經(jīng)濟(jì)有關(guān)的歷代王朝史著手。這些歷史著作詳細(xì)記載了新政權(quán)在統(tǒng)一中國后,是怎樣普遍使用徭役修建大型公用設(shè)施的(通常把人用到筋疲力盡),例如在農(nóng)民中實行“均田制”,并把他們組織成互相監(jiān)督、互相負(fù)責(zé)的小組。歷代王朝所用的巧妙方法不下幾十種,其中包括各地的“永豐糧倉”和在邊境上使用兵士開荒屯田。至于在實踐中學(xué)者兼管理者,代表著統(tǒng)治者無可爭辯的特權(quán),他們通過身體力行,制定、取締法規(guī)、進(jìn)行道德規(guī)勸和給予應(yīng)得的懲罰等方法,來組織人民的生活。費正清認(rèn)為,建國初期的中共領(lǐng)導(dǎo)人借鑒了前任動員民眾的精神,并因時因地制宜,加入了新的方法。大躍進(jìn)中,成千上萬的農(nóng)民帶著勞動工具,浩浩蕩蕩地走進(jìn)莊稼地,就像對待不共戴天的敵人一樣使足力氣進(jìn)行勞作,之所以出現(xiàn)這樣的情景,是因為發(fā)動大躍進(jìn)的最主要想法就是認(rèn)為充分的社會動員可以使經(jīng)濟(jì)問題迎刃而解,也就是說大量地使用人的勞動力,就能扭轉(zhuǎn)經(jīng)濟(jì)頹勢。當(dāng)然,勞力在開挖運河、利用水利灌溉農(nóng)田等大型工程的建設(shè)方面的力量和事實是客觀存在的,大躍進(jìn)期間的人工湖泊和水渠在今天的農(nóng)村依然隨處可見。費正清對此提出了質(zhì)疑:這種奮不顧身的大量體力勞動同先進(jìn)的技能和機器相比,對平均生產(chǎn)力的提高能起多大的作用呢?他提出,勞力的動員應(yīng)當(dāng)以能夠切實提高經(jīng)濟(jì)效率為前提,不然只是徒勞。
在閱讀與研究《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年)》《美國與中國》和《中國觀察》等著作的基礎(chǔ)上,本文對費正清歷史觀下的大躍進(jìn)研究做了簡單梳理與總結(jié),由于筆者資質(zhì)愚鈍,所述難免有不妥之處。費正清的歷史觀不止體現(xiàn)在對大躍進(jìn)的研究上,在整個中華民族歷史的研究中都貫穿著歷史觀的研究方法;同時,費正清對大躍進(jìn)的研究也不僅限于所列書目中,他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等著作對大躍進(jìn)都有深刻獨到的論述。費正清站在歷史視野的高度,為我們展現(xiàn)了大躍進(jìn)的全貌,無論是中國史的初學(xué)者還是淫浸已久的高手都應(yīng)借鑒并靈活運用這一研究方法,以還原歷史的真面目。
參考文獻(xiàn):
- 費正清著.劉尊棋譯.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
- 費正清著.張理京譯.美國與中國[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
- 費正清著.傅光明譯.觀察中國[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