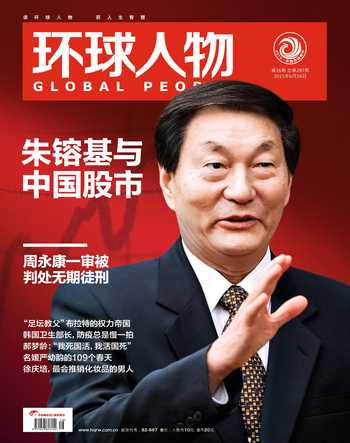格應大師
明海
“格應大師”是我們柏林禪寺民國年間的得道高僧。他本來的字號現(xiàn)已無從查考,只大略知道他是趙縣本地人,在柏林寺出家,曾到南方受戒,回來后就再沒有離開。他大約是在1941年去世,享年60來歲。
這幾年,我?guī)状翁峁P想寫“格應大師”,但總是無從下手。主要是一想到他的不為人所理解,我心中就涌現(xiàn)難以言表的感慨。
那還是1995年初,師父命我組織人編寫柏林寺志。柏林寺從建寺至今已有1700多年的歷史,但之前都沒人編寫過寺志。于是,我開始收集碑文、石刻,召集地方耆(音同奇)宿記錄口述資料。這時,我了解到民國年間一位僧人的事。當?shù)厝硕挤Q他為“各影”(音)。“各影”為何?我是南方人,乍聽不懂,細問才知道,這是個帶有污辱性的詞。在河北一帶,是令人討厭、惡心的意思。他們說這個僧人總是很臟,說話前言不搭后語。日本人進村時,寺里的僧人都跑光了,只有他留下來靠化飯為生。他化飯時,通常是往人家門口一站,喊:“中了飯唄?”僅此一句,并不多言。他邋遢的樣子讓人們起了這個傻子般的禪號,而他的真實法號則無人知曉。柏林禪寺最后的破敗竟與一個傻和尚聯(lián)系在一起,我們大家為此唏噓感嘆了好久。
直到有一天,一位老農(nóng)民找到我,事情才有了轉機。他叫張海慶,因為信佛,過去常來寺里,對寺里的情況知道不少。他交給我一疊寫滿字的白紙,其中有些是關于柏林寺的傳說,還有就是“格應大師”的事。他說自己是“各影”大師的皈依弟子,看到現(xiàn)在“佛門又開放了”,很高興,就把知道的情況寫了出來。這樣,“各影”師父的形象便在我心中清晰了,所以在我的本上,記錄為“格應大師”。所謂“格應”者,感格而應也!
據(jù)張海慶回憶,他外祖母一生拜佛,后來就領他去柏林寺拜了“格應”為師。1937年,那時他才十來歲。日本兵占領了趙縣城,柏林寺也未能幸免。當時寺內有一紀念趙州禪師的古佛堂,“格應”就住在那里,后來被日本人趕到外院的兩間土坯屋。寺里的僧人早已散去,財產(chǎn)也被侵占。“格應”卻在風雨飄搖時堅守在這里,每天上街化飯,回來后在破落的土坯屋里用功夫。
大家都說“格應”傻,沒文化,其實他已悟明心地。張海慶還記得他留下的順口溜:高高山上一樹桃,大風刮來小風搖。旁枝邊葉通刮落,剩下有限幾個桃。剩下大桃結佛果,丟下小桃還得熬……這些順口溜有的勸善,有的隱含了更深的奧義,有的則是他對佛教、柏林寺未來的預見。
張海慶年事已高,有些事已記不清了,但與“格應”的最后一面卻忘不了。“民國二十九年的冬天,師父3天未上門化緣。外祖母領著我去看他。進門一看:我?guī)煴P膝端坐炕上,口內念佛,閉目不視……他知道我來了,用木杵敲著我的頭說:‘我有幾句話等著跟你說呢。惡逢五八佛門閉……自管吃屈多忍耐……他最后對外祖母說:‘這兩句話要叫這個孩子記住:凈掃菩薩身,慧從塔院起。那時佛事昌盛,你可再入佛門。”第二天,“格應”坐化圓寂。當天下著雪,村民草草把他埋在了寺院東邊的空地上。
“格應大師”顯然是一位如濟公的高僧。他貌似癡呆,實是和光同塵,潛移默化。在那兵荒馬亂的歲月,他獨守這破敗的古寺,在蕓蕓眾生中出沒。可以想象他以神通智慧度化眾生的許多故事,也可以想象他遭受到的侮辱與誤解。他的沉默與忍耐使我們心生慚愧與后怕。仿佛那時在街上奚落他的就是我們,仿佛今天我們仍在不斷忽略身邊沉默的圣者……深夜掩卷,透過窗戶遙望星空,“格應大師”的事總會浮現(xiàn)腦際,使我心生一種神圣莊嚴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