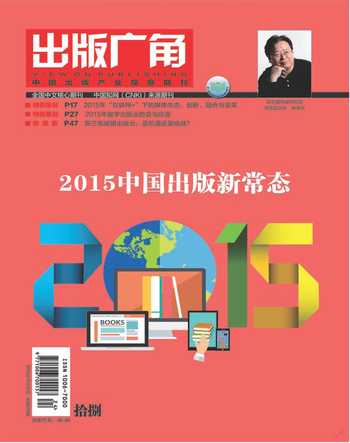清代“同光中興”時期儒學典籍出版初考
【摘要】“同光中興”是近代中國社會走向沒落前的回光返照。這個時期,雖然清朝的統治階層將學習西方的思想落實到了實踐層面,但這種學習仍然停留在器物和技術方面,社會正統思想方面還是堅持將儒家學說作為“中興”的思想支柱。在這種特殊的社會背景下,儒學典籍出版呈現新的特征。
【關鍵詞】“同光中興”;儒學典籍;出版
【作者單位】劉赫男,通遼職業學院。
從同治元年到光緒二十年(1862—1894)前后32年間的“同光中興”,是近代中國社會走向沒落前的最后一次抗爭。在這一時期內,面對國家和民族的危難,清政府在“中興名臣”的推動下推行了一系列自救的政策措施,使腐朽的大清帝國在衰敗道路上出現了短暫的反彈,形成史學界所說的“中興”局面。當時,由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的影響和客觀技術條件的限制,清政府提倡的儒家主流思想傳播主要依靠圖書的出版和流通來實現。于是,這種特殊的社會背景和技術條件給這一時期的儒學典籍出版帶來了新的機遇,儒學典籍出版在新印刷技術的影響下呈現新的特點。這是儒學典籍出版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
一、“同光中興”與儒學典籍
“同光中興”時間上是指從1862年到1894年前后的32年。人們通常認為“同光中興”即所謂的洋務運動,然而從“同光中興”的實際內容來看,洋務運動只是其中的經濟部分。我們可以從三方面完整概括“同光中興”的內容:軍事上,包括平定西北、云南、捻軍以及太平天國四次大規模農民起義;政治上,在短時間內重建了清政府在西北和長江中下游地區因戰爭遭受破壞的行政管理系統;經濟上,通過洋務運動在一定程度上振興了鴉片戰爭以來不斷下滑的封建經濟,中國經濟近代化開始起步。
在筆者知識范圍內,關于什么是儒學典籍,似乎沒有一個明確的界定。《辭海》對儒學的解釋為儒家的學說。這一解釋雖然無誤,但難免過于簡單和狹隘。《中國儒學》對儒學的解釋為儒學是孔子所創立、后儒所繼承發展的以仁愛為核心、以三綱五常為主要內容的儒家學說。按照上述兩種觀點,儒學典籍的范圍可寬可窄。從寬泛的角度來看,古代經史子集中受儒家學說影響、占了大部分的典籍都屬于儒學典籍。本文對儒學典籍的界定,其范圍僅局限于四部分類法中除去小學類的整個子部和經部的儒家著作。
二、“同光中興”時期的儒籍出版主體
1. 官方儒籍出版
“同光中興”時期,官方的儒籍出版主要是以官書局作為出版主體展開的。在同治以前,儒籍出版主要以中央的武英殿和地方各級學校、書院、官學為出版主體。同治以后,由于東南地區在戰火中遭受極大破壞,各種地方書籍出版機關蕩然無存,傳統的出版機關和技術已經難以滿足“中興”對迅速恢復文教的要求。于是,清朝地方政府直接參與出版工作,其以大型文集的校刻為起點,成立了一批官書局,作為官方儒籍出版的主要機構。著名的書局有金陵書局、正誼堂書局、長沙傳忠書局、江蘇官書局、廣雅書局、廣東書局(又稱羊城書局)、江西書局等。目前所能查到的資料顯示,當時官書局刻印的儒籍共計578種,占據了同時期刊刻總量的19.01%。其中經部儒籍為423種,子部儒籍為155種。這一時期的官書局刻印儒籍主要以經部儒籍為主,同時兼顧子部儒籍的刻印出版,意識形態色彩非常濃厚。
2. 書院儒籍出版
同治以前,書院是地方儒籍出版的主體;同治四年以后,清朝地方政府一邊成立官書局刻印儒籍,一邊同時恢復書院作為儒籍刻印的重要場所。這一時期的書院以江南地區的書院為主,其他地區有所發展,但是由于官書局的興起,書院失去了以往刻印儒籍的重要地位。整個“同光中興”時期,書院刻印儒籍總數只有138種。書院失去刻印儒籍優勢地位的原因大致有兩個:一是官書局的成立,二是各種原因造成的書院經費不足。
3. 私人儒籍出版
除官書局和半官方性質的書院刻印儒籍之外,還有以個人作為主體的私人儒籍刻印出版。私人刻印儒籍可以分為以營利為目的的書坊刻書(坊刻)和側重思想、學術推廣的私宅刻印(私刻)。目前可以區分的當時坊刻儒籍有298種,其中經部有266種,子部有32種。私刻儒籍有839種,其中經部儒籍為584種,子部儒籍為255種。在“同光中興”時期,私人儒籍的出版尤其是坊刻呈現出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新的印刷技術——石印印刷術的引入,二是新的出版單位——石印書局應運而生。這些新特點標志著中國近代出版業的興起。
三、“同光中興”時期的儒籍出版類別
1. 儒經的翻刻
“同光中興”時期,儒經翻刻是儒籍出版的主要方式,官書局的基本工作就是儒經翻刻。據統計,整個“中興”時期,官方和私人的儒經翻刻共計刊刻正經正注415種,其中編入合刻本的正經正注為271種,編入雜篆叢書和單行的有144種。儒經的翻刻數量在當時出版的全部儒籍中占了13.12% 。其中271種合刻本中的正經正注主要有十三經系統,包括武英殿本《十三經注疏》《袖珍十三經》(其中 《公羊傳》和《毅梁傳》采用明代閡齊極裁注本,《孟子》《論語》采用朱熹注本),同時列入兩本《易》的有金陵書局版本《十三經讀本》、魏氏《十三經讀本》和《十三經讀本附校刊記》;七經系統,即清代康乾年間皇帝欽定的《詩》《書》《春秋》《周官》《易》《禮記》《儀禮》;五經系統,即《相臺五經》《五經四書》《五經》。
2. 漢學書籍的出版
首先,諸經新疏的刊刻。近代國學大師梁啟超的著作《清代學術概論》對諸經新疏有這樣一段評論:“清學自當以經學為中堅。其最有功于經學者,則諸經殆皆有新疏也。”查考諸經新疏的刊刻情況,可以發現,梁先生的這一論斷并非虛言。這一時期比較著名的諸經新疏刊刻有惠棟的《周易術》、張慧言的《周易虞氏義》、姚配中的《周易姚氏學》、孫星衍的《尚書今古文注》、陳立的《公羊義疏》、孔廣森的《大戴禮記補注》等。這一時期總計21種新疏中有14種得到刊刻,占了總數的三分之二;并且這些得到刊刻的新疏刊刻的次數也不少,有3種刊刻了1次,剩余的大部分刊印了二三次,其中《孟子正義》《大戴禮記解詁》刊印了4次之多。這種漢學書籍的刊刻狀況比之于清嘉慶年間《國朝經師經義目錄》著錄的漢學書籍獲得刊刻只有28%的機會、再刊機會不到10%的狀況顯然要好得多。這也從側面反映了“同光中興”時期漢學書籍的出版狀況。
其次,《清代學術概論》提及漢學著作的刊印。梁啟超先生的《清代學術概論》總計提及29種著作,同光年間,這些漢學著作有刊印的數量為15種,剛好過半數,但是其中獲得二次刊印機會的僅有《群經宮室圖》1種,約為總數的3.4%。這種狀況與諸經新疏的再刊比例相去甚遠,即使與嘉慶年間《國朝經師經義目錄》著錄的漢學書籍6.8%的再刊比例相比也相形見絀。
筆者對比研究發現,21種新疏中有14種得到刊刻,刊刻次數總計達31次,其中有10次由官書局刊刻,有12次由書坊刊刻; 29種著作中,有15種獲得刊刻,刊刻次數總計17次,其中只有1次由官書局刊刻,2次由書坊刊刻。在出版方式上,采用傳統方法刊刻經文新疏和研究著作的機會基本上相等,但是,官書局和石印書局這類新的出版機構通常側重于經文新疏的出版,而不是研究著作的出版。所以,在這些新的出版機構中,經文新疏的出版機會要明顯高于研究著作的。
3. 宋學書籍的出版
首先,清人的宋學著作出版狀況。“同光中興”時期清人的宋學研究以“傳道學案”中的陸隴其、陸世儀、張履祥、張伯行4人為代表。這4人的著作在這一時期的出版狀況:陸隴其的著作有40種獲得刊刻,陸世儀的著作有4種獲得刊刻,張伯行有18種著作獲得刊刻;從數量來看,4人中陸隴其、張伯行、張履祥的著作獲得刊印的機會居于這一時期學者的前列,其中漢學家中可以與之相提并論的只有江永1人(著作刊刻19種)。從上述數字中我們不難看出,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指導思想下,“同光中興”時期在出版機會上,宋學儒籍要明顯高于漢學儒籍。并且,左宗棠、吳廷棟等高官對宋學儒籍刊印的關照直接反映了這一時期社會上層對宋學儒籍刊印的重視程度。
其次,鐮洛關閩的宋學著作出版狀況。鐮洛關閩的宋學著作除了收錄入《正誼堂全書》,其余刊刻情況:周敦頤著作《周子全書》被“西京清麓叢書”收入;張載著作《張子全書》被“西京清麓叢書”收入;朱熹經學著作《四書或問》和《國朝諸老先生論孟精義》被“洪氏唐石經館叢書”收入。朱熹性理著作中作為叢書出版的主要有《朱子遺書重刻合輯》《朱子全書》,作為單行本出版的主要有《朱子語類》《朱子五書》等。在這一時期,朱熹的著作被刊刻最多的為《小學集注》。
從上述情況來看,這一時期,各種形式的宋學儒籍得到了比漢學著作更多的刊印機會,反映了這一時期社會對宋學思想的青睞。儒籍在“同光中興”時期的出版狀況從其背景及具體表現來看,都不是一個簡單的事件。這一時期在江南地區發生的戰亂使傳統出版業受到毀滅性打擊,重建過程中產生的官書局成為官方刻印圖書的主力。同時,這一時期新印刷技術的傳入實際上催生了石印書局這種帶有近代色彩的出版機構。這種新的出版機構和官書局一起直接參與了儒籍的刊刻。此時清政府面對的內憂外患危機使當時的乾嘉學派難以繼續發揮思想學術的支柱作用。在中興運動中,從朝廷到普通的書齋,人們開始將注意力轉向一直被忽視的程朱理學。由于曾國藩等中興名臣的努力,理學在這一時期成為人們救世的思想良方,受到官方和民間的重視。這種思想的轉變反映在出版領域,就表現為正經和相關儒學著作成為官書局出版的主要對象。
[1]《辭海》[M].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0:263.
[2]龐樸.中國儒學[M]. 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7:5.
[3]徐曉楚. 清“同光中興”時期儒籍出版考[D]. 華東師范大學,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