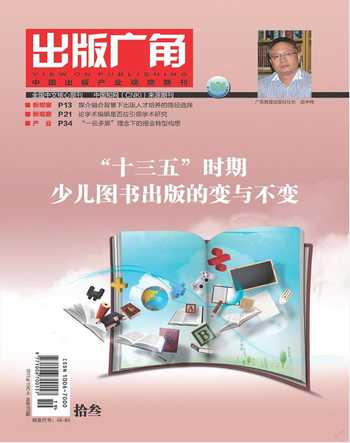專業圖書數字化出版探究
【摘要】對于專業圖書出版來說,數字化出版將如何開展,如何深化、如何盈利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筆者以專業圖書出版數字化轉型為視角,對專業圖書的數字化出版進行探究。
【關鍵詞】專業圖書;數字化出版;著作權保護;盈利模式
【作者單位】王哲,群眾出版社,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
隨著數字時代的到來,出版業數字化轉型正如火如荼地展開。對于專業圖書出版來說,數字化出版將如何開展,如何深化、如何盈利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筆者以專業圖書出版數字化轉型為視角,對專業圖書的數字化出版進行探究。
一、專業圖書出版
專業圖書出版,顧名思義就是將專業化的書稿經過編輯加工等一系列出版流程,最終印制成圖書的出版活動。專業圖書的出版與其他圖書的出版活動沒有任何區別,為什么筆者要專門提出專業圖書出版的問題進行討論呢?
首先,專業圖書出版是圖書出版的重要組成部分。市場上的圖書種類繁多,有少兒類圖書、教材教輔類圖書、科技類圖書,還有勵志類、生活類圖書等。市場需求不同,圖書分類方法也不盡相同。但有一類圖書,它的讀者對象相對固定,讀者范圍不是很大,圖書內容基本限定在某一領域,它就是本文所要討論的“專業圖書”。每個行業都有屬于自身行業獨有的、排他的特點,這種屬性被人們稱為“專業”。“專業領域”“專家”都是源自“專業”,“專業圖書”也是為“專業”服務的。就因為“專業”,所以專業圖書的出版只能由“專業”的出版機構才可以完成。從市場規律的角度來說,專業圖書的出版應該是在市場競爭下市場細分的結果,但我國的專業出版機構在計劃經濟時代已經進行了細分,其在市場經濟時代具有了先天的優勢,體現在專業內容劃分清晰、專業編輯隊伍健全、專業作者資源豐富、專業發行渠道成熟等。
其次,在數字時代,專業圖書出版也面臨與其他圖書出版同樣的問題。如今,互聯網、數字化、大數據、云計算使信息的傳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紙質圖書出版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紙質圖書原有的信息載體、信息存儲、信息檢索、信息傳遞、信息整合等功能幾乎全部能由數字媒體所替代,只剩源于讀者本身的閱讀習慣和圖書藝術化、個性化的外觀還暫時無法被替代。在這樣的背景下,紙質圖書的出版路徑一定會發生改變,至于如何改變尚沒有一個清晰的答案。從目前出版業的發展來看,出版路徑發生了改變,即加大數字化出版的比重,加強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提高出版機構的核心能力(核心能力包括策劃能力、編輯工作能力、編輯人員的專業素養等)。既然是圖書出版,無論是專業圖書還是其他類型圖書,都要遵循出版規律,都要接受挑戰。
再次,傳統專業圖書出版自身面臨的問題。專業圖書自身同樣面臨數字化的挑戰,甚至可以說這個挑戰更為嚴峻。為什么這樣說,因為專業圖書的讀者群體不大、范圍較小,專業化信息的量不是很大。如果讀者已經從其他渠道,如互聯網上獲取了相關信息,那么他就不會再通過購買紙質圖書獲取同樣的信息。也就是說,只要這個信息占據了一個載體,如互聯網,那么其他的載體,如圖書就會被讀者放棄,而互聯網這個載體的傳播功能如此強大,誰會是它的對手呢?
另外,專業領域往往有各自傳播交流的平臺,如網站、專業的電子刊物,這些平臺已經將數字化做得很好,信息的處理非常系統,讀者只要上網查詢,專業問題基本都能解決。那么紙質圖書與其相比劣勢顯而易見,如紙質圖書信息量不如網站、檢索項目有限、無法及時更新內容、視界不夠友好等。
二、數字化出版
數字化出版是指互聯網信息提供者將自己創作或他人創作的作品經過選擇、編輯和數字化制作,登載在互聯網或者通過互聯網發送到用戶端,供多人同時在線瀏覽、使用或者下載的傳播行為。數字化互聯網出版物主要分為8類:學術文獻數據庫,網絡期刊、圖書,網絡游戲出版物,網絡文學讀物,網絡教育讀物,網絡音樂,網絡音響出版物,網絡動漫。
2011年5月19日,原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鄔書林在教育出版數字化交流講座開班儀式致辭時強調,中國出版界要迅速行動起來,掌握數字化時代的主動權,跟上世界的數字化潮流。
時隔幾年,我國的數字出版有什么樣的發展呢?2014年,我國數字出版產業繼續高歌猛進,政策進一步利好,轉型升級、融合發展得到了自上而下的推動;產業規模明顯攀升,收入規模已達2540.35億元,同比增長31.25%,數字人才、特色資源得到進一步關注;推廣渠道更加多元,移動互聯、在線教育已經與出版水乳交融。
2015年 5月14日,在深圳舉辦的第十一屆文博會2015數字出版高端論壇上,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副局長孫壽山在報告中指出,據統計,移動互聯網用戶如今已達8.83億,為數字出版提供了更多空間。2014年,國民數字化閱讀接觸率達到58.1%,比2013年提高8個百分點,這也是數字化閱讀首次超過紙質圖書閱讀率。目前,傳統出版與數字出版的融合已提升至國家戰略,傳統出版要將內容優勢發揮出來,數字出版也要注重內容優化。
以上這些數字告訴我們,我國的出版業正在進行數字化轉型,大有“時不我待,只爭朝夕”的緊迫,也有“不往前走就是倒退”的危機。那么,專業圖書出版如何跟上數字化轉型的步伐,是當下迫切需要解決的課題。
從世界范圍看,當前專業出版、大眾出版的數字化商業模式已經日益清晰并逐步完善。比如美國在2011年就已經有20%的大眾出版采用數字化發行,而我國專業出版的數字化商業模式尚處于摸索階段,還有很多東西需要學習。
三、專業圖書數字化出版相關問題探討
從數字化出版的定義來看,數字化出版的主體可以是機構,也可以是自然人,本文的討論僅從出版機構的角度來進行。
1.專業圖書數字化出版要因“人”而異
作為專業圖書的出版機構,如何進行數字化轉型,采取什么樣的商業模式,應該是因“人”而異的。因為每個專業出版機構各具特色,除了專業不同,在管理、投資、人力資源、渠道資源、技術等方面,各機構也存在差異。例如,數字化轉型初期需要一定的投資,而且投資還要達到一定規模,如果沒有專項投資,轉型的速度則會放慢;在渠道方面,如果專業系統內原先就存在網絡系統,那么數字化后機構的發行渠道自然就會暢通;在技術方面,如果出版機構本身就是從事與網絡技術相關的內容出版,那么其數字化轉型的人力成本就會降低。因此,專業圖書出版機構在進行數字化轉型前,應該綜合評價自身的優勢劣勢,低成本高效益地完成轉型,不要盲目跟風。
2.專業圖書數字化出版與傳統出版的關系
數字化出版與傳統出版的關系,是轉型期人們頭腦中的疑問。它們之間的關系歸結起來就兩個,一是取代,二是并存。從整體出版角度來看,數字化出版與傳統出版應該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是并存的,這也是大多數人的共識,但筆者認為,在不遠的將來,數字化圖書出版一定會取代傳統圖書出版。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專業信息的傳播載體并非離不開紙介質。圖書作為信息傳播載體的大多數功能,數字媒介都可以完成,除了人們的閱讀習慣以及紙質圖書本身的藝術性、外觀裝幀等。專業圖書不存在藝術性及外觀裝幀等需求,因此,也不需要紙介質。至于閱讀習慣,在不久的將來,人們的閱讀習慣大多會偏向數字產品,從現在隨處可見的“低頭族”現象就可以預見。
二是專業信息的及時更新、傳播方式的方便快捷等需求也要求其借助數字媒介進行數字化出版。隨著信息、知識、科技的發展,專業領域的開發、拓展速度也將加快,信息量增大,知識更新加速,專業人士必須要及時消化吸收新的信息才能跟上節奏。同時,快速的更新也需要傳播方式的變化,便于人們方便快捷地獲取這些信息,而數字媒介是最好的選擇。
三是投入產出的需求。許多作者提供的書稿基本上是電子版的,傳統出版將其轉化于紙質介質上,消耗了大量紙張,在印制過程中還有印刷耗材的消耗,既不環保,也不節約,還延長了出版時間。而數字化出版則不需要紙張及印刷材料的使用,可以說完全是綠色環保,不僅減少了出版環節,還縮短了出版時間。數字化出版在轉型初期投入大,但進入正常軌道后,其出版環節的運營成本要低于傳統的出版環節。
3.著作權保護問題
筆者認為,數字化出版面臨的最大問題,不是技術問題,而是著作權保護問題。在紙介質時代,由于復制相對困難,查處相對容易,國家對著作權的保護還是可以預期的。但在互聯網時代、移動數字時代,侵權者要想復制文稿易如反掌,而且侵權者的ID可以非實名,加上接收的終端天南海北,侵權者往往不知道自己已經違法。這些現象使著作權的保護十分困難,成為數字化出版巨大的障礙。有些出版機構由于無法逾越這個障礙,便在數字化轉型方面停滯不前。著作權保護問題如果解決不好,將嚴重影響今后數字化出版正常發展。那么該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
首先,要有相應的法律來規范數字化出版著作權保護方面的相關問題。明確侵權行為的法律責任、侵權認定、處罰條例等,大力宣傳著作權保護的法律法規,提高人們的法律意識。
其次,疏通著作權交流的渠道。運用大數據、云計算等先進的計算機技術,使著作權在網絡中有明確的提示,哪些內容是開放的,哪些信息是受保護的一目了然。
再次,提高著作權保護的技術。在網絡環境下,如何保護著作權,限制來訪者隨意復制、隨意傳播,就需要有一定的技術措施。例如,可以通過密鑰、身份認證等技術來保護。
總之,作為與數字化出版相伴相行的著作權保護問題極為重要,對它的重視程度應該不亞于數字化轉型本身,因為它對數字化出版的影響是戰略層面的,應該得到國家層面的支持。
4.專業圖書數字化出版盈利模式的問題
伴隨著數字化的轉型,數字化出版的盈利模式也是各出版機構一直在探索的問題。有沒有一套行之有效而且成熟的盈利模式呢?截至目前,筆者相信還沒有。那么不妨在這里探討一下,在數字化出版的過程中哪些環節具有盈利的可能。
數字化出版與傳統出版相比,其出版模式發生了變化。傳統出版是產業鏈式的,從圖書策劃到讀者購買圖書,中間經過一系列的產業部門,涉及出版社、排版公司、印務公司、營銷公司、物流公司、紙張公司等;而數字出版是平臺模式,數字出版平臺是一個大的數據庫,出版機構負責不斷往數據庫中添加信息,消費者作為終端用戶,直接從數據庫中尋找需要的內容,不需要紙張、物流、印刷,只需要一臺能上網的電腦或一部移動互聯的手機即可。
無論是傳統出版還是數字出版,“內容為王”是出版機構存在的前提。從源頭上說,內容策劃是出版的第一環節,在這個環節上著作權交易可能產生盈利。如前所述,數字出版是一個平臺、一個數據庫,出版機構策劃出選題,從作者手中獲得著作權,這項著作權在平臺中與其他著作權一起,形成一個著作權產品市場,個人或機構可以像逛超市一樣從中購買所需產品,進行著作權的交易。對于專業出版來說,這個著作權交易市場更為適合,就像實體市場一樣,有各種專業化的市場,有專門賣衣服的、賣電腦的等。如果專業化的著作權交易形成規模,那么專業作者還可以為自己的著作權主動尋找平臺,這樣,出版機構又可以收取一項管理的傭金。
在產品的輸出環節,出版機構也可以盈利。數字平臺是一個數據庫,其中的產品可以任意組合、拆分,可以把若干小的內容整合成一個大的產品,也可以把一個大的產品拆分成若干細小的產品。比如,把一本書的章節拆分,每一章都可以出售,或者按消費者的要求,把不同書的不同章節整合在一起打包出售。
在營銷環節,更是理所當然要盈利的。出版機構可以根據讀者需求將數據平臺上的部分圖書做成紙質書,以迎合讀者的閱讀習慣,只不過這不是批量印刷,而是個性化服務,其收取的是服務的價格;也可以通過APP帶動一系列相關內容的營銷;還可以通過連載、下載的方式為讀者提供服務等等。
總之,數字化出版盈利模式多種多樣,跟傳統出版大相徑庭,需要出版機構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一邊前進一邊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