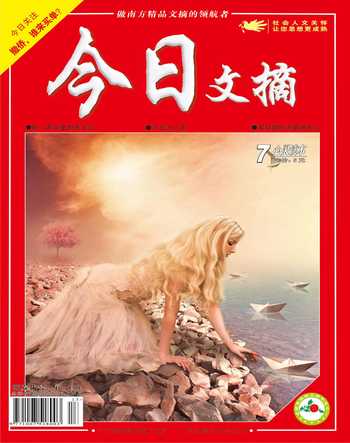最壞的時(shí)光最好的人
筱懿
她是我身邊難得的理科女性,做事干脆、直接、果斷,從不向我傾訴自己的情感糾結(jié),永遠(yuǎn)開(kāi)朗、豁達(dá)、直視世界。直到有一天我實(shí)在按捺不住,萬(wàn)分好奇地問(wèn)她:“你真的從不糾結(jié)?”
于是,我第一次聽(tīng)她講述了自己的經(jīng)歷。
我和老公都是情感上比較遲鈍的理科生,一起走過(guò)從大學(xué)到現(xiàn)在的14年。
14年里,我在美國(guó)工作兩年,周游世界兩年,獨(dú)自在上海做項(xiàng)目3年,兩地分居的時(shí)間總共有7年,中間經(jīng)歷了若干次考驗(yàn)。
在美國(guó)的時(shí)候,我們還沒(méi)結(jié)婚,為了省錢(qián),兩年里他來(lái)看過(guò)我兩次,我回國(guó)看過(guò)他一次,其余的時(shí)間天天在網(wǎng)上聊天。我回國(guó)那次,意外在他衣柜里發(fā)現(xiàn)兩套女士?jī)?nèi)衣,不是新的,而是折疊整齊放在衣櫥的角落。我拿著內(nèi)衣問(wèn)他:“這是什么?”
他表情尷尬,居然回答:“我在外面撿的。”
你瞧,一個(gè)技術(shù)型理工男連撒個(gè)謊都不會(huì),我被他氣笑了,大聲說(shuō):“我寧愿你和別的女人上床,也不愿你是個(gè)盜竊型異裝癖!”
他也被我說(shuō)笑了,撓了半天頭,盯著地板,然后,我們一起把內(nèi)衣扔掉了。
我從來(lái)不去想穿那套內(nèi)衣的女人是個(gè)怎樣的人,三圍多少,臉蛋如何,我不想知道任何細(xì)節(jié)。我只知道,一個(gè)兩地分居的男人有正常需求,而且我們不想分開(kāi),我們這些年的感情擔(dān)得起一個(gè)人的本能。
我們從不提這件事,就像它從來(lái)沒(méi)有發(fā)生過(guò)一樣。這是第一次考驗(yàn),之后我們依舊在一起。
我在上海做項(xiàng)目時(shí)風(fēng)生水起事事順利,正當(dāng)信心滿滿躊躇滿志時(shí),卻出事了——我在出差途中遭遇了連環(huán)車(chē)禍。當(dāng)時(shí)交通擁堵,車(chē)輛進(jìn)不來(lái)也出不去,那時(shí),我懷孕兩個(gè)月。
我感覺(jué)血像一條細(xì)細(xì)的線從身體里源源不斷淌出來(lái),又像沒(méi)有關(guān)的水龍頭,順著腿往下滴,臉上劇痛,滿臉是血,周?chē)艘惨粯印N覈樀脦缀鯖](méi)有知覺(jué),看著車(chē)窗外到處是驚恐的人,不知道什么時(shí)候才會(huì)有救護(hù)車(chē)進(jìn)來(lái),把我送到醫(yī)院。
再次清醒的時(shí)候,我已經(jīng)在醫(yī)院里,身邊是他和我的老板,他握著我的手。
老板說(shuō):“你快點(diǎn)兒好起來(lái),我給你加薪30%,再給你一個(gè)小組管!”這是我下一步的職業(yè)規(guī)劃,也幾乎是一個(gè)女人在這個(gè)行業(yè)里所能走到的頂峰,沒(méi)想到意外達(dá)成,可我并不雀躍。
而他,握著我的手,摸著我被繃帶裹住的臉,撇了撇嘴:“孩子沒(méi)了,你臉上肯定會(huì)留疤。可是,有沒(méi)有孩子有沒(méi)有疤,我們都在一起。”我撲到他懷里放聲大哭,最壞的時(shí)候有他陪伴,夠了。
住院期間,難得有大把時(shí)間想想我和他的那些年。大學(xué)里我們相識(shí),吃校門(mén)口5毛錢(qián)一串的羊肉串;我去美國(guó)工作,連父母都要我抓緊攢錢(qián)回國(guó)買(mǎi)房子,只有他支持我用這些錢(qián)窮游世界,說(shuō)未來(lái)很久的人生都可以賺錢(qián),想看世界的心境或許只有這兩年。于是,我在各國(guó)行走,由著性子生活,他由著我,只要求每天早晚報(bào)平安。他說(shuō),知道我安全就放心了。
我曾經(jīng)覺(jué)得每天“早安”“晚安”很累贅,當(dāng)我躺在醫(yī)院的床上才體悟到,這是連接我和他的密碼,比“我愛(ài)你”更平實(shí)可貴。車(chē)禍讓我們真正成為彼此的親人。
大學(xué)時(shí),他父親去世了,我們的女兒3歲時(shí),他的母親再婚。我原來(lái)覺(jué)得這沒(méi)什么,老年人找到伴侶應(yīng)該祝福,直到參加完婆婆的婚禮,他回到家一言不發(fā)。
我蹭到他身邊問(wèn)怎么了。他眼圈突然紅起來(lái),說(shuō):“雖然為媽媽高興,可是,我再也沒(méi)有原生家庭了。”
我突然特別心疼他,把女兒抱過(guò)來(lái)放到他腿上,摟著他們倆:“這就是我們?nèi)谥业脑彝ァ!?/p>
從那時(shí)起,我心里特別踏實(shí),確信自己有一個(gè)普通而幸福的家庭,確信他無(wú)論做什么,我都能陪伴和原諒。
我們共同經(jīng)歷了那些最壞的時(shí)刻,卻依舊在一起,這就是最好的事,也是最重要的事。
聽(tīng)完她的講述,看著陽(yáng)光透過(guò)咖啡館的玻璃窗均勻地灑在她臉上,心里覺(jué)得安靜而溫暖。可我依舊忍不住八卦一句:“后來(lái)的那么多年,你真的沒(méi)有一次想問(wèn)問(wèn)那兩套內(nèi)衣的主人?”
她微笑:“為什么要問(wèn)呢?在難得孩子不吵不鬧,我們花前月下情投意合的時(shí)候,煞風(fēng)景地來(lái)一句:‘嘿,說(shuō)說(shuō)你和別的女人上床的故事吧?無(wú)厘頭地把現(xiàn)實(shí)的美好一巴掌打碎?只要想在一起,就別瞎折騰,一個(gè)負(fù)責(zé)解決,一個(gè)負(fù)責(zé)遺忘。”
我們經(jīng)常糾結(jié)要和怎樣的人共同生活,或者身邊的這個(gè)人夠不夠好,實(shí)際上,最好的那個(gè)人,往往是能夠陪伴我們度過(guò)最壞的時(shí)光的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