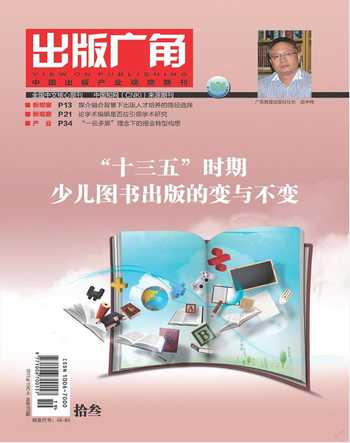淺議湯亭亭《女勇士》中的創傷敘事
【摘要】《女勇士》是美國華裔作家湯亭亭的第一部作品。作者在《女勇士》中通過創傷敘事對女性身體進行了動態建構,為擺脫創傷影響提供了有效的心理距離,將不可敘述的事情用隱喻的敘事策略表現出來。同時,讀書通過作者與讀者的反應來消解創傷體驗,并通過對抗記憶重構歷史,重塑我國女性形象,引領華裔女性走出創傷。
【關鍵詞】湯亭亭;女勇士;創傷敘事;女性身體
【作者單位】趙越,哈爾濱學院。
【基金項目】黑龍江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項目“身體社會學視閾下的湯亭亭作品研究”成果之一。
湯亭亭的作品《女勇士》作為其代表作,震撼了當時的美國文學界,它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華裔美國文學的地位,而且與其后續出版的《中國佬》《孫行者》《第五和平書》等一起贏得了當時評論界的好評。之后,眾多學者從女性主義、敘事策略等方面解析《女勇士》,關注華裔女性的種族、文化、社會身份以及作品中呈現出的多種敘事策略。學者詹妮弗·格里菲思(Jennifer Griffiths)認為,《女勇士》代表了華裔女性的寫作水平,這部作品體現的是創傷的再現與和解;學者胡曉玲從創傷敘事角度,探討了女性的情感欲望。可見,創傷敘事是少數族裔特別是邊緣化的女性寫作的內驅動力。湯亭亭在訪談中曾說道:“我在作品里力求捕捉講故事的流動性。”《女勇士》不僅符合現代主義文學的特點,而且作者試圖用中國的思維模式再現華裔的成長歷程。
一、《女勇士》的創傷敘事策略
1.創傷敘事通常呈現出時間的延遲和非線性的敘述進程。創傷事件與創傷敘述有時間延遲,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敘述者對記憶的修改和見證。《女勇士》中的故事與湯亭亭生活的時代跨度很大,書中看似并無關聯的故事,充滿了共同的集體創傷與焦慮。從“無名姑姑”(1924年的第一代移民)、母親勇蘭、姨媽月蘭以及“我”的童年故事展開,敘述者真實再現的是情感,至于歷史事件是否真實已經不作為重要考慮因素。
正如同創傷記憶的特點是非線性的,湯亭亭在回顧、書寫時,也呈現出復線的敘事模式。她總是試圖從創傷的敘事中,用想象的經歷超越記憶——如在“白虎山學道”和“羌笛野曲”中,華裔女性終于突破壓抑的心理。湯亭亭為讀者提供一個創傷與解脫的心理距離,欲借創傷敘事的延遲性,消除創傷的毀滅性影響。
2.敘述者通過傾聽創傷回憶的敘述呈現出存在的確定性。《女勇士》中,故事的聽者是不確定的,所以該書在敘事過程中并沒有主觀設定聽者。在創傷與體驗中,不確定聽者的內心反應與重構消解了創傷本身。同時,敘述者在心理上抗拒或隔絕創傷,這種對創傷的反應消除了部分創傷的影響和傳承。作品中到處可見一個叛逆女孩與母親說教的強烈對抗。湯亭亭在重現創傷的同時,也在力求隔絕和消解它。
3.創傷敘事創造了“對抗記憶”。湯亭亭在談創作時曾說,把花木蘭和岳飛故事糅合是為了體現女性的力量,并在作品中混合使用東西方神話。作為華裔女性,她揭示出充滿創傷的歷史,并用主體創傷敘事來重新構建歷史。在敘事進程中,她糅合虛構的情節對抗歷史,正如在“羌笛野曲”中的“割舌筋”情節,把華裔對語言的集體創傷與焦慮重新再現,并從中自我復原成為集體建構的歷史記憶。在敘事角度上,她植入了現代話語的力量,使創傷在敘事進程中被評論和改寫,使受創傷者在不同意識層面出現,湯亭亭通過講述與傳達的過程,走出創傷。
二、女性身體表達出的創傷記憶
身體不僅是人類生理意義上的存在基礎,而且在文學作品中具有多重象征意義。《女勇士》就是通過“無名姑姑”身體表達出創傷記憶的。
學者亨克 (Suzette A Henke)、維茨(Deborah Horvitz)、 魯特(Maria Root)等都曾深入研究創傷與女性身體寫作的內涵,探究了文化傳承中女性作為故事敘述者的必要性,并提出:在對故事重復的傳承中,說者和聽者都能夠產生“重復的愉悅”感受。湯亭亭在《女勇士》中用女性身體敘述來呈現創傷的記憶,并在敘述過程中對創傷進行再現、植入現代話語建構,試圖把女性身體從集體焦慮與暴力符號中解脫出來。在該書序言中,湯亭亭表示,這兩本書掏空了她的家史和故事,書中內容是通過她的童年回憶逐漸展開的,通過母親的口述故事,帶給現代華裔女性的是來自遙遠的、傳統的創傷記憶。湯亭亭在書的開頭寫道:“作為華裔美國人,當你們希望了解在你們身上還有哪些中國特征時,你們怎樣把童年、貧困、愚蠢、家庭、用故事教育你們成長的母親等特殊性與中國事物區分開來?”
魯特(Root)認為,通過回憶家族故事并向下一代傳承的方式以及下一代人的反應與行為,體現“未解決的創傷”,產生沖突或超越敘述者的意圖。湯亭亭在重述“無名姑姑”的故事時就超越了傳承故事的內容。由于“無名姑姑”所處的年代,父權社會中的女性無從反抗男性的壓迫,恐懼、被控制,是她通奸的無奈之舉。“無名姑姑”生活在一個拘謹的時代,美是奢侈的,她卻渴望通過“梳妝打扮” “別具一格的發髻” “不會對這種普通的美麗感到滿足”,在“把性欲表征隱藏起來”的社會中,她“渴望著有個情人”。
湯亭亭在“無名姑姑”創傷敘事的進程中,糅雜了部分虛構的內容,在創傷記憶中加入了后代敘述者的聲音。“無名姑姑”死后成為淹死鬼,伺機把人拉下水,從這一點來看,作品中“無名姑姑”從女性受害者變成了有力量的復仇者。通過敘述的力量,作者試圖把女性身體從創傷記憶中解脫出來。
三、疾病與創傷敘事
《女勇士》不僅將“身體敘事”的身體作為認識自我的前提,也將女性所遭受的疾病等作為衡量世界、展示世界的另一個角度,通過女性的這類遭遇,更準確地呈現了所處大環境和女性命運的關系。湯亭亭書中的女性受到的創傷,從精神心理疾病診斷能夠追溯到華裔的真實生存狀況,這在身體上又以疾病的形式體現出來。但這種著眼于創傷與疾病的探討,應加入敘事理論的相關探討。疾病或創傷敘事是現代主義文學敘事的基本特征之一,意識流、疾病或創傷敘述,顛覆了自亞里士多德以來的線性情節關。”
書中眾多華裔女性以瘋癲、失語癥或其他疾病形象呈現,在看似無關的故事敘事過程中,極度渲染和彰顯著疾病的象征性。從更廣義的角度來講,華裔女性受到的是種族、性別、父權的多重壓迫,“我”不明白如何能具有美國女性的美麗,即對無法成為“天使”的華裔女性,呈現出多維度的解讀。
湯亭亭刻畫了許多患歇斯底里癥的女性形象。“在我們附近的幾個街區,有十多個瘋女人和瘋姑娘”;如西宮門外的月蘭、瘋瑪麗、皮亞杰,可能連“我”也是瘋女人。湯亭亭說:“我認為講不講話是正常人與瘋子的區別所在。瘋子從來不會解釋自己的行為。”湯亭亭的女主人公就時常遭受失語癥困擾的痛苦。從“無名姑姑” 的通奸虛構情節到自殺的整個敘述過程中,“姑姑”沒有申辯,沒有控訴,沒有聲音;月蘭姨媽來美尋夫,見到丈夫后就瘋了;“我”從進幼兒園開始,就沉默了;還有我的妹妹、別人家的華人女孩,老師要“我們”進行語言障礙治療,可是到了醫生面前,奇跡般地恢復了正常……諸如此類的種種描寫,恰恰說明了這種所謂的疾病并非是病理上的,而是心理上的一種壓迫。
這樣的疾病敘述,在“羌笛野曲”人物蔡琰的歌聲中被消解,代表華裔女性終將走出“黑色”生存狀態的壓迫。創傷敘事的意圖在于,敘述者在重述的過程中使創傷釋放、修復和再現新的形象。這種敘述手法,值得現代女性文學作家學習和借鑒。
《女勇士》作為華裔美國女作家探索女性價值的一本自傳體小說,作者運用創傷敘事的手法,煞費苦心地發出了當時社會背景下女性沒發出的聲音,揭示了在中美兩種文化沖擊下女性的生存狀態。正如作者所說,作品的力量在于體現了女性的理想和憤怒。站在今天的視角下看《女勇士》這部作品,其對文化差異的撞擊力度之大,以及作者對女性遭受創傷之重的描述,都極大地促進了美籍華人文學的發展,值得現代的女性文學作家去借鑒和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