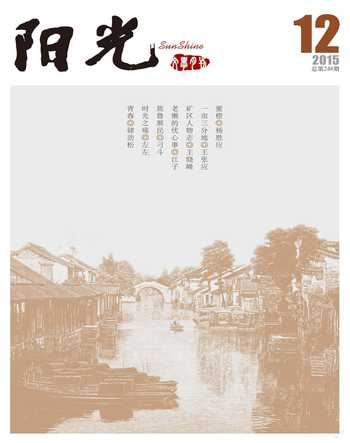青春
二 廠
二廠是我的“發配充軍”之地,也是我人生行旅的一個驛站。
我的畢業派遣證上寫的分配日期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的一個八月,真正被一家縣級國有供水企業接納則是翌年元旦過后。其中的原因和過程頗為復雜,簡言之,公司當年為職工子女就業考慮,委托一所建筑工程類中等專業學校培養六名學生,謂之定向委培生,但他們的子女都不爭氣,考分離錄取線隔了幾座山,于是連我在內六個出身貧寒的農家子弟草窠里撿了個粑,代替職二代們去拿了文憑,又替他們來到公司,準備接手他們父母輩的事業。這自然令公司上下羞慚惱怒,于是公司高層一致決定拒不接納。但在那個時代,派遣證就像尚方寶劍,是不能不認真對待的。結果,公司的主管部門甚至縣政府都被驚動,公司一把手被免職,而我們六匹年輕的狼長驅直入。在工作有了著落之前,那東奔西走到處求爺爺告奶奶甚至準備請律師打官司的凄惶的幾個月,則讓我終生難忘。
梁子早就結下了,而且結得很深,雖然我們都很無辜,但人還未到就命定被列為不受歡迎的人。在六匹狼正式入侵之前,公司做出兩個決定:一是年內不給班上,到元旦過后再正式報到;二是全部放到二廠,公司總部一個不留。關于第一條,后來有人告訴我說,公司是為了節省月獎和年終獎;關于第二條,明里說是為了讓我們到最艱苦的環境中接受鍛煉,將來如何如何,實際上就是發配充軍,說是報復也未嘗不可,因為與我們一道畢業的公司一位高層主管的女兒,并沒有受到接受鍛煉的“特殊優待”,而是上班第一天就直接在公司總部做了辦公室文員。后來我們知道了她也是定向委培事件相關者之一,不得已進了一所技工學校,身份被定性為工人,而我們則赫然是干部。順便說一句,當時整個公司近百號人,在我們進入之前有院校背景的只有幾個人,其他的都是小學或初中文化程度的老職工以及他們的子弟。
二廠就是第二分廠,在離縣城七八公里處的一個鄉鎮,如今那里是一片被稱作縣城副中心的開發熱土,而在二十年前卻是一個荒涼而毫無生氣的小鎮。二廠坐落在鎮子邊緣一座光禿禿的小山上,前不著村后不著店,廠區的幾間青瓦平房還是當年三線廠從大別山大撤退時遺留下來的,早已殘破不堪。那年元旦收假后第一天,六個不滿十九歲的“童子雞”到公司報到,并點頭哈腰地接受了一番堂而皇之的崗前教育,之后一人騎著一輛老永久加重自行車,沿著坑坑洼洼的山區國道,一路呼嘯著從縣城沖向二廠。吹著口哨,沿著百步水泥臺階進到廠區,心情原本不錯,可是望見與公司豪華典雅的總部大相徑庭的荒草叢生蛇鼠出沒的廠區時,我的心頓時掉進了冷水盆里。
從前我個自命不凡的人,胸有鴻鵠之志,不像現在這么灰撲撲地墮落了江湖。雖然只是個中專畢業生,但在高校門禁仍然森嚴的上世紀末,中專生算不上“天之驕子”起碼也能算個“地之驕子”,理想中的上班應當是坐在寬敞明亮的辦公室里寫寫畫畫,而不是當一名工人。原本,當年考取中專的人是學業最優秀的一批人。現實的殘酷性正在如此,它偏偏安排我在破敗的鄉鎮中破敗的小廠里當了一名幾乎不需要任何技能的開水泵的青工,每天枯索地獨坐在密封的機房里,守著一塊電子儀表板,看看上面顯示的電壓、水壓、水塔水位,在紙上作作記錄,再就是擦擦水泵上的灰塵,打掃廠區的衛生,其他時候無事可干。實在說,我頗有藍田之玉落塵沙的不遇感。
起初幾天,我們六個既是同學又是同事的年輕人,一道上白班,跟在老師傅后面學習開水泵,一道下班,回附近的二廠職工宿舍十一號樓吃飯睡覺,只要姓李的那位老師傅不在,幾個人每天嘻嘻哈哈倒也不覺得日子十分難過。
老李是廠里的老桿子,在小字輩面前固然有高高在上的資格,加上我們如同發配寧古塔的罪臣一般,不受公司待見,于是他自以為更有嚴加管束的責任,每每喝得醉醺醺之后,便搖著巨腹坐到我們中間耳提面命。他響亮地叫著我們每一個人的名字,一個不落一人數落一通,都是些雞毛蒜皮不值一提的小事以及莫須有,經他上綱上線,每一件幾乎都足以打發我們回老家。舉個例子,上班頭兩天,我們帶著過去的課本以及文學書到機房里看,與其在機房里無所事事,不如讀讀書增加一些知識,這本應當是受到前輩鼓勵的事,但到他眼里就成了不務正業,于是舉報到廠長那里。還好廠長是個明事理的人,熱情表揚了我們一通,又叫我們不要與他計較。據說后來他又告發到公司經理那里去了,事情不了了之。但這足以讓涉世未深的狼們惶恐多日。還有一件事記憶猶新,春節期間的某一天,我正和老水在機房里吧唧著口水談縣城絲綢廠里的漂亮妹子們,老李突然來了,打著飽嗝兒呼著酒氣,指點我們要尊重老前輩,并詳細告知我們他家的具體方位和行走路線,大約是叫我們去拜年。那時我們年輕氣盛,并未讓他如愿。
接下來就是獨立倒班,那開水泵的活計不是開飛機造火箭,說到底是從街上隨便拉一個人都可以勝任的。廠里的職工本來就只有寥寥十數人,倒班過后,就只剩下當班者一個。水泵在運轉時,廠區里只有淹沒一切的轟鳴聲,一旦水塔水滿機器暫停運轉,就靜得能聽見螞蟻走路。十八九的青春原本熱血,卻被圍困在離地兩百米高不見人煙的山中碉堡里,好比籠中困獸。我常常站在廠區圍墻邊上,面目呆滯空洞地望著前方的那條流向縣城的大河,覺得自己是個被遺棄的人,每天數著秒虛度年華,那河里流的似乎不是水,而是群蟲撓心般的寂寞和憂傷。
白天尚可勉強打發,躺在廠區野草坪上曬曬太陽,看看飛鳥,讀讀古詩,想想心事,一天就慢騰騰地過去了。到了晚上,就很難熬了。幾盞昏黃的白熾燈照著廠區,一個人坐在機房里,望過去就像明滅的鬼火,偶爾一聲鳥叫,能把人嚇得魂飛魄散。刮大風的時候,廠區高高的柏樹被吹得東搖西晃,像人影在出出沒沒。于是想到鬼。那些日子,廠里的幾個青工常在我們面前談鬼,說某一天他們晚上值班,聽見泵房里的凳子被拖得嘩啦嘩啦響,從門縫偷偷往里看,有兩個青面獠牙的老鬼正在拖著板凳干架。又說某一夜,他們看見一群鬼坐在廠區院子里,就著一堆火抽水煙筒。諸如此類。青工們說得有鼻子有眼,當時自然是不信的,可是夜里竟不敢出門,連撒尿也在備好的啤酒瓶子里解決。有一天晚上我值班,金海和發祥這兩個與我關系不錯的老青工偷偷摸進廠來裝鬼,躲在一棵樹下喋喋哇哇地亂叫,把我三魂嚇掉了二魂半,身上汗毛根根豎起。
那年的臘月三十,正好我值班。我早早在家吃過年夜飯,就騎著自行車往二廠趕。漫天的大雪狂亂飛舞,我穿過茫茫雪地和煙花爆竹的熱鬧,把自己鎖進差不多與世隔絕的被大雪靜靜覆蓋的碉堡。我帶著一只微型游戲機,打俄羅斯方塊,從除夕一直打到初一早上八點同事來接班。出廠區大門時才想起廠長年前曾交待我貼春聯,趕忙返回取來對聯胡亂貼上。
馱日子過山頂,說的就是那時我的生存狀態吧。心里一直郁悶、迷茫、倉皇,甚至絕望,不知路在何方,與一個十八歲少年花紅柳綠的夢想遠之又遠,也不知道這樣的日子哪天才是盡頭。多年以后,一位朋友在詩作中這樣寫道:“如果你還在思想,就可能過得比較艱難。”
遠在縣城的公司總部在我心中仿佛圣地,一個可望不可即的天堂,心中最大的愿望就是公司高層慧眼識珠,調我去體體面面地坐辦公室。況且,那里還有幾個與我年齡相仿的姑娘,裝點著我孤獨的瘦夢。直到現在我仍然想問一問,那些在公司總部辦公室里蝴蝶一樣飛來飛去的姑娘,是否明白一匹少年狼當年蝕骨的憂傷?
十一號樓
十一號樓是二廠的職工宿舍,磚混四層,奶黃油漆涂面,上三層有的住人有的空著,底層是廠里辦的并不景氣的三產肥皂廠。十一是它的編號,在小鎮蓮花村千園岙地片,這樣的宿舍樓總共有二十余幢,另外還有許許多多高大的廠房和辦公樓,在當年大別山里那個荒涼的村莊以至整個鎮子,它們是鶴立雞群的村中城,十分搶眼。它們是頗有些來頭的,原是建于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兵工廠長寧機械制造廠,生產軍用雷達。其時蔣介石叫囂著要反攻大陸,美國出兵入侵越南矛頭直指中國,社會主義老大哥蘇聯停止援助撤走專家逼迫還債,國際國內形勢異常復雜,國家從安危考慮,決定搞“三線建設”,并要求各省“搞兵工廠”,于是大別山里這個封閉的小縣,一下子遷移進來五個兵工廠,本地人謂之“五大廠”,職工六千余人,長寧機械制造廠是其中之一。八十年代初,形勢趨好,“五大廠”陸續遷出大別山,所有房產全部移交本地政府并被分作他用,二廠分得原是兵工廠供水站的廠區和宿舍群中的十一號樓。
我只是十一號樓短暫的住客,因為在二廠上班不很久,我就調回了縣城總部,繼續接受鍛煉,做管道工。但我對十一號樓是有特殊感情的,雖然接到調令離開的時候,我仿佛從前謫仙流放遇赦,卷起鋪蓋急吼吼就走了,連回頭望一眼也沒有。
我們住進十一號樓之前,廠長就已經安排人把房間用石灰水重新粉刷了一遍,并購置配備了煤氣灶,給每個人買了一張簡易工人床。六個人除了一個家在本地不住外,五個人分得兩個套間,我和老水、力峰住三樓三號房,文明和顯亞住二樓一號房。在二廠惟一的好處,就是住房比公司總部寬敞,從學校十人一間的擁擠宿舍里搬出來不久,一個月交兩三塊錢就能住到六十多平的房子里,也算是一種驚喜。正式搬進去那天正好單位發工資,六匹狼揣著一把錢就騎著二八大杠呼嘯著往城里奔,買鍋碗瓢盆,買洗換衣裳,買青菜豆腐肉,開始了新的群居生活。
廠里沒有食堂,除了我們幾個,其他有家有室或者雖是單身但開小灶,所以我們自給自足吃伙食團。輪流買菜燒飯洗碗,吃完了往貼在墻上的紙上劃個圈兒,月底結算各自的伙食費。工資不算多,但在小城也的確不算少,只是我們都是農家出身儉省慣了,并不舍得經常吃肉,嘴里長期淡出鳥來,金月、老房這兩位老職工于是隔三差五叫我們去他們家改善伙食,廠長也常常把燒雞烤鵝夾到我們的碗里。十八歲的年紀,吃自然不是最重要的事,個個都有遠大的理想。不當班時,就在房間里下棋、練字、抽煙、扯閑篇,或者看專業書準備自學考試拿大專本科文憑。房間的墻上貼著廉價買來的勵志字幅,“有志者事竟成”,“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諸如此類。閑得發慌時,就結伴去兵工廠的老廠區瞎逛。那里有兵工廠留下的電影院、澡堂、醫院、冰棒房、防空洞、五金倉庫、職工培訓中心等等設施,當然都是遺跡,房子大都空空蕩蕩,門窗被貪小利者拆得七零八落,有一些房子被附近村莊里的農民占去改作了豬圈牛欄雞舍,實在沒什么好看的。不過那里有一個小型的菜市場,還有臺球室,倒也還算熱鬧,最關鍵的是,那里偶爾會有年輕女子出現。
飽暖問題初步解決之后,女人對少年狼突然間具有了無窮的誘惑力。然而二廠陽盛陰衰,只一個女職工而且早已結婚生子,十一號樓周邊那些樓上住的多是鄉鎮企業的青工,他們的女人只能偷偷地望望,縣城又那么遠,城里的女子根本沒有機會結識。幾匹狼可謂如假包換的沒嘗過女人滋味的童男,真實卻又不明就里地渴望著,半夜躺在床上睡不著,扯女人經扯到渾身發熱,第二天掀開床鋪,總能在某匹或幾匹狼的床單上發現可疑的地圖。幾個已婚的老青工,又偏偏愛在我們面前大談男女歡愉之妙,惹得少年狼拼命舌舔干唇。有一天,一名老青工偷偷帶著正在戀愛中的女朋友溜到十一號樓過夜,據說還把單薄的工人床弄出了不小的動靜。這原本是件幽密的事,可是第二天一大早,向來有些邋遢的他忽然把被單洗了晾曬在陽臺上,暴露了秘密,經一名過來人竊笑著指點,十一號樓忽然間有了曖昧的意味。那夜的床談因之多了些知其所以然卻不知其然的探討,那夜的清夢因之更多了些朦朧和焦渴。然而女人都在城里,女人遠在天邊。
如同一樹李子,雖是一同開花一同結果,果子卻有早熟遲熟之分。上班不長時間,在另幾匹狼還在不著邊際地過嘴癮時,文明和老水私下里已經在結伙搜尋目標了。一個初春之夜,這兩個家伙背著我們從縣城絲綢廠馱回兩個妹子,去二廠廠區喝酒。據說其中一個長發飄飄長得很像其時正紅的歌星周慧敏。據說那晚他們喝了整整一捆啤酒,然后又騎著車一人車屁股后面馱一個,跑到縣城大河的沙洲上談戀愛。還是據說,據老水說當晚下著雨,老水和他帶的那個妹子早早散了,而文明和小周慧敏摟抱著躺在沙洲上,冒雨一直交流到下夜三四點。事發后,這二位尤其是始作俑者文明受到另幾匹狼激烈地聲討,被迫請喝了一場啤酒了事。每個人包括老水都巴巴地探他的口風:“你這個雜種,到底搞到手沒有?”文明這哥們兒卻既不承認也不否認,只管一味奸詐地壞笑,酒喝得夠高了,笑得頭都埋到褲襠里了,仍然沒套出什么實質性的話來。只透露說隨便摸了,至于摸了哪里,怎么摸的,摸到了什么,問了一百遍,硬是屁也不放一個。這事當年是個謎,而且必然是個永久的謎,因為一年多前文明就在一起交通事故中永遠閉上了那雙炯炯又壞壞的眼睛。去年底他的祭日,幾個當年躊躇滿志的少年狼而今灰頭土臉的中年貓相約了,驅車數十里山路,去他老家背后山坡上給他燒紙,我們還在問:“文明你這狗日的,當年到底搞到手沒有?文明你這混蛋,怎么丟下父母妻兒一個人跑到陰間享清福了?”
一周只用上兩三個清閑的既不用動腦也幾乎不用動手的班,如果不時刻想著到公司總部去高就,并且不想女人的時候,十一號樓里的光陰還是很閑散的。陽光總是很好,我也總是喜歡坐在陽臺上給過去的同學寫信,無非是現實的工作生活和空而又遠的理想,重復來重復去的相互不厭其煩。或者讀書,寫寫日記,與在廠區碉堡里一個人心事滿腹黯然神傷相比,十一號樓多了些人間煙火味。
二廠的職工差不多有一半是原來兵工廠的遺民,也是鎮子上的原住民,十一號樓里之前其實只住著幾個同事以及他們的家屬。廠長姓程,是廠里最大的也是惟一的官,自然也是十一號樓的樓長。是個矮壯謝頂的半老頭兒,早年離異,帶大兒子過,大兒子與我們一道從學校畢業,分在縣城里公司辦的三產一個小機械廠當車工,并不常回來,所以等于是獨居。他是個極愛整潔的人,廠區和十一號樓因之幾乎一塵不染,也是一個十分講原則的人,老職工并不敬他甚至還老在我們面前說他的不是,然而他對我們卻仿佛嚴父,生活中悉心關照,工作上嚴格要求,為人處世方面也經常提點。那些日子,他經常寬慰我說:“是金子總會發光的。”雖然不免空洞,于我卻也是希望和安慰,并且我的調動,他也的確是在公司經理面前說過不少好話。他還對我說過:“你性格清高又倔犟,將來可能要為此多吃些苦頭。”后來也都應驗了。
二廠惟一的女同事胖胖憨憨的金月,是我們名副其實的大姐。家里有好吃的必定老海碗裝了送來,我們的被子臟了她必然拆了洗好再做好,我從十一號樓搬走的那天,天剛好下著小雨,我都敞著頭騎車出門了,她還攆上來送給我一件紫色的塑料雨衣。她的丈夫與我同宗,在一所偏遠的鄉村中學教英語,也是個人緣極好的人。好些年以后,我早已從公司調出當了一名記者,在一個鄉鎮采訪吃飯時偶然遇見他們,我恭恭敬敬陪了他們夫妻倆一杯酒。人生行旅中遇見的這些好人,是應當銘記并終生感激的,雖然那些事他們早就忘了。
十一號樓我近二十年沒去過了,不知道三樓三號房墻壁上,我當年用鉛筆給想象中的情人寫的詩還在不在?
安裝隊
我承認,十八九歲時我有著一架與自身資歷、閱歷和能力極不相稱的瘦硬的骨頭,也就是廠長所說的清高又倔犟。并且這種瘦硬一目了然,像草標一樣隨時出賣著我,讓我為此付出代價。我不是為此檢討或是感到羞愧,青春原本就應當是一把青霜劍,而不是一根蔫黃瓜,即使不是刺傷別人就是刺傷自己。如果時光倒流,我想我仍然會不計后果地在脖子上插一根草標。只是有點兒不巧的是,新任的公司經理也是一根亮晶晶的麥芒。
到二廠上班后不久的一天早晨,廠長召集所有職工開了個短會,主題是迎接新任經理到二廠視察。新經理比我們遲三天到公司,是第一次來二廠,對于全體職工來說自然是天大的事。廠長一聲令下,整個廠區頓時如臨節慶,擦桌子,掃機房,除雜草,掛橫幅,在忙活了一個多小時又齊刷刷站在圍墻邊眼巴巴望著通往山腳的水泥臺階個把鐘頭后,經理終于在公司部分高層的簇擁下蒞臨廠區。是個三十出頭的年輕人,瘦削,黑臉,目光凌厲,眉宇間有殺氣,眼掃到我時,我身上感到涼。據說是從建設局放下來重用的。夾道鼓掌歡迎之后,頭頭們擠在簡陋而整飭的廠辦開了個短會,隨后經理分別找職工單獨談話了解情況。新官上任,這些原不過是履行程序。但待經理走后,廠長忽然對我們幾個人說,新經理此行有考察我們幾個中專生的素質、準備調一兩個人去公司總部的用意。廠長話未落音,我骨頭都涼了。
“公司安排你們到二廠基層鍛煉,對此你有什么想法?”擱在二十年后的今天,冠冕堂皇大而無當的虛話我張口就來,可當時我說:“我認為是浪費人才,公司職工整體文化素質不高,應當把我們分布到各部門充實力量。”經理兩道眉往中間擠了擠。“專業之外,你有什么特長?”“我會寫作,會吹口琴,會彈吉他,會寫美術字,會主持晚會。”經理的臉上起了烏云,順手拿了一本雜志看。“你認為,怎樣才能增加二廠的供水量?”“自來水最大的用戶是企業,所以我認為首要的是扶持鄉鎮企業發展。”“怎么扶持?”“……”我語塞,然后很不靠譜地東扯西拉。經理把雜志往桌子上一扔說:“好,你可以出去了。”
經理走后,廠長悄悄對我說:“經理對你印象好像不是太好……本來公司認為你是個不錯的苗子,唉!”隨后的那些日子,我站在廠區圍墻邊看河水東流的次數更多了。
然而幾個月后,公司突然下了一紙調令,調我和文明到公司總部工作。廠長把蓋著鮮紅公司大印的文件遞到我手上時,就像打入冷宮多年的妃子重被召幸,我激動得發抖。嗚啦!
我和文明被分在公司的給排水工程安裝隊,做管道工,而不是坐辦公室。公司一位高層找我們談話時說,這是讓我們繼續接受鍛煉,但并沒有說明這鍛煉的時間是幾個月還是幾年。這叫我喪氣。后來有人告訴我,經理說我頭上長角,得狠狠地磨磨。
我穿著廉價的西裝,用二八大杠馱著笨重的管道套絲機、三角架,肩上扛著管子鉗、鐵錘、扳手、水龍頭、彎頭、束接、閘閥這些死沉的鐵器家伙,跟著老胡走街串巷,給用戶安裝水管子。我家住城郊,這個小城里有我太多的熟人,于是我盡量把頭低著,怕他們看見了笑話,一個念了書回來的人干著出苦力的營生,畢竟不是什么榮耀的事。當初中考的時候,全縣數千名考生我考分排前十,因而才得以走中專,錄取通知書到達的那天,家里擺了七八桌酒席,其榮耀遠勝于今天學子考上重點大學,遠親近鄰則把我當作他們教子的榜樣。
我沒臉見人。事實上,我家下屋的一位婆娘就跟她的三個兒子說:“念書有么屁用,你看上屋勁松,念那么多書把家都念空了,回來還不照樣出蠻力。”她家的三個兒子后來果然都沒念書,早早當建筑包工頭或做生意去了。
老胡是我師傅,年紀與我父親相仿,是個五大三粗的忠厚人,言語不多而詼諧,不如那些嘴滑的討頭頭們喜歡。他耐心地教我測量、套絲、安裝。然而我不肯學,不是把套絲機弄壞了勞煩他修理,就是把水龍頭擰斷了惹用戶不高興,還把工具往地上摜得嘩啦響。師傅脾氣好,從不惱,他總是慢條絲理地吸完一根煙,把煙屁股砸到地上,咕咚咚喝完一碗茶,捋一把滿臉的絡腮胡子,然后起身一個人忙活,只叫我幫他拿拿工具。在安裝隊隊長面前,也從不說于我不利的話。文明雖然比我務實賣力多了,他的師傅卻常常在隊長面前打他的小報告。在公司八年,我做過多次學徒,但我只承認老胡是我師傅,雖然他一流的管道工技藝我幾乎什么也沒學會。
那年夏天縣城東區大改造,地下所有的供水管道全部改線,安裝隊十幾名隊員全體上陣。鋪設口徑兩米的鑄鐵管道是地道的力氣活,光幾百個接頭就是浩大的工程量。幾個臨時請的小工負責抬管子,老師傅們負責技術,我和文明以及另兩個學徒衛東和王進打下手,用鋼鋸鋸管子,用手和膨脹水泥。死熱的天,敞著頭暴曬,一天身上脫一層皮,和水泥的手爛得大窟窿小眼。一天上午,公司經理開著小車來巡視工程進展,正好站在我和衛東邊上。我和衛東坐在沙土上,一邊兩手插在盆里撲噠撲噠地和水泥,一邊滿嘴跑火車,不像其他人噤若寒蟬。經理居高臨下地望著我倆,皺著眉毛,一臉慍色。衛東向我使了個眼色,我會意,四只手在盆里胡亂一頓撲騰,經理锃亮的皮鞋被水泥濺了個滿天星。
秋天的時候,公司舉行管道安裝大比武,要求安裝隊所有隊員全部參加,師傅帶徒弟,倆人一組。比武場設在公司大院里,七個三角架一字排開,每組各顯其能,公司高層以及辦公室的幾只蝴蝶站在二樓走廊上觀戰。后來,他們又走到院中督戰。老胡手腳如飛之余,扯起一根用于防漏的油浸麻絲,舉起來對觀戰者說:“你們看看,像不像大經帶?”比武場上頓時笑翻,幾只蝴蝶花容失色,經理原本興致勃勃,這時臉頓時往下一拉。然而老胡是元老級別的老桿子,又從無謀個一官半職的野心,經理對他也無可奈何,于是轉而批評他的徒弟技藝生疏,徒弟無能師傅有錯。我發了血性,把手里的管子鉗往經理腳下哐當一扔,國罵一句,“比他媽個×!”說完我就從車棚推出二八大杠,騙身上馬,揚長而去。
據說當天的比武不歡而散,經理極為震怒,在辦公室砸了茶杯。第二天下午,公司的一位副經理在門口看見我,語重心長地說:“小儲你是個好苗子,不過要學會能屈能伸。”我默然,心里盛滿感激。后來的一段日子,我好像沒有冒犯過任何人。
其間,公司搞技改、建水塔、辦元旦晚會、搞文明創建,經理親自安排我做過幾次寫寫畫畫或者監工的事,每次我都全力以赴。經理對別人說過,儲勁松那小子是有點兒才。每回活計結束,我都巴望著經理能夠加以委任,起碼調離安裝隊,但我一次次失望。
第二年春節大初二,我拎著煙酒到經理家拜年,本心也存著套套近乎的念頭,更想問問什么時候結束鍛煉。然而在他家的沙發上我如坐針氈,直到飛一樣地逃離,什么也沒套什么也沒問。經理也只顧專心喝他的功夫茶,肚子里肯定是熱的,但他什么體己的熱乎話也沒說。
我在安裝隊待了一年零五個月,這才調到生產技術科做了科員,如愿坐上了辦公室。那已是又一任新經理手上的事了,也就是之前勸誡過我的那位副經理,并不老的老經理被東區管道改造工程絆倒了。平心而論,他是個有水平有能力的人,公司在他手上蒸蒸日上,我不喜歡他,主要還是因為他是一根麥芒。后來幾個月我還夢到過他兩三次,不是什么好夢,內容也大致差不多:他胡漢三又殺回來了,重新坐在經理寶座上,黑著臉打發我回了安裝隊。
儲勁松:1970年代生于安徽岳西。現供職于某宣傳部門。出版有《黑夜筆記》《書魚記——漫談中國志怪小說及其他》《風霜冷白》等多種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