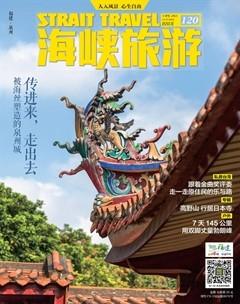下海,是一種態度
林翰
1974年,在泉州灣后渚港的海灘上,一艘700多年前的中國海船驚現于世。這是一艘13世紀泉州造的三桅遠洋商船,運載著大量香料藥物從東南亞歸來。這艘宋船的出現,不僅使許多先進的傳統造船技藝如水密隔艙等得到了實物印證,更使古代文獻上關于泉州是中古時期重要的國際性港口,與東南亞各國及印度洋沿岸國家頻繁貿易往來的記載得到證實。
七百多年前,這艘宋船是如何沉沒的?沉沒的原因是什么?是遭遇風浪還是宋元交替時戰火蔓延,船主還來不及出售貨物就倉皇逃命,還是有其他原因?這些我們現在已無從知曉,不過像這艘商船一樣,歷史上泉州木帆船往來于南中國海的帆影就不曾消失過,即使是在海禁最為嚴厲的明清兩朝。因為對于泉州漁民與船商來說,搏擊海浪是一種宿命;下海,是一種態度。
從中古時期開始,泉州海商逐漸成為海上絲綢之路上一股強大的貿易力量。正如新加坡學者王賡武先生指出,五代以后,中國海交史上最顯著的發展乃是“泉州時代的到來”,“閩南人在中國沿海作為一種連貫的貿易力量出現的時間,比葡萄牙人在歐洲沿海出現的時間還早。”以安平商人為代表的泉州海商,行商范圍廣泛,足跡遍及大江南北,而且與海外國家交流密切,“貿海則文身之地,雕題之國,無所不至”。現在在東南亞國家中,菲律賓華裔商人以泉州群體為最多,這與明清以來泉州海商的經貿傳統有極大關聯,史稱:“安平之俗好行賈,自呂宋交易之路通,浮大海趨利,十家而九”。
在地理大發現以后,尤其是大航海時代的到來,世界貿易體系日漸形成,泉州海商更是在跨國貿易中大顯身手。我們無法想象,在歷史上如果東南亞貿易中缺少泉州人的身影會是一種怎么樣的景象。由于西班牙人跟葡萄牙人無法與中國政府進行直接貿易,只能將從美洲及日本運來的白銀轉運至菲律賓群島和馬六甲、澳門,然后經由中國海商做轉手貿易。漳泉海商從中國運來西方世界渴望的瓷器、絲綢、茶葉等商品,隨后又將換取的白銀源源不斷地運往中國。也正是大量的白銀輸入,中國一種新的財政體制由此逐漸形成;與此同時,白銀作為基本的計量單位和支付物,也改變了傳統中國地方政府與中央朝廷的關系。
在十六世紀中期以前,到東南亞進行海外貿易的大多數福建海商并沒打算在當地久留,很多還是作候鳥式遷徙,做完買賣就回歸故鄉。不過我們也應看到,明初的海禁政策對泉州海商來說是災難性的,外國商船不能抵達中國口岸,中國也限制本土海商出洋貿易 ,那些為求生計鋌而走險的海商有國難回,在異國他鄉又得不到帝國的庇護,最終只能成為“沒有帝國的商人”。正是在這樣的境況下,他們只能依靠自己的才智謀生,也培養起“愛拼敢贏”的泉州精神。
泉州海商作為定居性移民基本要在明代以后,而對于清代中后期大部分下南洋的泉州人來說,“過番”有時卻是一種無可奈何的選擇。19世紀末、20世紀初廣泛流傳于閩南、臺灣及東南亞華人社區的一部閩南方言長篇說唱詩《過番歌》,講述的是一個安溪貧苦農民離鄉別親,遠涉重洋到番邦謀生,途中被思親情愫縈繞與抵達番邦后謀生遭遇的困頓,最后因謀生不易而失望返歸原鄉的故事。文化差異、身份認同、在地融合或回歸故里,是那個時代下南洋的移民群體所遭遇的普遍問題。有的返歸原鄉,困守故土;有的客死旅途,葬身海上;也有的留在異國他鄉,與當地土著融合。無論作出哪種選擇,都反映出當時海外移民的一個側面。
當然,我們還應看到,泉州海商在海上絲綢之路上不僅運銷貨物,同時也促進了中國與世界各地文化的交融。以泉州海商往來最為頻繁的南洋來說,伴隨著泉州海外移民的出現,泉州先民也將中國的冶煉技術、造船工藝、種植方式、制瓷方法帶到當地;除此之外,泉州本土的傳統民間信仰、生活禮俗、飲食習慣、戲曲音樂等也被帶到移民地區,并與當地土著文化發生碰撞與交融。
泉州人在移民在地化的過程中,也參與到華人群體與馬來土著的融合過程,成為“峇峇”次族群中的一股力量。早期移民馬來半島的華人娶了在地女子為妻,所生子女在日常生活中所講語言以峇峇馬來語和英語為主,所著服飾及所吃的飲食也都逐漸本土化,學者也將這些本土化的華人男性稱之為“峇峇(Baba)”,將女性稱為“娘惹(Nyonya)”。當然,這個過程是緩慢的,對于華人來說是交融了,對于在地土著來說,也標志著新生族群的誕生。從南洋竹枝詞的吟唱中,我們尚能看到海外移民對原鄉文化的固守,以及對故土的思念:
一聲爆竹響昏昏,異域猶將正朔遵。
中外一家同迓歲,桃符紅遍貼春門。
浮杯酒味入新年,旅客孤單恨萬千。
兩袖清風猶故我,不如及早整歸鞭。
雖然移居東南亞的泉州人已在不同程度在地化,但仍保留著過中國傳統節日的習慣,對于故鄉的梨園戲也仍念念不忘,當地僑民還為此結為社團進行排練,傳承并推廣閩南戲曲。而華文書院與學校的創辦,也為傳承中國傳統文化與故鄉觀念起到促進作用,上引竹枝詞提到的萃英書院,就是由泉籍華僑陳金聲籌款創辦的,這也是新加坡最早的華文教育機構。
泉州海商在跨海下洋的過程中,伴隨著人員的流動,也將原鄉的宗教信仰帶到異邦他鄉,這也為他們在新的環境中提供精神上的寄托。像馬來西亞檳城的清水祖師廟、印尼文登的清水祖師廟都是由安溪清水巖分靈設立,新加坡鳳山寺、馬來西亞古晉鳳山寺均是從泉州南安詩山分香過去的,新加坡通淮關帝廟也是從泉州通淮關岳廟分香的,馬來西亞聚星堂關帝廟于1954年由泉籍華人發起興建。共同的信仰不僅成為海外泉州人與原鄉密切聯系的紐帶,更是族群內部聯系的載體。
作為人員來源身份表征的方言也對當地產生影響,馬來語中就有許多詞匯是借用閩南方言發音的,如面線(misoa)、米粉(mihun)、豆腐(tahu)、紅包(angpau)、醫生(sense)等等。當然,這種影響也是相互的,泉州本地將肥皂稱為“雪文”,把水泥稱為“洋灰”或“紅毛灰”,將運動場上球類比賽的出界叫“歐賽”,把手杖叫“洞葛”,將雪茄叫做“朱律”,把氈帽叫“招瓢”,把咖啡稱為“哥卑”,把朱古力叫“則龜力”,把煤油稱為“番油”,把華僑與僑居國結婚的婦女稱為“番婆”等,這些都是外來語言對本地方言的影響。
從中國的東南到亞洲的東南,泉州人一路遷徙。在這片充滿夢想、機遇與變數的土地上,泉州人與當地土著、曾經的殖民者、還有來自不同地域的華人群體,從最初的打交道,再到行業的競爭,以及行為方式的磨合;更為微妙的是不同文化間的碰撞,相互妥協,再到有機交融。在這一漫長的過程中也演繹著許許多多的故事,我們所能捕捉到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通過對這吉光片羽的拼接,雖不能完整重現移民社會的整個面相,卻尚能為我們提供多個維度且可供解讀的歷史片段,而這些卻也是泉州人在東南亞的真實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