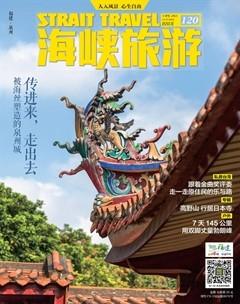路上有宵夜
尼佬
旅行的宿命,便是居無定所,食無定時。所以當我們每次車船勞頓又饑腸轆轆時,就會希望自己身處東亞或者東南亞,那個二十四小時運轉的世界啊,只要有幾個銅板,什么時候也不會餓到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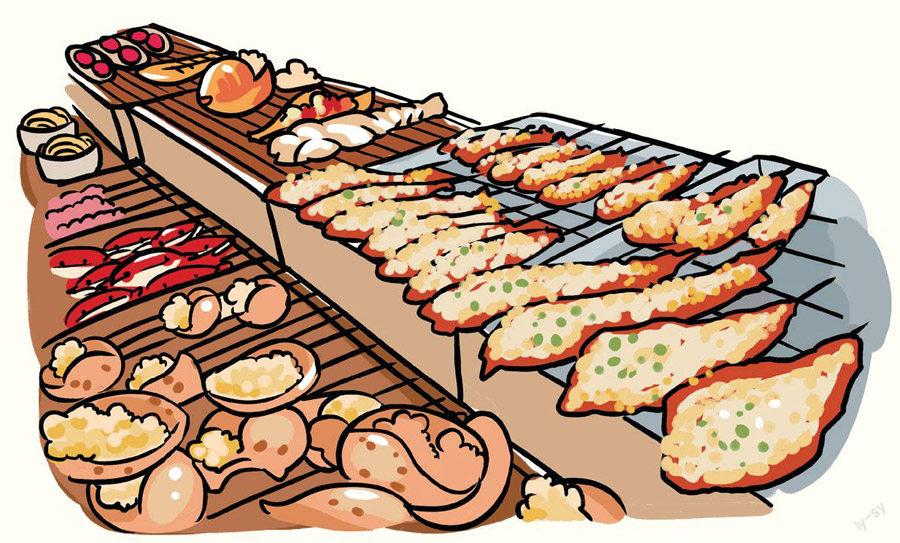
臺灣就是這樣,而且奇妙地集合了大陸、日本和東南亞的夜晚精華。我對山水和城市的景觀記憶已經模糊,卻依然記得臺灣的夜食。
第一次到臺北,住在西門町旁,沖個澡后開始步行臺北,已是八點半。從淡水河邊,穿過西門町,跑步穿行二二八公園,四月末的臺北夜晚舒適清涼,二二八公園沒有密林,大王椰禿驢般的頭顱沖向城市的夜空,毫無遮掩。將出門時,看到幾個和白先勇先生一樣年紀的革命先烈依然坐在月下攜手相談,也算和睦結局吧。
穿過臺大醫院繼續走,永康街到師大,看燈火街旁,居民在路邊小公園里做下蹲運動鍛煉。順路吃了舒國治做廣告的大腸面線,加了蚵仔,點了醋,是我喜歡的味道。一路熱熱鬧鬧,學生喜歡的炸物居多,還看到兩家令我倍感親切的云南館子,有一家叫“伊洛瓦底”,大致就是緬甸的騰沖籍華僑菜罷,大薄片、水腌菜、豌豆粉加上泰緬咖喱,價格實在,想是學生吃飽飯的不錯選擇。
從永康街回西門町,我繼續用腳步丈量臺北。大概是因為公共機構云集,十一點的長長街道,寂靜得多,只有一家家的便利店,提醒著臺北的繁華人世。走了一個小時后,霓虹漸起,樂聲搖曳,臺北老城的日閩味道如茶漬一樣溢出來。龍山寺廟外,男孩女孩推著摩托車停下,坐在排檔的桌下,炸物三兩,還有露天現調的雞尾酒,大概并不需要像在大陸一樣猜測它是不是來自潮州的假酒吧。
夜宵是這般的多,有好有賴,有的拉客,還有的海產面店排著長長的隊,人群神色緊張,像是怕等不到凌晨一點前打烊的最后一碗。我猶豫再三,還是沒有加入這執著的隊伍。
“我們以前從不排隊,這兩年不知道怎么搞的,一到周末,臺東幾家小吃都排上了隊。”在臺灣11省道上,面對太平洋的郡界小村里,年輕的民宿老板對我說,好像也搞不清忽然之間的吃客爆棚,是港客陸客的涌入,還是人人都循著同樣的手機網絡消息,蜂擁地擠到了一起來。
臺灣買不到夜宵的,大概就是這樣僅有兩三戶人家的“偏遠”漁村。然而這竟是人口稠密的臺灣島啊,即使是空曠的臺灣11省道上,村落的數量,也遠遠多于那些真正荒涼的所在。年輕的老板開著他平時送鳳梨的皮卡車,帶我和另外一個住客在海邊公路開了十分鐘,就到達了一家7-11,買齊了明日的早餐,以及今晚的夜宵。
三步一崗的便利店做夜宵,即使口味還不錯,總是有用流水線制品打發腸胃的委屈感。幸好我把在臺灣的日子,留給了滿城煙火的臺南府。那時住在古老的舊式商務飯店,出門幾步就是二十年前小混混們的時髦去處,如今近似荒冢的中國城。熱炒店到了華燈初上的時候,便擺出桌椅來。黑簾子的居酒屋,無聲的擔仔面攤,芒果剛剛上市的冰店齊齊開著,相安無事。三十米就一間茶鋪的場景,更讓人安心。在21世紀的臺灣,茶飲店早就超出了“奶茶店”的甜膩想象,我總是要充足的冰,少糖,要那一點茶香,算是容易厭煩的臺式小清新的一個提神點。
不知從飯店走到赤崁樓來回了多少次,夜夜凌晨時分在騎樓下徘徊,臺南府到底是首善之地,隨便一家小店都有幾十年歷史,甚至還有日本殖民時期就開業的碗馃店。常常會在騎樓下的街頭水果店,點一份芒果冰。看旁邊金毛穿著金項鏈黑背心和他的胖臺妹聊天,看黑夾克花褲子人字拖的大哥帶著他“濃妝大波浪水鉆高跟鞋臺劇”女朋友笑嘻嘻進來吃冰,感受到旅行臺灣的異域情調所在。
吃完芒果冰往飯店走,快到那冷冷清清的中國城時,騎樓下停著的一輛農用小貨車,想不到卻成為了我臺灣之行最念念不忘的一攤。這家“禿頭老爹鮑魚海產粥”原來也是個二十多年歷史的“名店”,每到十點,就開著小貨車進到臺南的最中央,粥里有火燒蝦,小卷,蚵仔,蟹肉和一片金貴的鮑魚,有鮮有甜。我用湯勺喝著扒著,想著二十年前臺灣經濟蒸蒸日上的盛況時,那些從中國城游戲廳玩出來的“兄弟”,也需要這一碗粥去去躁火吧。
有誰不愛盛夏的夜晚呢? 南方的夜宵經年不休,大概也是長年如夏的習慣養成。而那些夏日難得的北方,每年七八月的夜晚,更是不能浪費的。在開封,在蘭州,在張掖,甚至在你可能都不知道它在哪兒的韓城,北方中國的很多鄉親,都聲稱自己擁有全亞洲最大的夜市。韓城確實令我印象深刻,傻眼于一個黃河邊的小城市會擁有如此巨大的夜市,像是丟進了人山人海。蕎面和白面烙成餅,晾干切絲,在湯里抄過,拌上各家秘制熬出的辣油,是我對關中平原最深刻的記憶之一。
在夏日往北方去,就像是在追趕太陽的腳步。到新疆這種有著巨大時區差異的地方,更有窮盡日落之感。喀什夜市可能是全中國最異域情調的夜市,它正對著宏偉的大清真寺,所有擺攤的人都是高鼻深目的維吾爾,金黃色的抓飯上堆著羊頭、羊腰和羊肉,肉感十足香氣四溢的烤串,需得配上冰甜的奶油冰淇淋才有中亞情趣。盛夏的甜瓜和無花果四處擺放,那種軟潤甜糯的質感和香氣,是輸往內地的品種所無法具備的。或許也正是這種一年僅有幾十天的相遇,才是夜宵界一期一會的高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