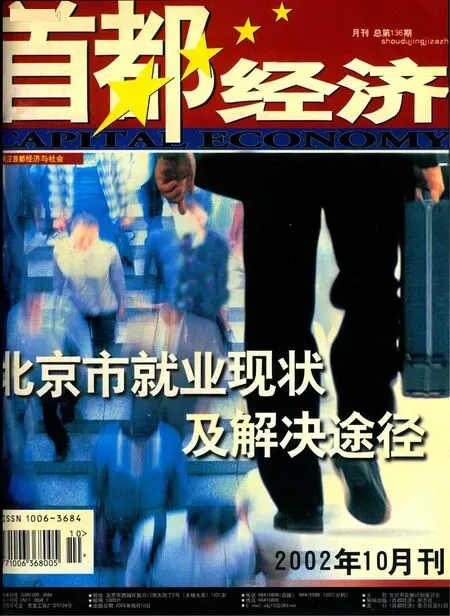互聯網“+”擊之下的電視業
李雪


廣告金主流失,電視開機率下滑,主持人屢屢出走,面臨互聯網的來勢洶洶,被“+”之下,電視臺各出何招?
閉環被打開,狼來了
電視業屢屢傳來壞消息。
首先是收視人群縮水。根據電視廣告咨詢機構“視揚顧問”此前發布的報告顯示,今年一季度,全國省級、市級、衛視、央視四頻道組收視率無一例外同比下滑,央視、衛視均下滑嚴重,分別是6.3%和6.6%。
其次是廣告收益萎靡。電視廣告投放總量出現了近年來的首次負增長,一季度電視廣告刊例同比下滑5.5%,央視一季度廣告投放時長同比跌了22.5%。
再有,主持人才也在流失。從“臺柱”級別的董卿、李詠,到最近的張泉靈、郎永淳,主持人出走央視的消息接踵而來,并且其中相當一部分“跳”往了互聯網。
“互聯網+”之下,未來的電視業,不再是電視臺的天下。
今時不同以往。在以前電視的黃金年代,電視臺制作節目,通過信號傳到千家萬戶,就完成了一個媒體的閉環傳播。老百姓看了,有收視率,電視臺就有了廣告收入。而今天的問題是,“從東方明珠發出的信號,到老百姓家里面,中間出現了各種傳輸通道,有IPTV(交互式網絡電視),有OTT(互聯網電視業務,例如國內的小米機頂盒、愛奇藝盒子等),是通過互聯網傳送的,中間還有電信的運營機構、移動的運營機構,不再是有線網絡公司一家。用戶終端也發生了變化,不再是在電視機前,而是在公交上、地鐵里,用手持終端。”前上海東方傳媒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SMG)總裁黎瑞剛語。
如他所說,在這個多屏互動時代,人們娛樂方式變了。最便利、最隨心掌控的設備最受青睞,逐漸在取代傳統的觀看設備,由此,電視開機率、收視率下滑成為必然。與此同時,互聯網視頻巨頭紛紛發力,不但開始自制節目,意圖在內容產業上分一杯羹,對電視業來說更具威脅的是,當這些互聯網企業把觸角伸進智能機頂盒、互聯網電視等硬件終端領域,開始搶占家庭娛樂入口的時候,電視業的危機是真的來了。
對廣播電視來說,入口被搶,渠道被占,后果很嚴重——平面媒體、唱片公司的現狀都是極好的例證:當高品質音樂實現了在線播放和下載的時候,互聯網成了人們獲取音樂主要渠道,而內容提供方唱片公司則完全失去了議價能力,在版權費上只能任人宰割。
同樣的道理,在這場發生在客廳的戰役中,一旦失去渠道,淪為內容提供商,電視臺將失去話語權,到時就像黎瑞剛所言:“閉環被打開了,你不控制用戶那個界面的時候,價值被大大稀釋。”
獨播的雙刃劍
當然,電視業也沒有坐以待斃,面對互聯網的來勢洶洶,可謂各出其招。
我們不妨從湖南衛視說起。
2014年4月,湖南廣電宣布其“芒果獨播戰略”,幾大王牌綜藝、電視劇只在旗下視頻平臺“芒果TV”上播出,不再將版權分銷給“愛奇藝們”。盡管過去兩年湖南衛視節目版權的“互聯網價”始終處于行業高位,光是將《我是歌手》第二季獨播權銷售給樂視網,就凈賺了5000萬。但在當下,現象級的綜藝節目和電視劇往往在移動互聯的平臺上充當了類似“入口”的作用,具有很強的導入流量的效應。因此,對于想打造平臺的湖南衛視來說,“獨播”邏輯不難理解。
根據今年早前媒體披露的數據,2015年3月“芒果TV”日均活躍用戶近3000萬,較獨播之前增長迅猛。數據服務公司Quest Mobile在4月底公布的數據顯示,“芒果TV”3月份月活躍用戶的增長率甚至達到109.0%,用戶使用時長增長率高達160.7%,這就是“獨播”之后帶來的用戶遷移效應。而在收益上,版權回收后《快樂大本營》、《爸爸去哪兒》等在線視頻廣告貼片收入與此前賣給互聯網的版權費相比也有明顯提升。
其實,當具有巨大內容優勢的湖南衛視開始自建版權壁壘,并用來反哺渠道,這對“愛奇藝們”都將是一個不小的打擊,因為這意味著數億的視頻瀏覽量流失以及龐大的粉絲群的遷移。
不過反過來客觀地說,“芒果TV”仍然有不少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就是因為其“芒果臺”的色彩過于強烈,在獨播帶來流量的同時,反而可能形成一把雙刃劍。
如果用戶對“芒果TV”的認知固化成了“湖南衛視網絡版”,產品調性也就成了平臺發展的天花板,甚至會威脅到平臺中的其他內容。也就是說,除開“芒果系”的節目,其他類型的節目可能很難吸引到那些芒果臺的鐵粉,比如曾獨播美國金球獎頒獎典禮但反響平平就是一個例證,這也會使得其他想在“芒果TV”上投放節目的制作者加以審慎。
當然,或許拿它與“愛奇藝”、“優土”等體量巨大的視頻巨頭們相比也不公平,如果湖南衛視充分利用“芒果TV”這一平臺挖掘其粉絲群體的潛在價值,發展粉絲經濟,專注“小而美”,或許是一條可以嘗試的路線。
傳媒新“生態”
除了湖南衛視,在“互聯網+”上,動作更大的是SMG。
今年6月,SMG旗下兩大上市公司“百視通”和“東方明珠”資產重組一事正式落定,此舉被外界解讀為SMG集團的加速互聯網化。
作為在國內新媒體視聽服務領域的“大拿”,據悉,截至2014年上半年,百視通已經擁有200萬互聯網機頂盒電視用戶、3300萬數字電視一體機用戶、2200萬IPTV用戶、3800萬有線數字電視用戶和688萬戶電視購物與電子商務用戶,渠道受眾量巨大。
而在此之前,黎瑞剛也曾在不同場合中強調,互聯網電視將成為SMG的戰略重點,接下來,在已有基礎上SMG對渠道建設和搶占家庭互聯網入口的布局將會進一步加深。
從重組方案中募集資金使用方向就可以窺知一二:據悉,百億募集資金中有近50億元將投向互聯網電視業務相關,其中20億元購買優質版權內容、9.86億元投向全媒體云平臺項目、17億元投向互聯網電視及網絡視頻項目,以及4.18億的新媒體購物平臺建設項目等。
當然,從家庭互聯網入口獲得流量只是第一步,流量經營同樣重要。
重組之后,SMG原本分散的各個板塊整合成了一個生態系統,內容、平臺、渠道與服務全覆蓋。其中內容板塊是傳統電視傳媒業務,包括節目、影視劇制作和版權經營;渠道則囊括了IPTV、互聯網電視、在線視頻,以及有線電視網絡,為全渠道;服務與應用板塊則包括數字營銷、游戲娛樂、電視購物、電子商務和文化旅游,值得指出的是,好好經營的話,游戲、電視購物、電子商務等具有比較強的變現能力。
客觀地說,在如今視頻平臺全行業虧損這個大背景下,像SMG這種一線衛視仍然握有很大的財務優勢。除此之外,電視制作屬于資產和智力密集型,要想制作出一個好內容需要很強的資金實力、統籌實力和經驗,根基深厚一線衛視相比年輕的“優土”們著實不缺優勢。
因此,做內容出身、又有渠道基礎的SMG其實比一直自詡在構建“生態系統”的“樂視”看起來更有成熟,因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會有業內人士認為,在未來的娛樂影視業,SMG這只國家隊相比“BAT”們更具競爭力。
一朵“廣電云”
再來看看北京電視臺率先升起的一朵“廣電云”,也開了電視業的先例。
2014年2月,“北京電視臺新媒體云平臺”建立,形成了一個以云計算模式為核心的制、編、播全媒體平臺。
別小看這朵云,它標志著一個電視臺全新的新媒體思路和系統。用北京電視臺新媒體發展中心主任蔣虎的話說就是,北京電視臺的電視端、IPTV、北京廣播電視臺網站、BTV版媒體客戶端、微博、微信,在“云平臺”的基礎上都能形成矩陣。
仔細觀察不難發現,傳統媒體在向新媒體轉型的過程中有一個“通病”,即渠道眾多,但各自為政。就拿BTV為例,據統計, 其擁有微博賬號就達112個,微信賬號150個,此外還有獨立建設的IPTV,北京廣播電視網(www.brtv.cn),移動客戶端等等,數量極為可觀。
但它們能否獨立生存,能否帶來的營收讓人存疑。傳統媒體的新媒體平臺似乎更多地局限在擴大品牌影響力上,幾乎沒有商業化的可能。
仔細分析也不難理解,畢竟,報業集團、電視臺的單個新媒體通道所聚集的用戶數量十分有限,各自的用戶屬性也不同。這也就意味著,沒法統一進行商業化,畢竟每個新媒體渠道的受眾不同;也不能分別進行商業設計,高成本的商業方案設計與淺層次的用戶價值挖掘會顯得得不償失。
因此,北京電視臺“云平臺”的建設才有了解釋和意義,它能實現這樣一個功能:在不同的新媒體渠道,有用戶使用,就能留下行為偏好和痕跡,據此分析出需求信息,系統再將與之匹配的內容發送到不同的終端——這些發生在瞬息之間,數以千萬計甚至億計信息的數據處理都可以借助云計算來完成。
“云平臺”可以起到總流量池的效果,相當于散落在互聯網不同角落的用戶都是BTV的用戶,積少成多,形成規模化效應,可以統一進行商業化設計。然后再靈活根據用戶屬性,分別推送內容到不同的終端。
由此,用什么樣的內容去適配什么樣的終端、什么時間與場合推送怎樣的內容去怎樣的終端也就有了答案。商業變現、幫助電視臺改進產品設計、強化客戶關懷、增加粘度都是云平臺之上水到渠成的事情。
在以往的廣播電視傳播中,用戶看得到內容,但內容看不到用戶,也就是說,對所有追逐內容的用戶來說,產出這個內容的電視臺不一定能抓住他們。云平臺的思路就是,廣撒網,在互聯網這片汪洋之中,分散在各個浪花的用戶,即便數量再小,也盡可能多地抓住它們,留住它們,成為自己的用戶。
應該說,這樣一朵既能聚少成多,對每位用戶也都精耕細作的“廣電云”一定是電視臺未來的發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