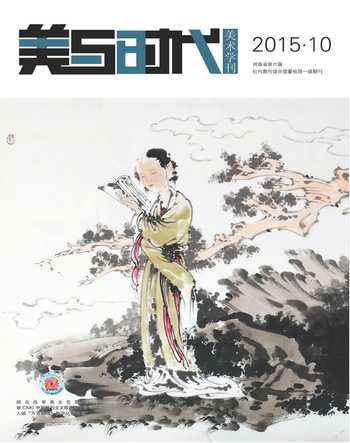也談中國水墨人物畫創作
杜清波,江蘇徐州人。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江蘇省國畫院特聘畫家,徐州市文聯書畫院副院長。 2008年畢業于中國國家畫院梁占巖人物畫工作室。作品多次在中國美協主辦的全國大展中入選或獲獎。其中,2007年,作品《九個炊事員》獲《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80周年全國美術作品展覽》三等獎;2006年,作品《朝霞》入選《紀念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全國中國畫作品展》;2004年,作品《今早有霧》獲《2004年全國中國畫作品展》優秀獎;作品《這年這月這日》入選《第二屆中國人物畫展——紀念蔣兆和誕辰100周年》;2001年,作品《那年九歲》入選《“亞亨杯”全國繪畫書法精品大展》;1999年,作品《彭祖》入選《“鑫光杯”迎澳門回歸中國畫精品展》;作品《彭祖》入選《紀念孔子誕辰2550周年全國美術作品展》;作品《犟》入選《紀念張大千誕辰100周年華人書畫名家精品展》等; 2005年,作品《向網》獲《“黎昌杯”第三屆全國青年國畫年展》銀獎;2004年,作品《老街·早霧》獲《“黎昌杯”第二屆全國青年國畫年展》銀獎;作品《今早有霧》獲《江蘇省文化廳精品創新工程現代都市水墨畫展》銀獎等;還有多幅作品在全國各類大展中獲獎或者被收藏。
中國畫是中國傳統民族繪畫的統稱,也稱國畫或水墨畫。它以墨為主要顏料,以水為調和劑,以毛筆為主要工具,以宣紙和絹帛為載體,是具有民族特色的特有畫種。它是中國藝術的典型代表,是精神性、哲學性很強的藝術。因此,作為中國畫家如果不能深層次的對筆墨的形態、內涵、筆墨結構、規律、以及繪畫題材進行深刻研究和把握,就不能真正進入中國畫的藝術境界。可以這樣說理解了筆墨也就抓住了中國畫的靈魂。
初識繪畫,知道中國畫有寫意和工筆之分,看到的作品,一種無非是把畫的東西事無巨細地如實地畫出來,如同照片;另一種則是粗線條,把基本形狀畫出來,看著很像要畫的東西就行了,書上叫寫其大意。像李可染畫的牛、徐悲鴻畫的馬、齊白石畫的蝦,就那么幾筆,卻活靈活現地表現出了牛、馬、蝦的形象,于是從小率性的我就愛上了寫意畫,更是愛上了寫意水墨人物畫,可是模仿來模仿去就是畫不出人家那樣的活靈活現,琢磨了幾十年,這才感悟“寫意”二字不是那么簡單的畫其大意的意思,卻是意蘊深厚。
每逢中秋佳節,總是常常記起小時候過中秋,一家人團團圍坐、邊吃月餅邊賞月,這時流螢輕舞,小蟲低鳴,夜露微寒,父母親說著細語,兄妹拍手念“月光光,照河上,河犁田,抬花鞋......”記憶兩岸的花瓣紛紛落下,盡管很多東西都已淡去,但那永遠鮮活的是我兒時的故鄉、兒時的中秋、兒時的月。繼而這一切便都成了我創作的源泉,他們給了我無限靈感,因此創作了《兒趣》系列作品。
鄭板橋有語:意在筆先者,定則也;趣在法外者,化機也。童年生活傳達的是人間最美好,最純潔的真情。人之初,一根繩子,一個毽子,一片石塊,手拉著手都是那么的美好。一切藝術緣自一個“情”字,在對情字的表達上,畫家們的基調、姿態各有不同,其靈魂深處的東西更不相同。我難忘家鄉的田野、大樹、小溪、石板橋,那兒多有野趣,妙不可言,所以產生通過藝術語言的闡釋,將家鄉之美和兒時生活之趣融入水墨,從而向人們傳達諸多意趣和對孩提時代的懷戀之情。
很長一段時間,人們對水墨人物畫多少總是有一些偏見,總覺得油畫中的人物是真實的,而寫意為主的國畫中的人物不是那么真實。我認為水墨人物同樣是真實的,也是緊隨時代。為了改變那種偏執的看法,我把目光始終向下看,看生活的底層,始終對現實進行觀注,讓筆墨在悸動和痛楚中展示。要把最后一滴血汗留給土地的老農;正等待著微薄退休金,面對疾病苦苦掙扎的退休工人;甚至是街頭的流浪漢。他們的眼睛睜著、半睜著、閉著,充滿了渴盼、失望、無奈。讓這些真切、鮮活的藝術生命引人心顫,繼而為之感動,甚至生發無限感慨,從而改變那種錯誤的看法。因為無論什么作品樣式,人物要與時代契合,這樣才能真正有生命力。
我越來越深刻的認識到,中國畫絕不只是單獨的表現手法,它更是一種精神、一種手段。“筆墨當隨時代”。雖然幾千年來中國畫的筆墨表現領域在不斷變革中得到完善與超越,但是我們在繼承前人精華的同時,還需要不斷地去變通、去發展......但凡有成就的中國畫家,總是在掌握了一定筆墨技巧與筆墨規律吐故納新中不斷發展。筆墨之道是一個永恒的話題,只有鍥而不舍、聚精會神者才能在這條道路上艱辛地走下去。
探索就是要打開一扇門,門里有什么,只有進去后才會知道。潘天壽論畫時曾講到:“境界層上,一步一重天。雖咫尺之隅,往往辛苦一世,未必夢見。”可見境界是窮其一生都很難得到的東西,是水墨寫意品格思考中上下求索和磨礪祈盼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