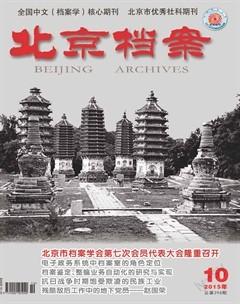朱元璋的懲貪秘籍
馮喆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生于元朝末年,其出身貧寒,幼年曾為地主放牛,飽受欺凌。17歲時,失去了父母和兄長,以乞討為生。他對貧民百姓的疾苦感同身受,對貪官污吏恨之入骨。他深知,曾經輝煌一時的元朝之所以那么快土崩瓦解,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官吏普遍貪污腐化。因此,在明朝建立之初,面對經濟凋敝、百廢待舉的境況,朱元璋以鐵腕懲治貪腐,整頓吏治。
嚴刑峻法懲治貪腐
朱元璋非常重視法律的制定與完善,本著“刑亂國用重典”的指導思想,親自主持制定了《大明律集解附例》(以下簡稱《大明律》)和《明大誥》。
《大明律》歷經數年多次修改,至洪武三十年(1397年)修訂完成,頒行天下,成為一部明代終世大法。對貪污受賄處以嚴刑,對于職務犯罪規定詳細,處罰嚴酷,專門設立“受臟”(所謂“臟”是指非法所得財物)一門,詳細規定了官吏受賄的11種情況的犯罪處罰條款,分別是:官吏受財、坐贓致罪、事后受財、有事以財請求、在官求索借貸人財務、家人求索、風憲官吏犯臟、因公擅科斂、私受公侯財務、克留盜臟、官吏聽許財務。
洪武十八年(1385年)至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又相繼頒行《大誥續編》《大誥三編》和《大誥武臣》,加上《大誥》,統稱《明大誥》,共四編二百三十六條,絕大部分條款針對貪官污吏。《明大誥》由朱元璋親筆完成,語言通俗易懂,內容以具體案例為主,并附有犯人所受的各種酷刑。
《明大誥》集中體現了明朝的嚴刑峻法與刑罰的不拘一格,并將法外用刑法律化。“族誅”、“凌遲”等刑罰被擴大化,并恢復了許多已被廢除的體罰,如:極刑、梟令、墨面文身、挑筋去指、挑筋去膝蓋、剁指、斷手等。《大誥》中收集的案例絕大多數屬于懲治官吏的刑事案件,側重點是打擊貪官污吏,充分體現了朱元璋重典治吏的立法取向。史上著名的“剝皮揎草”就出自其中:“贓至六十兩以上者,梟首示眾,仍剝皮實草。府、州、縣、衛之左特立一廟,以祀土地,為剝皮之場,名日皮場廟。官府公座房,各懸一剝皮實草之袋,使之觸目驚心。”其意是:官吏貪污受賄白銀六十兩以上的,斬首示眾,并把他全身的皮剝下來,再在人皮內填塞稻草。地方各個府、州、縣、衛衙門的左邊特設立一座廟宇,以祭祀土地,同時是剝皮的刑場,也稱為皮場廟。官府的案桌旁,各懸掛一個填滿稻草的人皮袋,以警示繼任官吏不要重蹈其覆轍。酷刑的矛頭直指官吏的貪污腐敗與失職、瀆職,以及不作為,用刑之嚴酷可謂登峰造極。
監督監察
預防貪腐
為預防貪腐,朱元璋建立了完善的監督、監察機制。在中央,有都察院負責糾劾“壞官紀者”,還有獨立于都察院的六科給事中以稽查百官之失。地方上,既有提刑按察使對地方官員進行監察,又派出巡按御史考察府州縣官。巡按御史是皇帝的代表,權力極大,有權監察考核地方官吏。
朱元璋廣開言路,借助民眾力量懲治貪官污吏,建立了“民拿害民官”的舉報制度。《明大誥》規定對于害民之官吏,允許良民綁縛赴京治罪,如“有等貪婪之徒,往往不畏死罪,違旨下鄉,動擾于今后敢有如此,許民間高年有德者率精壯拿赴京來,民拿害民官吏敢有阻擋者,其家族誅”。他規定各地民眾可以捉拿害民官吏進京,也可以越級訴訟,赴京狀奏,如“自布政司至于府、州、縣官吏,若非朝廷號令,私下巧立名目,害民取財,許境內諸耆宿人等遍處鄉村市井,連名赴京狀奏,備陳有司不才,明指實跡,以憑議罪,更賢育民。”典型范例是在《大誥續編》的《民拿下鄉官吏第十八》中,朱元璋向全國通報表彰了江蘇省常熟縣農民陳壽六。陳壽六帶領自己的弟弟和外甥三人捆綁了“害民甚眾”的縣吏顧英到首都告御狀,得到朱元璋大力表彰。
朱元璋還打破只有大員才能上早朝的規矩,規定不論朝廷官員品級、隸屬,均可參加早朝,上殿言事,有隱情還可單獨召見。他準許百姓密封奏事,直接向他上奏。朱元璋還對各級握有實權的司吏進行監視,校檢一旦發現官員有貪贓枉法等問題即可隨時上奏。
此外,朱元璋還建立了校檢和錦衣衛特務組織加強對官吏的監督與監控,利用特務組織從事緝訪、逮捕、訊獄等任務。
堅決懲貪刑上大夫
洪武十八年(1385年),郭桓案事發。這起案件起因于大名府開州的地方百姓進京舉報州判劉汝霖。當時北平布政司、按察司即省一級官員們與戶部尚書郭桓勾結,侵占應入庫的稅鈔。事情暴露后,本應各自追回所侵占的贓鈔,可是身為大名府開州州判的劉汝霖不去追討贓鈔,卻下文到各鄉各村,從老百姓身上搜刮,以補足那些官員們貪污的稅鈔。當地老百姓無法忍受,選派五個人進京告御狀,將這些貪官污吏告到了朱元璋那里。這個案件的主犯郭桓是戶部侍郎,相當于戶部副部長,他在收受浙西秋糧的時候,本應該上倉四百五十萬石,可是郭桓讓人只收進六十萬石上倉,又折收了八十萬錠鈔入庫,按照當時鈔的價值折算,大約可以抵得上二百萬石糧食,兩項加起來只入倉二百六十萬石,距應入倉的四百五十萬石,還差了一百九十萬石。這一百九十萬石已被他們貪污私分了。除此之外,郭桓還向浙西各府索要了五十萬貫鈔。當時南京應天府周圍的五個府內有不少犯罪官員原來的田地,被官府沒收了,成為沒官田。這些田地的夏稅秋糧合起來也有數十萬石,郭桓伙同地方官員把這些稅糧全部拿去私分,一粒糧食也沒有入倉。按照當時調查的結果,這些私分的糧鈔合計一共多達二千四百余萬石。這個數字接近明朝初年洪武朝一年的全國稅收,超過了明朝嘉靖、隆慶兩朝平均全國一年的稅收。
郭桓是戶部副部長,他只能貪污各地上繳國庫的糧鈔。而國家入庫糧鈔是有數的,他貪污多少,入庫就會少入多少。實入庫與應入庫的數字不符,這樣一來他們貪污的事情立刻就會暴露了。因此,他要貪污就必須與地方官員、管庫官員勾結起來共同作案。所以,這個大案被追查的時候,竟然有數以萬計的官員牽連其中。這一方面說明這起經濟案件牽扯范圍之大,官員之多;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朱元璋肅貪決心之大,不管是誰,一個也不放過!當時因為抓的官員太多了,于是有人私下議論,說朝廷打擊范圍太大,好人壞人不分了。朱元璋聽到后,專門寫文駁斥說:你們看到我處理貪官,覺得我處理得太過嚴厲了,于是有人來替貪官說情,這是惻隱之心。可是你為什么看不到貪官侵占民財的時候,對老百姓有一點惻隱之心呢?你要是在那時候能夠有一點對老百姓的惻隱之心,不跟貪官同流合污,在貪官們搜刮民財的時候出面阻止,或者舉報他,這才是對老百姓的同情愛護。當時視而不見,到了貪官事發又說三道四,這種人跟貪官又有什么區別?
吏治清明兩漢遺風
朱元璋通過重典治貪,使得明初吏治清明,幾有兩漢遺風。《明史·循吏傳》認為,重典治貪使“(官吏)一時守令畏法,潔己愛民,以當上旨,吏治煥然丕變。下建仁、宣,巡撫休息,民人安樂,吏治澄清者百余年。”清代史學家趙翼在《二十二史札記》對明初吏治的評價是:“幾有兩漢之遺風,且駕唐宋之上。”他將明初吏治與歷史上最好的兩漢相比,把唐宋完全比下去了。據《明史》記載,在重典治貪的環境下,明初六十年的廉吏有一百多人,占明朝廉吏的六分之五。
既然重典治貪效果顯著,有人不禁質疑,為什么明朝中后期是中國歷史上腐敗最嚴重的時期之一?這首先是因為明朝統治者未能將重典治貪制度化、常態化。朱元璋因為重典治貪而背上暴君的惡名,所以他晚年對自己的繼任者建文帝朱允炆說:“朕治亂世當以重典,爾治平世當以輕典。”由此可見,朱元璋重典治貪,只是在元末明初這段動蕩年代所采取的特殊手段,未能長期實行,隨著時間的推移最終廢弛。其次,絕對的權力必然產生絕對的腐敗。封建王朝的行政權、司法權、立法權高度集中,因此,腐敗是無法杜絕的,即腐敗是封建王朝無法根治的痼疾。只有將行政、司法、立法等權力分立、相互制約才是根治腐敗之關鍵。
作者單位:中國檔案報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