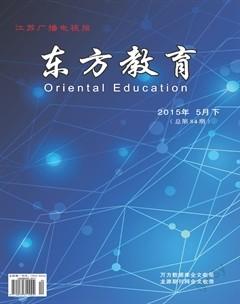戰爭中的女性:淪陷與救贖
喬石
【摘要】電影《我們的父輩》作為近年來反思二戰的經典之作,獲得了不錯的反響。在展現戰爭的殘酷與無情的同時,更注重個人在戰爭中的苦難與掙扎,尤其是女性在戰爭裹挾下的淪陷與救贖。電影既刻畫出女性作為戰爭中的普通一員的境況,又細膩地表現出女性特有的視角,十分難得。
【關鍵詞】《我們的父輩》;淪陷;救贖;女性
《我們的父輩》是一部德國人關于二戰的自我審視的作品,以“我們的父輩”威爾漢姆自述的方式還原那段不堪回首的歲月。在這部迷你電視劇中,五個年輕人在戰爭伊始,正值青春年華,他們對人生懷著甜蜜的期待,對未來有著美好的期許。可戰爭爆發,他們的人生軌跡已被改變,注定在戰亂中掙扎,注定會用鮮血甚至生命為這場戰爭付出代價,也注定會被這場戰爭烙上痛苦的印記。
哥哥威廉是一名軍官,他代表著戰爭開始時德國社會的主流思想——德意志無往不勝。最初,他對于上級的任何指令都努力完成,隨著戰爭的一步步僵持,他從勇往直前的勇士變成厭惡戰爭和殺戮的普通人;弟弟弗雷德漢姆是個偏愛文學反對戰爭的年輕人,他被迫走向戰場,從一名厭惡戰爭的“膽小鬼”變成一名殺人不眨眼的惡魔。哥哥的女朋友夏莉是一名對德意志引以為傲的護士,從一開始憧憬著奔赴前線到在救護中認識到戰爭的殘酷,夏莉完成了她特有的蛻變。而他們的好朋友維克托和格雷塔——一個猶太人和他德國女友——在戰爭中則舉步維艱。格雷塔為了救維克多,委身于高級軍官,希望借此為維克多換來逃離的通行證,但這張通行證卻將維克多送上開往集中營的列車,本以為她委身的男人可以依靠,到頭來卻被他送進監獄。
一、時代洪流中的女性
戰爭,通常被認為是男人的專利。因為戰爭本身所體現出來的暴力,殘酷,血腥以及不擇手段,正是戰爭所擁有的這些特性使其成為男性釋放多余荷爾蒙的合理途徑,戰爭也成為男人心里殘存的夢想游戲。該劇在導演上帝視角敘述下的女性是豐滿的,性格刻畫得相當細膩,并沒有因為其敘述視角的缺席而變成一個扁平人物。在反思二戰,反思希特勒法西斯的大背景下,女性同樣作為被時代裹挾的一份子,她們和實際參與戰爭的男主人公一樣,身上也留下了時代的烙印。
夏莉在五個人的圣誕聚會時,高興地向伙伴們宣布自己已經獲得了護士資格,非常天真地懷著愛國心準備去前線做護士,來到戰地醫院面對護士長的詢問,她會自豪地說:“代表全德國的婦女同胞!”經過第一次面對鮮血不止的傷員,她會慌亂不知所措,但是當她作為一名德國戰地醫院的護士去挑選莉莉亞作為幫手的時候,她的身上還是有著一種膨脹的驕傲。在法西斯的宣傳下,最年輕單純美麗的姑娘,應該富有人道主義的地方——醫院,因為這樣一種時代的要求,夏莉會變成一名帝國的護士,也會響應號召去舉報猶太人莉莉亞,盡管莉莉曾幫助她脫離窘境。
而格蕾塔在時代洪流中的漂浮更加明顯,她和維克托因為種族的差異,兩個人相愛本就不易。“水晶之夜”開始,事態急轉直下,年輕的德國女孩格蕾塔能為愛人做的,也就是送他遠離是非之地,為此她付出了自己的身體。讓人難受的正是眼睜睜看著她的付出其實沒有任何回報,蓋世太保只是為了得到她的肉體,卻轉手把她的愛人送往了集中營。
而另一方面,格蕾塔又有著成為歌星的夢想,為此她會繼續跟蓋世太保保持著關系,因為他能幫助她成就夢想,成為歌星,去到巴黎,米蘭演出。在戰火紛飛的時代中,格蕾塔通過出賣自己的肉體,完成了自己的理想,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看起來她仿佛是時代的寵兒,可是她卻因為一句“我們不會贏的”,而被定為散布失敗言論罪最后被槍斃。其中固然有蓋世太保想擺脫她以孩子為威脅的原因,但不得不說格蕾塔既是時代的寵兒,又是時代的棄兒。
當時代需要她作為歌星去安慰在前線熱血奮戰的時候,她可以享受專車專機等各種優厚的待遇,可是軍人只是覺得她是一個慰問品,甚至是玩物。不管是積極響應時代召喚的夏莉還是最后成為時代棄兒的格蕾塔,她們原本都只是被時代洪流所裹挾的善良的女子而已。時代的不幸不光落在了在炮火下喪生的男性身上,而女性亦以別樣的方式承擔著時代的痛苦烙印。
二、愛情與肉體
關于愛情,劇中有兩條明線:夏莉與威廉,格蕾塔與維克托,或許還有一條暗線:維克托與波蘭女子。
夏莉與威廉本是相當合適的一對,男才女貌,只因為戰爭爆發,兩人都要前往前線,兩個相愛的人為了不讓對方擔心,彼此都沒捅破最后一層窗戶紙。當夏莉在得知心愛的人威廉戰死的消息后,選擇了與主管醫生發生關系,或許,主管醫生只是威廉的代替,夏莉只想通過肉體的發泄來緩解愛人喪生的痛苦。故而當夏莉發現威廉并沒有死的時候,她選擇了悲喜交加的逃離。
對于格蕾塔而言,當她用肉體與蓋世太保交換一張愛人逃離柏林的通行證的時候,她承受的巨大痛苦與誤解我們都可以看到,戰爭將愛情硬生生地毀滅,只剩下赤裸裸的肉體交易。而當她繼續淪落,為著自己的歌星夢而用肉體向蓋世太保獻媚的時候,我們會情不自禁地感到不適,因為她在用肉體交易的方式滿足著自己的私欲。
而與維克托一起患難與共的波蘭女子,最后在游擊隊中,當維克托被質疑是否是猶太人的時候,她毅然回答:“正如你所說,我和她睡覺,所以我清楚他猶太人。”雖然她知道維克托就是猶太人,而她和其他游擊隊員一樣認為“猶太人和共產黨人、俄國人一樣討厭,死了比活著強”。但是她會依舊選擇挺身保護維克托,她的這種行為是善良的,但是她用來證明維克托不是猶太人的方式卻是值得玩味的。其實這還是她在用自己的肉體在證明,盡管她與維克托之間只有經歷患難的情誼,但是在那樣的環境中,肉體無疑更令別人相信。
從男性視角出發,一方面,女性可以運用自己的肉體去換取某種所謂的“正義”的事情,另一方面,女性運用自己的肉體在戰爭年代去謀求生存卻是受到歧視的。那我們對于女性的要求是否過于苛刻呢?本片中的男性視角敘述決定我們不會照顧到女性作為區別于男性的第二性的存在的特殊性,如果還是依照男性視角的標準去作價值判斷,不免顯得武斷而不近人情。
三、救贖
本劇最后出現的一個比較神奇的人物——莉莉亞,她曾經因夏莉告發而被捕,而當蘇軍戰士沖進醫院想要強奸沒有來得及撤離的夏莉時,她卻作為蘇軍政委,夏莉的拯救者出現了。不得不說,莉莉亞的出現顯得太巧合了,十分突兀,但是想想莉莉亞最后說的話,我們或許會明白,導演的良苦用心。冤冤相報何時了,莉莉亞和夏莉這兩個女性最后的和解,或許正是導演所寄予希望的救贖所在。而這或許是因為女性善良的本性,在戰爭過后還存有一絲善良,這也為和平帶來了一絲女性的曙光。
參考文獻:
[1]《<我們的父輩>:德意志零年》,《文藝風象》2013年11月。
[2][荷]伊恩·布魯瑪:《正常的納粹》,《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4年3月16日。
[3]《帝國風雨后,戰爭中的一代》,《經濟學人》(Economist)2013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