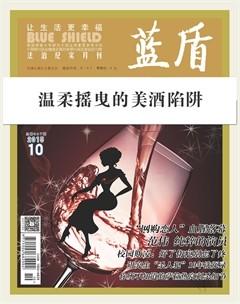校園欺凌:好了傷疤別忘了疼
佚名
一件事情如果基本判斷是錯的,后面就全錯了。在無數(shù)成年人眼里,校園欺凌不過是“小孩子之間的打鬧”——這是錯的。
它很惡劣。青春期的殘忍,超乎想象:花樣百出的人格侮辱,不顧后果的肉體摧殘,在媒體報道的校園欺凌事件中屢見不鮮。重慶一個初中生,就被同學毆打致死,鼻青臉腫,渾身瘀青。死后解剖,腸胃里全是血。
它很頻繁。在任何時候談論這個話題,都不愁找不到由頭:隨便去網(wǎng)上一搜,總能搜到一兩周內(nèi)發(fā)生的此類報道,少則一件,多則數(shù)件。而媒體報道出來的,不過是冰山一角,以中國之大,說校園欺凌每時每刻都在發(fā)生,毫不夸張。
它影響極壞。它給受害者留下深重的陰影:在知乎網(wǎng),因為永新校園欺凌事件,一堆成年人回憶自己少年時被欺負的經(jīng)歷,感慨不堪回首。它給施害者造成長期影響,有研究顯示,校園欺凌行為和青少年犯罪有一定聯(lián)系。即便你只是旁觀者,也不能置身事外,它會影響你對社會的看法并固化為相應的行為模式。
但是,事情的嚴重性與受重視的程度完全不相稱,問題就出在很多人認為這不過是“小孩子之間的打鬧”罷了。這種認識極其冷漠,甚至可說冷血,它把被欺負的孩子置于孤苦無告的境地。說起來也奇怪,很多人在成長過程中都目睹、經(jīng)歷過校園欺凌,但長大之后就迅速地“好了傷疤忘了疼”。
在中國,大多數(shù)校園欺辱事件處于被忽視狀態(tài)。校園欺辱大致可以分為身體欺辱、語言欺辱和關(guān)系欺辱(比如刻意排斥、散布謠言等),媒體曝光的一般都是比較惡性的身體欺辱。即便極少數(shù)被曝光的案例,事后處理往往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多由學校內(nèi)部處理了事,少部分由公安機關(guān)介入,但處罰也很輕。因為被忽視,對被欺凌的孩子來說,要么忍氣吞聲,要么以暴易暴。有網(wǎng)友回憶往事,說:“我最痛苦的事情在于,我要把我本質(zhì)上變成一個跟加害者一樣的施暴者,才能保護自己。”
現(xiàn)在,事情開始發(fā)生一些變化,網(wǎng)絡的發(fā)達,自拍的流行,讓原本隱蔽的校園凌辱得到越來越多的曝光——很難說是“愈演愈烈”,也許只不過是以前我們不知道而已。而對外部世界的了解,也逐漸讓人認識到對校園欺凌不該如此輕忽——最近發(fā)生的中國留美學生欺凌同胞事件,施害者在美國可能面臨終身監(jiān)禁的刑罰,這給國人帶來了極大的震動。
但大體而言,我們對于校園欺凌的認識仍然處于萌芽狀態(tài)。這其實是一件非常復雜,非常難以處理的事情。留美學生欺凌事件讓很多人提議立法嚴懲,但嚴刑苛法并不足取——因為這是最后的手段,走到這一步,本身已經(jīng)是教育的失敗。我們需要的并不是在刑法中增加一條關(guān)于校園暴力的法條,而是一項專門的《校園欺凌防止法》。這項法律的主要功能并不是研究如何處罰施害者,而是建立各種制度,規(guī)定各方責任。
比如在韓國,2004年就出臺了《校園暴力預防及對策法》,并在此后不斷修訂。該法制定了“校園暴力對策委員會”制度,歸國務總理管理,委員從專業(yè)人員中產(chǎn)生,每所學校都要設置學校暴力對策自治委員會,配置專職的咨詢教師和負責小組。在日本,經(jīng)歷了80年代中期、90年代中期和2011年三次大討論后,于2013年公布了《防止欺凌對策推進法》。而歐美國家對校園欺凌的研究和干預比東亞地區(qū)走得更早,模式也更為多樣。
由于涉及未成年人的教育問題,它比一般的暴力犯罪問題要復雜很多,牽涉到政府、學校和家長等方方面面。比如說,普遍認為學校應負主要責任,但目前中國的教師是否有精力和能力處理相關(guān)問題?再比如說,家長責無旁貸,但在家長責任和學校責任之間如何區(qū)分以防止卸責?考慮到中國國情,有大量外來人口子弟和留守兒童,這對于校園欺凌的成因和形式有什么樣的影響?……對我們來說,現(xiàn)在最需要的是最基本的調(diào)查研究工作,然后制定出一個本土化的校園欺凌行為預防和控制計劃。
當一件事情開始引起注意,這時候我們需要的是給它指出一條正確的方向,而何謂正確,則需要大家一起來商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