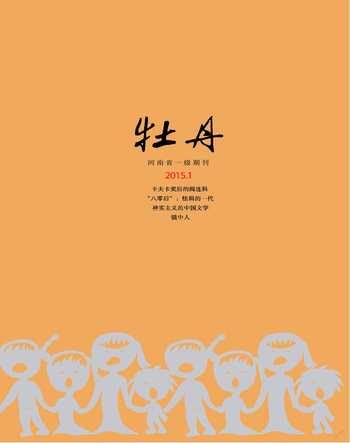氣球
唐詩,湖南安仁縣人。2009年出版短篇小說集《兩情相持》,作品散見《散文選刊》《海外文摘》《四川文學》《作品》《廣西文學》《山東文學》《芳草》《安徽文學》《南方文學》《工人日報》等刊。現居深圳。
1
整整兩個月,四到六天之間,林影都會做同樣的夢。夢里出現了氣球,五顏六色,很好看,飄浮著。在某個昏暗的空間,她似乎在等什么人,因為等待而焦躁,緊接著,夢就醒了。
林影在“世紀佳緣”注冊的名字就叫等待,特意挑了兩張美艷動人的生活照貼在上面。幾百封來信中,她略略算了一下,互相加過QQ的不下六十位,聊過天的占百分之四十,三成約見過,另有七個約好了又改約,最終再沒心思赴約直接打入黑名單。
約見林影的男人大致分為三類:離異有孩,離異無孩,中年未婚。經過她多方面的調查研究分析,“中年未婚”這一類最不靠譜,他們有驚人的共性:自命不凡、憤世嫉俗。“離異無孩”類最現實,他們大都老成世故而多疑。有誠意的還數“離異有孩”類。可誠意歸誠意,要做好人家的后媽也得有一定的修行。林影不認為自己具備這方面的才能。
在林影的記憶里留下烙印的要數一個七歲大的小女孩,彎眉、瓜子臉,睫毛又密又長,眼睛清澈如水。男人牽著她的手出現在林影面前時,幾乎是出于一種本能,林影立即喜歡上了她。
席間,男人去上洗手間,留下小女孩和林影獨處。小女孩將頭低著,一邊吃飯一邊說:“我媽比你漂亮多了。”
“這么說你像媽媽啰。”林影說。
小女孩看她一眼,說:“如果你嫁給我爸,我只能喊你小媽。”
“小媽?”這個詞讓林影心里咯噔了一聲,像是被人狠狠摑了一耳光。
前兩年,林影三十四歲,鼓足勇氣才回家過了春節。兄弟姐妹全部出雙入對,就連十八歲的侄女都領回一個青春美少年,只有她還是一個人。
在林影面前,家里人都有意無意避開戀愛、結婚、生孩子這些話題,似乎一觸及就是拿刀刺向她的面皮。
返粵前,林影長長噓出一口氣,心里想,再也不一個人回來了。誰知,她媽到底沉不住氣,趁著大家上桌吃飯的間隙,將她拖到臥室里,反鎖上門。
“有沒有男朋友?”
“沒……有。”她囁嚅半天,回答。
“到底有沒有?”
“有。”她咬了咬牙,不禁嘆了口氣。
“那怎么……”輪到她媽嘆氣。
母女倆面對面默默坐了一會兒。
“實在不行就生個孩子吧,我幫你帶。”這話讓林影眼睛瞪得老大,下意識喊出一句:“媽!”
她媽面無表情,眼睛望著窗外,說:“我不是開玩笑……總是要有一個人陪在身邊才好。所以,趁著還不算老,趕緊生個孩子吧。”
“媽!”她驚訝得不知道該說什么才好。
“真的,生個孩子吧,我替你帶。”她媽說完這句話后,用手抹了抹臉,打開門,走出去了。
林影知道她媽的意思,可她沒有做單親媽媽的勇氣。
2
“我小時候很喜歡氣球,過年時想得到的唯一禮物就是幾枚嶄新的氣球。”林影對倪洪說起那個莫名其妙的夢。倪洪歪在沙發上,耷拉著腦袋對著手機按著什么,并未搭腔。
林影離開電腦桌,走到倪洪身邊坐下。他沒有看她。“我媽希望我生個孩子。”她說。
倪洪迅速看她一眼,又埋頭看手機。
“她說孩子可以交給她帶。”話才說出口,林影突然覺得自己特賤,這個念頭讓她幾乎是從沙發上跳了起來,像是被什么東西嚇到了。愣一會兒,她重新回到電腦桌前,眼睛盯著屏幕,右手無意識地點開一個又一個淘寶店。
她和倪洪剛認識那會兒也如膠似膝過,一天不見都受不了似的。不過半年時間,雙方都冷淡下來,幾乎到了彼此厭倦的地步,卻都避開分手這個詞。有幾次,林影覺得兩個人到了非“分手”不可的地步了,話也到了嘴邊,又生生被她用口水咽進肚子里。她下意識審視鏡中的自己,唇兩側的法令紋即使不笑也很深了。明艷動人的女子早已老去。
不輕言放棄,這是林影希望自己能夠做得到的事。和初戀男友相戀七年后分手,是她主動提出來的。七年后的某一天,她想念那個男人的笑容,竟然覺得不管他曾經怎樣荒唐,她都可以不在乎,只要他愿意繼續留在她身邊。她暗暗發誓,若再次戀愛,她不再做那個主動提出分手的人。
沒認識倪洪之前,林影想過獨身。她的朋友圈中就有獨身主義者。特別是那些離異有孩的女性,她們多數處在高不成低不就的狀態,久而久之,獨身成了定局。也有少數男性,甚至是從未有過婚史的。
林影把獨身主義看成是獨善其身,與世無爭。獨身多好,不用擔心情感上的背叛和傷害,不用對別人付出愛和責任。可她現在想和倪洪結婚,想和他生個孩子。她不知道自己為什么會產生這種想法。也許跟年齡有關。她已經有了危機感。事實上,她并不認為自己有多愛倪洪,她不過是想找一個人來分擔寂寞,來對抗無情歲月。
倪洪究竟怎么想的,她從來沒有問過。他對她的態度令她捉摸不透。他偶爾叫她“影子”,多數時候直接喊“寶貝”。情人節也給她送玫瑰或者百合,也對她說:“我愛你。”可她略略想一下就發現,他給她的承諾沒有一次兌現過。他沒有像他說的那樣帶她去海南島度假,沒有在她生病的時候及時出現在醫院里,更沒有像他說的那樣在三年內迎娶她。就連她費盡心機做好晚餐等他回來,他也沒有一次準時過,有幾次,他甚至壓根沒出現過,連一句合理的解釋也沒有。
“這個月的最后一天,如果是個雨天,我們就分手吧。”林影說。倪洪“嗯”了一聲,眼睛仍然盯著手機屏幕,一會兒卻又問:“你剛才說什么?”
3
隔壁住的女孩在酒店上班,這是林影在這個城中村的小公寓里居住了三年之后才知道的。那晚,她從凌晨三點的夢境中爬起來,打開門走到小區的空中花園去透氣。她去的時候,女孩趴在石桌上,穿著白色的短褲,雙腿架著,用半邊屁股坐在石凳上,整個身體呈現出隨時都要坍塌的模樣。她的長發完全遮住了整張臉,透過不明朗的光線望過去,毛絨絨一團,偶爾略略抖動那么兩下,令人聯想到幽靈之類的生物。
默默坐了一會兒,女孩對林影說:“我們聊聊?”林影遲疑了一下,問:“你和我?”女孩猛地抬起頭,伸手朝林影身后一指,聲音冰冷:“我說的是一直站在你身后的那個!”林影本能地打了個冷顫,女孩卻吃吃笑起來。
“失眠?”她問。
“不是……以往這個時候我正在上班。”女孩說。
“哦……還要上夜班?辛苦。”
“習慣了……你男朋友今天沒來?”
林影不想和任何人談起倪洪。他真的是她男朋友嗎?普通人眼中的那種男女關系?男朋友是什么?她模糊地想起他的樣子,他是單眼皮嗎?她記得一個冬天的夜晚,她從寒冷中醒來,伸手去摸他的臉,沿著他臉上的弧線畫起來。寬額頭,圓下巴,直鼻梁……他睜開眼睛時,她的手停在他的眼眶處……她明明記得有畫過他的眼睛,事后竟然完全記不起了。他究竟是單眼皮還是雙眼皮呢?林影想,下次見到他的時候,一定得好好看看他的眼睛。
“你相信愛情嗎?”女孩說,她的整張臉又藏于長發中去了。
“相信。”
“這么說你也相信男人?”
“愛情不一定來自于男人。”林影說完,抬起頭望了一眼天空。遠處什么都沒有,一顆星也沒有。她嘆了一口氣。
“我知道你不是同性戀。”女孩的聲音懶懶的。
林影不想再講話了。
“我上學那會兒愛過一個男人,我愿意為他做一切事情,甚至是死。”女孩說。
“后來我又愛了另一個男人,我也愿意為他做一切事情,除了死。”女孩說。
“前不久,我發現我又愛上一個男人,我希望他能為我做一切事情,包括死。”女孩說。
林影不知道女孩為什么會和她說這些,就她自己而言,她不會輕易跟任何人說起放在心底里的任何事,特別是情感上的那些陳芝麻爛谷子。女孩太年輕了,她這樣想著,從石凳上輕輕地站起身來。趁著天還沒亮,她想再回到床上睡一會兒。
離開之前,她想對女孩說點什么。她總不能任何話都不說就貿然離開吧?她想表現得有人情味一些。
“或者,遍體鱗傷,才會漂亮。”僵了一會兒,林影丟下這一句,往回走。
“我認識你男朋友。”女孩的聲音自林影背后橫掃過來。她略略愣了一下才繼續往前走。
“我在酒店上班。”女孩說。緊接著,她又說出了那個酒店的名字。
4
工作之余,林影喜歡關注征文啟事,寫點小文章滿世界投。除了偶爾中個三等獎,她獲得的全部是優秀獎。對此,她的說法是:“都怪我是個優秀的人。”如果頒獎地不是太遠,她便盛裝去領獎。
半年前,林影的郵箱里收到了一個征文頒獎嘉賓的來信。她不記得給過他名片。對方言語誠懇,對她贊美有加。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他們每天都通信。有時候一天之內,她會連續寫三封信給對方。在信中,他們的話題多而繁雜。她通過百度得知他在全國多家文學期刊發過小說若干,于是稱他為小說家。小說家有時候很狂妄,一副誰也瞧不上的語氣,有時候又很悲觀,過于自怨自艾。
小說家鼓勵林影寫小說。他認為是小說賦予了人類想象力和創造力。他說每個人都應該拿起筆來寫小說,這樣才會遠離罪惡、膚淺和無知。
林影自認是個缺乏想象力和創造力的人。
夏天時,小說家向林影發出邀請,約她一起出去旅游。他的文友遍布全國各地。他說只要他愿意,每個城市都有他的落腳點,而且是免費吃住行,還有人主動相陪。
林影沒有膽量和一個只見過一次面的男人出去旅游。
那個關于氣球的夢,林影和小說家也說過。小說家說氣球代表了膨脹的希望。他問林影是不是處于恨嫁的階段。她避開了這個話題。
林影最后一次和小說家通信,他們吵了一架。小說家說林影就算個球。她為此傷心了好久。她沒有告訴小說家,她的世界里有很多禁忌,比如球。只要球這個字一出現,倪洪兩個字便像一根刺那樣準確無誤地卡進她的喉嚨里。想嘔又嘔不出,要咽下去也絕非易事。
隔壁那個女孩說的酒店,林影去過一次。倪洪口袋里的紅色收款收據上有那個名字。她生日那天,倪洪說有公務活動。她一個人坐的士出去時,無意間瞥見他和一個濃妝艷抹的女人進了這家酒店。她讓的士司機將車停在酒店對面的一樹大樹下等他。等了一會兒,的士司機說:“如果你花的是男人的錢,就繼續在這耗著。否則,看在錢的份上,還是別等了。”
林影質問倪洪為什么要騙她的時候,他雙目圓睜,喊道:“你憑什么跟蹤我?你算哪個球?”她被這句話喊得愣在那里,條件反射地回了一句:“我是氣球!氣球!”
事后,倪洪又哄林影,說開展公務活動,有個把濃妝艷抹的女人出現也不代表他就帶女人去酒店開了房。她了解他,除非有確鑿證據,不然他是斷然不會承認的。
退一萬步來說,就算是有了證據又怎樣?倪洪會說那只是逢場作戲。男人們都一個樣——這個念頭在一瞬間將林影掏空,她感覺到自己的身體真的變得像一枚氣球那樣輕,隨時都可能隨風飄走。
林影再也沒有回小說家的信。
5
林影的初戀男友姓柏,她喊他木白,他喊她木木。
木白做IT行業,常年熬夜。木木在事業單位,每天朝九晚五。
兩個人在一起的第三個年頭,木木將家里的鑰匙拿給木白。
第七個年頭,兩個人談婚論嫁。就在約好第二天去領證的前一天晚上,木木有些亢奮得睡不著,打開電腦登上QQ找人聊天。一位久不聯絡的老同學和她聊了幾句,說起領證。對方說:“領證之前做個摸底調查是有必要的,免得貨不對板,想退貨就沒意思了。”老同學在派出所上班,他夸口說能調出所有中國公民的開房記錄。木木的內心被什么刺了那么一下,有些痛。
略略算一下,木白每天都對她說:“我愛你!”無需過腦子似的。
調開房記錄之前,老同學一再叮囑木木注意保密,否則,他的飯碗就砸了。
木木記得那是個春天,陽光顯得慵懶。她隨意穿了條洗得發白的牛仔褲和一件帶帽式的長袖衛衣,出了門。她和木白約在民政局前面的廣場見面。
“如果他說實話,我就原諒他。”木木一路走,一路這樣想著。
木白穿著一身西裝,還打了條新領帶,看起來很慎重。
“激動嗎?”她問他。他點了點頭。
“為了讓你冷靜下來,問你一個問題唄。”她說,面帶淺笑。
“隨便問。”他說,搓了搓手,表情輕松。
她低下頭,笑容從臉上一點一點抹去。她的眼睛并不看他。
“你有沒有背叛過我?”她眼角的余光抓牢他。
“沒有,怎么會呢?”他說,仍然笑著。她覺得他的聲音里藏著一絲令人不安的情緒。她長長地“哦”了一聲,毫不掩飾那份失望。
他一把摟住她,說:“別說這些掃興的,我們早點去把證領了。”她表現得不置可否。在領證之前,她得快刀斬亂麻。不原諒是什么?分手嗎?還是裝傻?
他牽著她往民政局走去,她由著他牽著。她覺得自己的腳步有些踉蹌。快到民政局門口了,她用力抽出自己的手,還下意識地甩了甩。
“我有個老同學在派出所上班。”她的話說得突兀,他一臉不解。
她看著他,張了張嘴。
“怎么這會兒說這個?”他說,有些不耐煩。
“他能調出全國公民的開房記錄。”她說這話的時候甚至努力地笑了笑。
多年后,木木已經忘了木白當年的表情,她也不記得他是否有向她解釋什么。她只記得他們之間最后的畫面。
她將一份早已準備好的禮物從隨身包里掏出來,盡量使自己的聲音平靜:“最后,我們交換一份禮物吧。你只需要將我家的鑰匙交換給我就成了。保重。”她記得那份禮物原本是準備在他生日那天送出去的——是一本DIY的相冊,里面是她偷拍他睡著后的每一個表情和姿態。
6
準備離開城中村那天,林影在搬空的房間里默默走了一圈又一圈。她想到要將屬于這里的回憶帶走,再也不會回來,心里空蕩蕩的。走到臥室,她盤腿坐在飄窗那兒。倪洪不回來的無數個夜晚,她通過這扇小窗望出去,能遠遠看得見海鮮市場,聞見魚腥味。
有那么一個不短的時期,倪洪身上總有一股奇怪的香水味,林影需要依靠窗外飄來的魚腥味來緩解嗅覺的靈敏度。她打算在空蕩蕩的房間里睡一晚再離開。
最后一次見到隔壁那個女孩是在白天,她敲開了林影的門。那張年輕的臉過于蒼白,眼皮耷拉著,明顯睡眠不足。奇怪的是她的長發在頭頂挽成一個高高的發髻,發髻正中間別著一枚亮光閃閃的皇冠發簪。
“東西都搬走了?”女孩倚在防盜門上,高昂著頭。
林影笑了一下,目光重新將房間環視了一遍。什么都沒有留下。
“人生非得這樣似的,必須一次又一次離開。”女孩說出這句話讓林影略略吃了一驚,她覺得自己不該將對方簡單的歸于風塵女子這一類。
“和他分手了?”女孩問。林影低下頭,不置可否。女孩嘆了口氣。
“我聽說你是寫小說的?”
“聽誰說?”林影看了一眼女孩,她的皇冠穩穩地插在發髻里。
“倪洪。”林影早該猜到是他。
“你為男人而悲傷嗎?”女孩微微歪了歪頭,又說:“你應該自信一些。”林影眼里只有女孩子頭頂上的皇冠,她如實告訴女孩,她并不寫小說。看得出女孩有些小失望,以至于那枚閃著光的皇冠發簪抖了抖。
“你的自信來自于哪里?”
“男人那里。”
“男人并不是你身體的一部分。”
“我還年輕,長得還很漂亮。”女孩說這話時笑了一下,她應該也意識到這是說了個冷笑話。
“我想一個人呆一會兒。”林影說。
女孩離開的時候低著頭,林影說了一句很文藝的話,她說:“別低頭,皇冠會掉。”女孩沖她嫣然一笑,比了個“勝利”的手勢,說:“你也是。”
林影下意識摸了摸頭頂,似乎真的能摸到一只閃閃發著亮光的皇冠。
一入夜,突然下起雨來,先是淅淅瀝瀝地下,到后來雷聲陣陣,大雨傾盆而降,天要塌下來那般。這個月只剩下最后兩天。林影躺在飄窗邊上看電視,天氣預報說接連三天都會是暴雨天,紅色預警顯示在屏幕上方。林影想到有句歌詞是分手總在雨天,沉沉睡去。
責任編輯 王小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