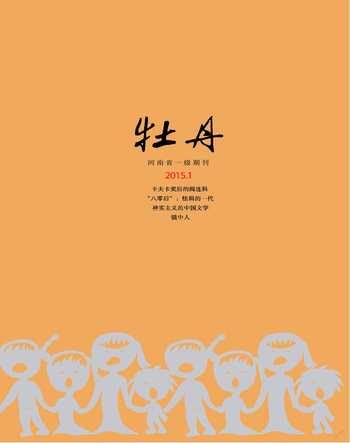母親的黃豆醬
王艷杰
自打我記事起,每到夏季,母親都要曬上兩壇黃豆醬。
先把顆粒飽滿的黃豆淘洗干凈,放到柴火灶上煮熟,然后撈出,再鋪在陽光下的白粗布上爆曬,直至黃豆脫去水份,表皮起皺發霉長出長長的絨毛后,才轉移到醬壇里去。這時就開始放調料,鹽、花椒葉、花生、八角是必不可少的,與別的人家放進一兩個饅頭不同,母親每年都會特意挑兩個皮薄瓤紅的大西瓜,去皮后把西瓜瓤放進去,這樣做出來的醬味道很鮮、顏色也會更漂亮。調料放進去后,攪拌均勻,封壇再曬。封壇時,先蒙一層白粗布,外面再套上一層薄塑料布,最后用粗皮筋繞著壇口拴上幾圈密封嚴實,制醬算是完成了三分之二。此后,還要經過數次翻曬,把表面起霉醭的黃豆攪拌到壇底,曬上二十多天,黃豆醬就可以品嘗了。
把切好的蔥花爆香,放進黃豆醬翻炒,不放任何調味品,那種香味就已令人垂涎。做炸醬面,放肉沫進去,翻炒片刻放黃豆醬炒香,加水做鹵,燒開后再用小火慢熬。面條煮沸后,根據個人口味選擇過水或不過水,撈到碗里加鹵汁、切好的細黃瓜絲、再配上幾個蒜瓣,那是我這種喜吃米飯的人最想念的面食。
弟弟畢業后也留在洛陽,和所有的上班族一樣,只有長假時才有空回趟家,團聚時間,一年下來也就三五天。我有家庭和孩子后,因路途遠,孩子又暈車,已經三年多未回家,家鄉的村落、炊煙、小河、窄窄的土徑只在夢里偶爾出現。
上個禮拜六,弟弟回老家補辦身份證,愚鈍的我竟然沒想起快到中秋,買上兩盒月餅讓弟弟捎回去。弟弟臨來洛陽前,母親打電話給我,說是讓弟弟給我帶些黃豆醬和辣豆。我告訴母親這里超市買黃豆醬很方便,不用麻煩。母親卻再三堅持,說放進食品瓶子醬不會灑出來,體積也小好攜帶,一定要給我帶兩份。還說快到八月節了,要買上一箱月餅給我兒子。
下班回家后,推開門,就看見放在客廳茶幾上滿滿兩瓶醬,邊上還放有一只蘋果,兩袋火腿腸。急不可耐地去洗了洗手,打開冰箱拿出兩個冷饅頭,倒上一杯開水,擰開瓶蓋就吃起來。熟悉的母親味道,熟悉的場景,我幾乎流著眼淚吃完了兩個饅頭。想起上大學時,每次返校,母親總會在我行李包里塞上一兩個蘋果,說是“平平安安”的意思,然后再放些自家炒的熟花生,自己鹵的茶雞蛋,一兩包火煺腸,每回我都是極不情愿地背上這些沉甸甸的東西,心里還直埋怨母親多事。
在母親眼里,我依舊是那個乳臭未干的小丫頭,雖然現在我已經是個三歲孩子的母親。
在我印象里,母親從沒有和我促膝談過心,也沒有嬌慣過我,她給我的感覺就是固執、嚴厲、脾氣沖。從小我就很怕她,直至我工作后,我才敢反駁她的意見,說出自己真正的想法。在一次次與母親的“斗爭”中,我由最初的下風轉為上風,以至到來后來,就算我認為她的觀點是對的,我也會不理智地否定她,母女往往鬧得不歡而散,數月不通電話。
以前,看到母女情深的電視劇都會為自己和母親之間生疏的關系流淚。越是得不到就越想得到,然而溝通時卻總會因為三言兩語再次引發沖突。冷戰后一方“求和”時卻又受不了對方的冷淡而愈加痛心,造成一種惡性循環。
這些年,我們母女就是這樣詮釋感情的。我痛苦傷心過,母親肯定也是一樣,我們都苦于找不到合適有效又不違本心的方法。直至我看到母親讓弟弟從700多里外帶來的黃豆醬、蘋果和火腿腸,才明白母親的愛一直都存在,就在那些我以前不注意、忽略的黃豆醬里。
責任編輯 譚 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