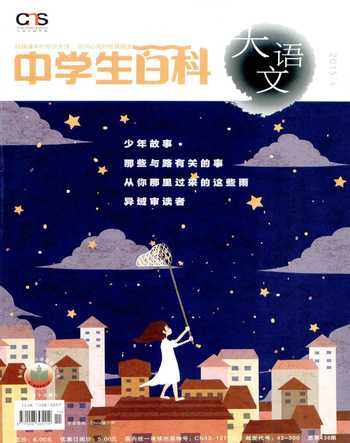回家路上好風光
徐昌才
希臘神秘哲學家說過這樣一句話,人生不過是居家,出門,回家。文化昆侖錢鐘書亦言,我們一切情感、理智和意志上的追求或企圖不過是靈魂的思家病,想找著一個人,一件事物,一處地位,容許我們的身心在這茫茫漠漠的世界里有個安頓歸宿,仿佛病人上了床,浪蕩子回到家。我想說,對于詩人來講,一路顛簸,一路折騰,經歷了多少風霜雨雪,飽受了多少冷暖炎涼,能夠回家,不管以怎樣的形式,都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情,都讓人感慨唏噓。讀一讀那些寫于人生旅途的詩歌,聽一聽那些長路浩浩的吟唱,你會覺得人生有家多么歡欣,人生回家又是多么傷感。
八十二歲的老詩人賀知童好不容易告老還鄉,看見孩童的真誠相問,不禁感慨萬千,悲從中來。其詩《回鄉偶書》寫出了一個老詩人回家路上的心酸與苦澀。
少小離家老大回,
鄉音無改鬢毛衰。
兒童相見不相識,
笑問客從何處來。
人生道路坎坷曲折,回家旅程山水迢迢,詩人舍去萬千風物不說,只選取回到家鄉村口的一個片段入詩,道盡萬千艱難,抒發人生苦樂。可以想見五十多年前,詩人年輕氣盛,懷抱遠大,離開家鄉,離開親人,不識離恨,不懂鄉愁,大有“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氣概。可是,到如今回到家鄉,詩人已是兩鬢衰殘,白發蒼蒼;這張臉,飽經風霜,布滿皺紋;這副身板子,彎腰曲背,瘦弱不堪;這雙腳,步履緩慢,行走艱難;還有這雙手,十指瘦長,筋骨畢露。歲月無情留下滄桑印記,宦海奔波蒼老憔悴的心。
眼前這些兒童,看著我這個步履蹣跚、老態龍鐘的大爺,一個個好奇興奮,一個個驚訝不已,問我,大爺,您從哪兒來?您要找誰啊?經小孩這么一問,老詩人真是哭笑不得。是啊,我什么時候成了家鄉的客人?我為什么會成為家鄉的客人?家鄉沒有我的日子里又該發生了怎樣的變化?親朋舊友都還健在嗎?村里還有多少年輕人不認識我這個老頭?回家令人高興,但是太多的牽掛和憂念又讓人忐忑不安,就像宋之問《渡漢江》所寫:“嶺外音書絕,經冬復歷春。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詩人既高興又不安,既急切又遲疑,站在原地,對視小孩,久久說不出話來。滿腹鄉情,太過沉重,太過糾結,縈繞詩人苦澀的心靈,纏住詩人艱難的步履。這條回鄉的道路,詩人用一生的時光來走,走得多么艱難,多么沉重。
唐代詩人戴叔倫漂泊異鄉,看到山水蒼茫,秋風漸起,心中不禁萌生濃濃的思鄉之情。其詩《題稚川山水》這樣寫道:
松下茅亭五月涼,
汀沙云樹晚蒼蒼。
行人無限秋風思.
隔水青山似故鄉。
游子漂泊在外,羈縻難歸,因秋風忽起而無限思鄉,竟把他鄉異地青山綠水當作是自己遙不可及的故園風光,足見思鄉之切,歸情之急。青山綠水,亦真亦幻,似曾相識,撲面而來。思鄉之情如秋風浩蕩,彌漫他鄉天地;思鄉之情如秋水潺湲,凄清敏感的心靈。詩人行走在遙遠的異地,滿目所見卻是故鄉的風光,滿心承載卻是沉重的鄉愁。這條路綿延在天邊,卻一直指向遙遠的故鄉。
比戴叔倫更凄苦、更想家的唐代詩人武元衡也是漂泊在外,則以一首《舂興》寫盡夢魂飛越的辛苦,道盡游子思鄉的急切。
楊柳陰陰細雨晴,
殘花落盡見流鶯。
春風一夜吹鄉夢,
又逐春風到洛城。
一、二兩句描寫異鄉景色。暮春時節,細雨初晴,楊柳褪去了鵝黃嫩綠,變成蒼蒼翠翠;枝頭殘花已在雨中凋零殆盡,幾只黃鶯站在枝丫上面啼叫,聲聲飄蕩,聲聲觸動游子的心懷。三、四兩句出語平易自然,想象新奇美妙,上句寫春風吹夢,下旬寫夢逐春風,使人聯想到那和煦的春風,像是給入眠的思鄉者不斷吹送故鄉春天的信息,這才釀成了一夜的思鄉之夢。而這一夜的思鄉之夢,又隨著春風,飄飄蕩蕩,飛越千山萬水,來到日思夜想的故鄉——洛陽城。思鄉之情宛如縹緲的春夢,因風而起,萬里飄飛,直奔洛陽。對于詩人來說,回鄉之路雖然千里迢迢,但是夢魂飛抵卻又輕而易舉。真不知道是替詩人高興還是悲傷。
回家的路漫長,正如人生旅途的遙遠,充滿了坎坷與艱辛,但是,也有歡欣,也有溫暖。唐代詩人于鵠《巴女謠》就以清新的筆調描繪一幅老牛暮歸,巴女唱晚的鄉村圖景.和諧寧靜,意味深長。
巴女騎牛唱《竹枝》,
藕絲菱葉傍江時。
不愁日暮還家錯,
記得芭蕉出槿籬。
夏天的傍晚,夕陽西下,煙靄四起,江上菱葉鋪展,隨波輕漾,一個天真伶俐的巴江女孩,騎在牛背上面,高聲唱著當地歌謠,沿著江邊彎彎曲曲的小路,慢慢悠悠地回家去。天色漸漸晚了,這個頑皮的小姑娘還是一個勁地歪在牛背上面唱歌,聽任老牛不緊不忙地踱步。路旁好心的人催促她快些回家,要不待會兒天黑下來,就找不到家門了!沒想到這個小姑娘不以為然地說道:我才不怕呢,只要看見那些伸出木槿籬笆外面的大大的芭蕉葉子,那就是我的家了!
事實上,木槿入夏開花,花色燦爛,芭蕉伸展,濃綠逼人,這些都是川江一帶農家住房四周的常見景物,家家如此,不足為奇,更不能以之當作辨認家門的標志。但是這個小女孩偏偏要如此炫耀,而且還不慌不忙,自信滿滿,什么原因呢?除了小女孩對家鄉、對生活的熱愛之外,關鍵是詩歌首句提到的那頭牛。我愿意相信,那是一頭老水牛,小女孩放牛多年,與它相依相伴,感情十分融洽,騎牛而歌就是明證。
古代有個成語叫”老馬識途”.結合這首《巴女謠》描述的情況可改為“老牛識途”,這頭牛像川江百姓一樣,也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熟悉這方山水,熟悉大小路徑,熟悉它的主人,天再黑,路再遠,它都不怕,它都能找到回家的路。有了這位老朋友的指路、帶路,小女孩還有什么擔心的呢?倒是路旁好心人的善意提醒顯得多此一舉。這首詩中,牛是安詳的,慈愛的,悠閑的,富于智慧的,像一位白胡子老大爺,疼愛自己的孫女,讓她歌唱,任她頑皮,和她一起走夜路,走了一千年,一直走進我們的生活。
對于詩人而言,離開家園和回到故里都是一道優美的風景。離開親人,走向異域他鄉,詩人心中時刻裝滿故鄉的一草一木和一山一水;回歸家園,團聚父老鄉親,更可共享天倫,安頓心靈,沿途的所見自然也是風光無限,引入入勝。唐代詩人王建的詩歌《江陵使至汝州》就記錄了詩人暫別家鄉,遠赴異地,又回歸故里,歡欣鼓舞的特殊心情。筆調清淡輕快,情意綿綿如水,讀之余味悠長,思之心有戚戚。全詩是這樣寫的:
回看巴路在云間,
寒食離家麥熟還。
日暮數峰青似染,
商人說是汝州山。
詩寫回程見聞,傾瀉歡快心情,有幾個地名很關鍵。王建家居穎川(今河南許昌),出使江陵,離家幾月,又返回故鄉,途經汝州(今河南臨汝縣),看到美麗風光,聽說又快回到故鄉,即興寫下了這首詩。汝州離許昌很近,到了汝州也就意味著很快就到許昌,詩人回家的心情自然是非常激動。首句回望來路,喜不自勝。巴路指通向江陵、巴東一帶的道路,江陵是詩人此行的目的地,汝州是詩人返程途中的一個停靠點,兩地相距遙遠,千里迢迢,詩人趕了一天的路,落日時分,回望巴路,只見白道如絲,一直向后方蜿蜒伸展,最后漸漸隱入云間天際。身后的道路伸向云天,當然是詩人極目千里的風景一線,也是詩人把漫漫長途拋卻云外而歡欣鼓舞的形象暗示。
次句瞻望前路,計算歸期。幾個月過去了,如今回來,尚未到家,想象中,家鄉郊野田間壟上,應是麥穗成熟,金黃一片了。離開的時候,是陽春三月,風光如畫,回來的時候是金秋時節,豐收在望,不管是離開還是回來,不管是春天還是秋季,家鄉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迷人的。
三、四句輕描青山,暗傳喜悅。回家的路越走越近,回家的心情也越來越急切。傍晚時分,落日返照,前方隱現幾座青山,像經過丹青妙手濃墨染過一樣翠綠迷人,詩人迫不及待地問,到了什么地方了?同行的商人毫不經意地回答,那就是汝州附近的山了。筆者喜歡這種說者無意,聽者有心的詩句。貌似輕描淡寫,波瀾不驚,其實心潮涌動,急如星火。商人出沒風塵,來往奔波,對這一路風景,早已了如指掌,毫不在意,不過就是到了汝州嘛,有什么值得大驚小怪的呢?可是詩人的感覺大不一樣,汝州一到,離家鄉許昌自然不遠,對于歸心似箭、火燒火燎的詩人來說,知道這一點,豈不更高興,更激動?
回家路上,最歡暢,最快意的當然要推唐代大詩人李白,其詩《早發白帝城》寫盡了一個詩人從戴罪之身到獲得自由的狂喜與豪放。
朝辭白帝彩云間,
千里江陵一日還。
兩岸猿聲啼不住,
輕舟已過萬重山。
李白因永王磷案,淪為罪人,流放遙遠的夜郎,取道四川赴貶地。行至白帝城,忽聞皇上大赦天下,李白重新獲得自由,立馬從白帝城出發,沿長江三峽東下,直奔湖北江陵,那里有他的妻兒子女。千里行程,詩人一路歡歌,一路飛奔,可謂心花怒放,神采飛揚。身子和心靈一般飄逸,行程和山水一樣飛舞。你看,詩人回家,千里迢迢,好不風光。告別白帝城,是彩云繚繞,氣象萬千;走千里行程,是猛浪若奔,飛舟似箭;聽高猿啼鳴,是聲聲不盡,歡歌樂唱;駕一葉輕舟,是風馳電掣,萬山奔騰。高江急峽見證李白的自由與豪邁,舟飛猿啼折射出李白的幸福與快樂。對于重獲自由的李白來講,千里歸程,早發夕至,一路風光,一路歡暢!
唐代大詩人杜甫曾經為戰亂阻撓,困守西南天地之間,思歸而不得,盼親而不至,驚聞大唐官軍平定叛軍,收復失地,無比激動,立馬打點行裝,準備回家,回到久別的親人身邊。其詩《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就描繪了詩人想象回家的歡悅與幸福:
劍外忽傳收薊北,
初聞涕淚滿衣裳。
卻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詩書喜欲狂。
白日放歌須縱酒.
青春作伴好還鄉。
即從巴峽穿巫峽,
便下襄陽向洛陽。
初聞喜訊,老詩人淚雨滂沱,悲喜交集。悲乾坤顛倒、黎民蒙難,喜噩夢過去,天下太平。寫妻子笑逐顏開,喜氣洋洋;說自己漫卷詩書,喜不自勝。想到立即回家,與春天同伴,帶喜悅上路;想到歡慶勝利,白日也要放歌,老病也要暢飲。詩歌最后兩句交代詩人回家的旅程,四嵌地名,變換畫面,迅疾飛馳,一閃而過,足以看出詩人的欣喜若狂,歸心似箭。從“巴峽”到“巫峽”,峽險而窄,舟行如梭。出“巫峽”到“襄陽”,順流而“下”,急駛如風。從“襄陽”到“洛陽”,改換陸路,直奔故地。千里迢迢,順風順水,且歌且樂。不難想見,飽經顛沛流離之苦、烽煙阻隔之難的老杜該是何等疏狂,何等歡悅。
人生一世,免不了行走山川,奔波天涯。出去是為了回來,回來交織著悲喜,跌宕起伏,來去不定,這就是人生。有起點,有終點,但更多時候,我們和詩人一樣顛簸在路上,也許功成名就,衣錦還鄉;也許落魄潦倒,一貧如洗;也許滯留他鄉,形影相吊;也許一帆風順,快意無比。但是不管怎樣,踏上漫漫長路,回歸故鄉,安頓心靈,這是我們內心深處永恒的呼喚。正如現代著名作家沈從文所言,一個戰士,不是戰死沙場,就是回歸故鄉。人生無異于一個戰場,勝利了要與家鄉分享,失敗了需要得到家鄉的撫慰,即便葬身他鄉異地,也要像王昭君一樣“獨留青冢向黃昏”。大唐詩人走過萬水千山,閱盡人世滄桑,用詩歌記錄一路的艱辛和欣喜,描繪回家的悲戚與幸福,于是,千百年之后,我們還聽到生生不息的吟唱,還看到多姿多彩的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