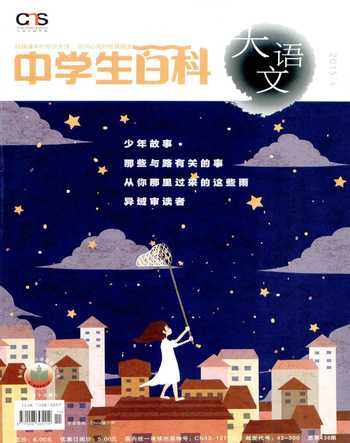通識教育還是專業(yè)知識?這才是個問題
短發(fā)小姐
羨慕美國校園電影里畢業(yè)舞會的場景?渴望提起行李飛到大洋的另一邊開始新的生活?想要和全世界的年輕人站在同一高度?別著急,你可不是唯一的一個。隨著傳媒和網絡的日益發(fā)達,信息流通的廣度和速度都今非昔比,交流變得越來越容易,我們開始了解世界,世界也開始了解我們。如今,留學不再可望而不可即。留學是不是真的像想象的那么美好?到底該不該選擇留學這務道路?要去留學你準備好了嗎?那就讓我先來說說自己和身邊朋友的留學故事,讓你自己來決定!
“生存還是毀滅,這才是個問題。”哈姆雷特王子在莎士比亞的筆下,發(fā)出了震撼自己人生和整個世界的怒吼。同樣的問題也擺在教育面前。教育的意義是什么?是通識教育還是專業(yè)知識?將這個選擇稱為橫亙千古的難題也不為過。
通識教育又稱文理教育,英文為liberal artseducation.字面意為“自由藝術教育”,起始于古希臘羅馬時期。那時候,人們相信,教育是為了成就更完整的人,從而建立起一個完善的公民社會。這意味著人人都能參與公共討論,在法庭為自己辯護,成為法庭評審團中的一員,并且通過服兵役來保家衛(wèi)國。文理教育的核心課程由三個部分組成,分別為語法,修辭和邏輯。除此之外,算術,幾何,音樂理論和天文也包含其中。而文理教育的最終目的,是幫助每個人獲得真正的自由,這就是“自由藝術教育”名字的由來。當然,在古希臘羅馬時代,人人平等還只是個夢想,奴隸和女人被剝奪了投票選舉的權利,被拒在文理教育之外,沒有真正的自由。
而在機會越來越多的今天,高等教育不再是少數(shù)人的權利,文理教育有了新的含義。今天我們討論的文理教育指的是以古希臘羅馬為藍本的本科或者研究生課程。在這樣的課程中,學生不再被學科之間的邊界所限制,思維的拓展和思想的碰撞可以跨過文科和理科的界限。文理教育在美國非常盛行,耶魯大學的文理教育課程非常聞名,而哈佛大學也有為研究生提供的文理教育課程。在國內,北京大學的博雅學院正是一個例子。
而與文理教育相對的則是專業(yè)和職業(yè)教育。隨著工業(yè)革命,社會的生產力大大增加,經濟發(fā)展和物質生活水平成為重中之重。隨之產生的是對專業(yè)人才的需求。如何在分工越來越細,越來越專業(yè)的工業(yè)社會充分地利用人力資源成了新的難題。同樣,教育的目的也發(fā)生了質的改變。如何自由地生活不再那么重要,而掌握一技之長,迅速找到工作,在事業(yè)上一步一步攀升成了每個人考慮的重點。職業(yè)教育隨之產生。今天我們所熟悉的大學學科,便是這樣歷史發(fā)展下的體制。
那么高等教育何去何從?作為即將面臨這個選擇的我們要如何做決定?追求自由和掌握專業(yè)知識一定是矛盾的嗎?讓我們來看看這幾個來自世界各地的小伙伴們怎么說吧。
瑞婭,新加坡人,19歲,耶魯新加坡國立大學學院
瑞婭坦誠地告訴我們,耶魯新加坡國立大學學院(簡稱耶魯國立學院)剛剛建立的時候爭議不斷。新加坡是個以商業(yè)貿易起家,重視科技研究發(fā)展的國家。作為一個以華人為主的社會,新加坡主流社會認為專業(yè)和高效才是最重要的,以文理教育為本的耶魯國立學院并不符合這個國家的主旋律。除了國家發(fā)展的考量,文化的差異也為美國耶魯大學和新加坡國立大學這兩所世界頂尖學府的合作增加了難度。美國耶魯大學的學生游行抗議新加坡缺乏學術自由,而新加坡人則對耶魯大學的批評嗤之以鼻。即使合作并非一帆風順,雙方還是堅定地完成了世界高等教育進程上的新篇章,將源于西方的文理教育帶到有著悠久歷史并且正在重新崛起的東方。這樣的文化交融和碰撞帶來無限可能,讓人期待。
在介紹自己在耶魯學院的體驗之前,瑞婭與我們分享了她的成長經歷。她降生在一個由非洲父親和新加坡馬來族母親組成的家庭,從小就習慣了文化的交融。現(xiàn)在,作為耶魯國立學院的新生,她感受到了西方文理教育下的學術自由,也有機會參與為耶魯國立學院特別設計的專門研究亞洲社會和文化的科目。
瑞婭向我們強調耶魯國立學院中西結合的重耍性。質疑文理教育的聲音提出它太以歐美文化為中心。大部分文理學院所強調的哲學著作,從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到黑格爾的唯心主義哲學,到羅索的西方哲學史,無不是西方哲學體系下的產物。而源自東方的孔孟之道,日本禪學和古印度的吠陀經卻不見蹤影。耶魯國立學院正是在文理教育普遍以歐美價值體系為重的情況下中西結合的產物。
對于瑞婭來說,最有趣的莫過于在一個國際化的集體中學習和生活。在2011年學院開始招收第一屆學生的時候,收到了來自全球13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的入學申請。從小在新加坡長大的瑞婭雖然對多文化交流并不陌生,但是和這么多來自不同國家背景的同學在同一個空間里成長,這還是第一次。不過,這也正是新時代的文理教育的目的之一,讓二十歲的年輕人走出自己狹隘的空間,去迎接全球化下的新的挑戰(zhàn)。
為了讓來自世界各地的留學生適應新加坡,也同時讓新加坡學生接受一個多文化的氛圍,耶魯國立學院每年邀請15位來自頂尖美國文理學院和新加坡國立大學的畢業(yè)生擔任“學長”的角色。這些年輕人在課堂上,和新生一起學習,一同活躍課堂討論的氛圍。在住宿生活中,他們則充當知心朋友的角色,和新生一起發(fā)起學生組織活動,提供自己的經驗。在耶魯國立學院這樣的學校,他們最重要的職責,是在這個多文化的環(huán)境里,在可能因文化差異而出現(xiàn)誤會的情況下,幫助學生們互相理解。
當然,耶魯國立學院并不是完美無瑕的。作為第一個東方和西方結合的文理學院,又因為來自兩所頂尖學府,耶魯國立學院注定要面對國際上的壓力和爭議。文化交流,聽起來是一個很美的詞語,卻可能因為一不小心在實際生活中造成很大的麻煩。比如,不同文化中的人們關于空間和隱私的不同概念,導致同一屋檐下的學生們彼此誤會。又或者,來自一個人家鄉(xiāng)的美食,卻讓另一個人無法忍受,這又如何是好?想要去非洲做慈善事業(yè),或者成為華爾街的銀行家,你能不能包容他人不同的夢想?
聽起來也許不簡單,成長也不是一帆風順的。最重要的是,像瑞婭一樣的年輕人在這樣的環(huán)境里幾經歷練,終究將成為更加包容的自己。
梧桐,中國人,23歲,從美國布明大學畢業(yè),現(xiàn)在一家國際咨詢公司工作
梧桐曾經就讀的布朗大學,雖然在國內不如哈佛和耶魯?shù)拿麣猓诮逃鐓s鼎鼎有名。它以自由著稱的學術氛圍,更是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學子。2014年時將近3萬高中畢業(yè)生申請入學,僅有不到10%的學生拿到入學通知書,競爭異常激烈。梧桐去美國想要的就是自由求真的學術精神,她終于如愿以償。在美國,大學入學并不是靠高分就能萬事無憂。除了優(yōu)異的學術表現(xiàn),還需要有豐富的課外活動和競賽能力。
“其實不需要太擔心,做自己就好了。畢竟,在全世界更發(fā)達國家的教育系統(tǒng)中,學生和學校是個互相選擇的過程。這也體現(xiàn)了西方教育和人文關懷中的自由吧。”梧桐笑著說。
就業(yè)是國內家長和學生關心的重點,也常常作為對文理教育的質疑。在這一點上,梧桐有話要說。首先,現(xiàn)在的文理教育不再完全按照古希臘羅馬的方式全心攻讀名著經典。美國高等教育最普遍的模式是前兩年新生不受學習科目的限制,修讀包括人文和科學的學科。但在第三年開始,學生將開始決定專業(yè)并且修讀相關科目。梧桐所修讀的國際學范圍很廣,但她也有同學專心于醫(yī)藥和法律。其次,如今在就業(yè)中,專業(yè)知識不再那么重要。全球化高速發(fā)展的今天,現(xiàn)在學習到的專業(yè)知識,兩年之后就會過時。如何在泛濫的訊息中尋找收集到最有價值的信息,就是新時代人才所面對的挑戰(zhàn)。有意思的是,不受學科的限制,提出問題,并且通過不同的途徑尋找答案,這恰恰是文理教育的強項。
美國的文理教育非常的多元化。很多精致并且非常有特色的文理學院仿佛埋藏在沙漠中的寶藏,不張揚,卻各有各的歷史和故事。梧桐還和我們分享了兩個她當初申請的學校。其中一個是圣約翰學院。這個學校完全是古希臘羅馬文理教育的傳承者。每個學生都修讀一樣的四年大學課程,其中包括閱讀哲學經典,修讀希臘語和法語,在星空下學習天文學。而每堂課都必須面對的討論形式,時刻挑戰(zhàn)著學生對知識的理解,不能有絲毫松懈。而漢普郡學院,則是文理教育的另一個先鋒。這里的學生掌握了自己教育的自主權,他們設計自己的科目,有自己的導師,還可以使用馬薩諸塞州五校聯(lián)盟的強大的網絡資源。可以說漢普郡的學生,沒有一個人的專業(yè)是相同的。這些文理學院雖然各不相似,自由求真的精神卻無一例外。
美國文理學院的弱點,恐怕就是太以歐美價值體系為中心。梧桐笑著說,一些美國人并不了解東方,也不知道亞洲人之間的差異,還以為只要是西方的,就是最好的。文理教育以西方為中心的模式需要改變,文理教育求真的精神卻更重要了。“起碼,我的美國同學并不會因為不了解東方而避開這個話題。他們反而抓著我好奇地問東問西。”
保羅,荷蘭人,22歲,阿姆斯特丹大學學院畢業(yè),現(xiàn)在攻讀物理工程碩±
保羅剛畢業(yè)的阿姆斯特丹大學學院是由阿姆斯特丹兩所高校,阿姆斯特丹大學和自由大學共同提供師資力量建立起來的文理學院。比起那些歷史悠久的高等學府,它確實年輕,才成立五年而已。可是無論從師資力量還是教學設施來說,它都毫不遜色。以全英文授課,一半外國學生的國際化作為特色的阿姆斯特丹大學學院也是全荷蘭最難進的學校之一。除了成績之外,面試也是必不可少的,以保證每個學生都是校園中積極的一員。為了增進多元化,學校還為國際學生提供豐厚的獎學金,以保證他們全身心地體驗阿姆斯特丹的生活,并且最大程度地參與校園活動。
有人認為,文理教育僅僅是人文科學的教育。阿姆斯特丹大學學院就提供了有力的反駁。學院的理念,就是以自然科學為學院特色,為學生提供全面的教育。保羅自己也正證實著文理學院的學生既有通識教育的廣度,又有專業(yè)知識的深度。專業(yè)是物理和計算機的保羅常常出入阿姆斯特丹大學和自由大學的實驗室,和這些大學的學生一起共享研究型大學的資源。在大學學院強大的就業(yè)網絡的支持下,保羅先后進入銀行和研究所實習。畢業(yè)之后,覺得還是想要專心研究物理,成為了一名物理工程碩士。
“有人問我為什么要選擇文理教育,這條看上去耗時更久的道路。我卻不認為文理教育讓我走了彎路。恰恰是文理教育的多元化,讓我忠于自己,不被學科之間的界限所束縛,嘗試不同的領域,終于發(fā)現(xiàn)我的熱情是物理研究。這樣我才能專心致志地走自己的路。”保羅認為進入大學學院是自己做過的最正確的選擇了。
如果非要說個缺點,那么恐怕就是文理學院通常都很小,因為它們致力于提供高質量的教學,保證有足夠多的教授能給與學生關注,幫助他們成長,而不單單只是打分走人。學院很小的原因還在于阿姆斯特丹大學學院為每位學生提供住房,讓他們不但一起學習,更一同共享生活空間,真正成為朋友和伙伴。在新的理工科學校讀碩士的期間,保羅常常想念大學學院開心的時光,他堅定地認為,文理教育的四年讓他獨立求真,勇于面對任何挑戰(zhàn)。即使偶爾有面對專業(yè)知識稍有欠缺的情況,他也能馬上查找資料,向教授求證,高效快速地解決問題。
“畢竟,知識可以隨時學習。而求真的精神和對事物的熱情卻非常難得。”保羅若有所思地說。
文理教育,何去何從?
你也許并不覺得文理教育有什么吸引人的,你的父母也許一直念叨著要你進入最好的大學最熱門的專業(yè),我們所生活的時代也總是追追趕趕,生怕落在人后。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教育的意義?你想要過怎么樣的生活?在這個以資本積累作為游戲規(guī)則的社會,人要怎樣存在?我們不一定要選擇文理教育來追求自由求真的精神。但我們需要和這個紛紛擾擾的世界保持一點點距離。這樣,我們才有獨立的思想,和真正的靈魂,不至于在關鍵的時刻,人云亦云,失掉了做人的準則。
我想,文理教育,不一定是四年高等教育的選擇,而是我們所選擇的生活方式,和我們想要成為怎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