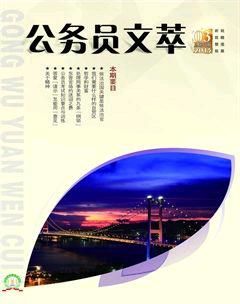依法治國關鍵是依法治官
葉竹盛
年過八旬的郭道暉是學界美稱“法治三老”之一。郭道暉早年參加革命,是解放前清華大學地下黨組織的成員。解放后留校工作,擔任清華大學黨委委員,但是在“反右”和“文革”中受到沖擊。改革開放后,郭道暉調入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參加立法工作和法學研究,參與了八二憲法和《民事訴訟法》等重要法律的起草工作。1989年后,郭道暉擔任法學界的權威雜志《中國法學》主編,發起、參與和弘揚了重大法治話題的討論。
郭道暉近年來頻繁在大眾媒體上撰文、接受采訪,是因為感覺到推動法治進步僅在法學界內部發聲還不夠,還應該面向社會,給社會啟蒙。他認為要建立法治國家,必須以法治社會為基礎,要打破過去那種國家和社會一元化的局面,給社會權力更大的發揮空間,以法治社會來推動法治國家的改革和進步。
“領導指示不可違,憲法違反無所謂”
《南風窗》:改革開放之初,法治建設的最大阻力可能來自于舊觀念和舊思維。例如1979年制定《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時,一些高層領導就認為引進外資相當于復辟租借、出賣國土。應該靠什么來突破舊思維舊觀念的阻礙?
郭道暉:制定這個法律時,我剛好調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當時王漢斌(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副秘書長)找到我,要我寫個材料,談列寧怎么論租讓制。當時這個法律遇到很大的阻力,彭真(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就要求借用列寧和蘇聯的經驗來說服反對者。我查閱材料發現列寧曾指出,“如果我們不善于把外國資本吸收到租讓企業中來,就不能改善我們的經濟狀況。這雖然意味著會‘發展資本主義,但并不危險,租讓制只是一種租借合同,資本家只是在一定期限內是一部分國家財產的承租者,不是所有者,所有權仍屬于國家。”列寧的論述有助于消除引入外資的爭議。通過這個辦法,最后一些領導人的顧慮消除掉了,這部法律也就順利通過了。
因為舊思維和舊觀念,改革初期鬧的笑話還不少。例如當時由交通部起草《海上交通安全法》,部長拿著草案參加討論咨詢,草案中有一條規定,海上安全警察有違法行為也不受司法起訴與審判,他們應該例外。參會人員問,他們為什么能例外。部長回應說,警察頭戴大蓋帽,上面有國徽,審判他們不就是審判國徽嘛。他堅持要加入這條,后來還是彭真做的工作,才拿掉這條。
另外是1983年“嚴打”的時候,當時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天就要閉幕了,臨時收到《關于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和《關于迅速審判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決定》的草案。常委會很不滿意,早不來晚不來,我們要閉幕了你們才來,但是也沒辦法,還是匆忙通過了這兩個決定。“嚴打”的決定有很多后遺癥。當時《刑事訴訟法》規定,一審以后,有10天時間考慮上訴。嚴打的第二個決定中規定,上訴時間縮短為3天,實際上剝奪了被告的辯護權、上訴權,違反了憲法精神。當時社會治安的形勢比較嚴峻,所以才開展“嚴打”,但是“嚴打”也受到了“文革”遺留觀念的影響,比如規定要殺多少人,這是從“三反五反”開始的“傳統”。人不夠就要抓人湊數。比如說當時有流氓罪,抓到人,就算事情不大,也是槍斃。“嚴打”假如要重新審查的話,錯殺的人還真不少。
糾正這些問題最有用的辦法就是違憲審查,但是我在全國人大那些年,從來沒有見過常委會行使撤銷違憲法律法規的權力。假如發現某個行政法規不合適,有違憲違法的嫌疑,并不是根據規定撤銷,而是派一個法工委的干部和國務院的領導口頭打招呼,“唉,你那個行政法規有問題,趕快改一改”,以免傷面子。由于缺少違憲審查,憲法沒有權威,導致很多干部錯誤地認為,領導指示不可違,憲法違反無所謂,因為違反憲法不會受到懲處,而違反領導指示,官帽就有危險。
邁向實質法治階段
《南風窗》:如果說改革開放早期法治建設的最大阻力來自舊思維和舊觀念,當下的最大障礙來自哪里?
郭道暉:當前最大的障礙可以說是這十來年形成的權貴資本集團,或者說特殊利益集團。他們成為改革的阻力,或者說是把改革綁架了,朝有利于他們的方向改。現在習近平總書記講得很好,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依憲就是突出憲法的權威。法律也好,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違反憲法就要撤銷。現在有些行政法規,甚至一些規章、紅頭文件,要么超越了憲法法律規定的內容,要么超越憲法規定的立法程序。沒有法律首先制定法規,這是越權立法。還有侵權立法,一些法規規章不是保障公民自由、保障公民權利,而是侵犯公民權利。比如說過去有《拆遷條例》,規定在司法沒有做出審判以前,也可以去強拆,這就造成既成事實了。這樣的條例完全有利于地方政府和“土豪”(笑)。假如要改革就要侵犯他們利益,他們肯定不愿意。
《南風窗》:十八屆四中全會的《決定》強調,要健全憲法實施和監督制度,完善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憲法監督制度,健全憲法解釋程序機制。若總結過去30年的經驗,如何才能沖破特殊利益集團的阻礙?
郭道暉:現在要用“打老虎”的精神,根據憲法,違憲必究,建立違憲審查的機構和制度、程序。這次四中全會已經提到了,接下來我們要研究建立怎樣的憲法監督機構。法學界早就有很多建議。比如有人提出可以由最高人民法院進行違憲審查,或者在全國人大設立憲法委員會。我的建議是,政協也是我們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也應該賦予他們一些實際的權力,可以賦予政協提請人大常委會進行違憲審查的提案權。政協的成員主要是知識界精英和退休的官員,賦予他們提案權,地位比較超然,也完全有這個能力。
《南風窗》:十八屆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的《決定》中包括了大量法治改革的舉措,要實現這些改革目標,需要什么條件?
郭道暉:四中全會的規定,我覺得總體上是好的,列出了180多項具體改革,說明并不是講空話。當然還要看舉措本身能不能形成制度,形成能夠執行的措施。如果把180項都落實了,法治就前進了一大步。假如這樣做了,中國的法治就可以說是從形式的法治進入了實質的法治階段。改革開放初期有一個16字方針——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這是從無法到有法。但是當時沒有討論“什么法”,是民主的法還是專制的法。現在要依憲執政,就是首先要依憲立法,要遵守公平正義這些原則,保障公民權利,限制國家權力。如果這些原則都能得到實施,我們的法治就能上一個臺階,甚至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這些都有待觀察,有待努力,而且有待克服那些反對改革的阻力。
《南風窗》:改革的阻礙者未必會自動退出,并且新一輪法治改革的涉及面更廣更深刻,那么應該如何保持改革的動力?
郭道暉:要真正落實和推進中國的法治建設,我的觀點還是要真正建立法治社會。這個問題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提出了,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要一體建設。實行改革開放到市場經濟以來,國家和社會已經二元化了。過去是一元的,社會是國家的社會,國家就代表社會,社會沒有獨立的地位,也沒有掌握獨立的資源,一切資源都在國家手中。市場經濟后,社會也掌握了一定的資源,包括物資資源、文化資源、精神資源等等,就對社會對國家有影響力有支配力。
假如說能夠依靠社會,以它為基礎和動力,推動法治國家的建設,推動法治國家的改革,去打破利益特權集團的阻力,我們就有希望。現在老百姓也在成長,當領導比以前不容易,因為他們面對的不是過去的順民、子民,不是那種聽話的群眾。現在是懂得法治,懂得自己有哪些權利,積極參與國家政治的群眾,所以不是很好領導。作為領導人,作為執政黨,都要與時俱進,所以現在提法治思維法治方式就很好。
要依法治官依法治權
《南風窗》:怎樣才能激發出社會力量?
郭道暉:四中全會雖然提出了法治社會的說法,但是我覺得討論還不夠。現在很多人,包括一些領導人和干部,把法治社會理解成教育公民守法,把法治社會僅僅當作一個守法的社會。當然守法社會是法治社會的一個前提條件,是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現代社會是民主、自治、法治的社會,它不僅要用法來管理自己,包括國家的法、社會的習慣等等,而且要管理國家、監督國家。馬克思講公民權就是公民參與國家事務的權利,公民就是“公人”——公共的人,公民權利必須得到保障,公民反過來要管政府。后面這個意義沒有討論,被規避了。以社會權力來監督國家權力,這樣來理解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會的一體建設才是完整的。社會權力要補充國家權力沒有做的或者不愿意做的。西方國家的“三權分立”還是國家權力之間的制約,防止國家腐敗。但是靠國家機器內部的制約還不夠,還應該發揮社會的力量,因為人民是站在國家機器之外的,可以補充和監督國家權力。所以,單建立法治國家是建立不起來的,要有法治社會這個基礎。沒有法治社會就沒有真正的民主法治的國家。
《南風窗》:如何才能改變官員的法治意識?法治社會為什么重要?普通人如何才能接受法治精神和法治信仰?
郭道暉:現在不是設立了“憲法日”嗎?這就是最好的辦法。憲法日首先要教育干部提高憲法意識。那么怎么教育?要拿案例來教育。建議公布幾個違憲的案例,而且加以追究,就會引起很大的震動,就會感覺到憲法不可侵犯,憲法的權威不忽視,憲法權威才可以樹立起來。人民也可以說,我是依據憲法來監督你。教育的對象應該主要是干部、官員。依法治國關鍵是依法治宮,依法治權,唐太宗也說過,治國重在治吏。
(摘自《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