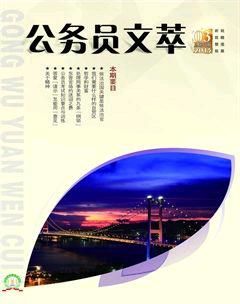人活在世上的品相
蔣方舟
章詒和的《伶人往事》里講過她的父親章伯鈞請京劇大師馬連良吃飯的故事:
剛過午休,幾個穿著白衣白褲的人就進了章家廚房,用自備的大鍋燒開水,等水燒開,放堿,然后用堿水洗廚房,洗到案板發白,地磚見了本色才罷手。再過一個時辰,又來了一撥穿白色衣褲的人,肩挑手扛著整桌酒席用具,還有人扛著烤鴨用的大捆蘋果樹枝。院子里,肥鴨流油飄香,廚師在白布上使用著自己帶來的案板、炊具,連抹布都是自備的,雪白。章伯鈞請馬連良吃飯,結果自家只用了水和火。
章詒和的評價很動人:“不管北京城頭懸掛什么旗子,報紙上宣傳什么主義,馬連良這樣的藝人都細心地過著自己的日子,精心琢磨那份屬于自己的舞臺和角色,以自己獨特又隱秘的方式活著。”
那一代人如何活著?具象地說,是活得“有規矩”;抽象地說,是活得“有樣子”;簡單地說,是活得有尊嚴;往大了說,是依然有著某種精神制約,服從于某種精神力量——高于柴米油鹽的精神力量。這種生活方式就是兩個字,“講究”。“講究”并不代表財富:用金錢窮兇極惡地堆積奢華的生活方式,未免失了分寸。
“講究”的生活一度被批判為小資的,而“講究”的人,也只好遮掩著對于生活細節的愛好,悄然毀掉了自己的“樣子”。
直至今日,人們終于不必隱藏對于生活細節的追求,甚至對物質有種報復式的惡形惡狀的追求:把苦過的日子賺回來。“享受生活”的說法重新回到話語當中,并被自動等同于豪門豪宅豪車。
日本著名的民藝理論家柳宗悅談論器物時說:“每天使用的器具,不允許華麗、煩瑣、病態,而必須結實耐用。忍耐、健全、實誠的德行才是‘器物之心。”樸素的器物因為被使用而變得更美,人們因為愛其美而更愿意使用,人和物因此有了主仆一樣的默契和親密的關系。
我剛剛去了日本的京都,那里的旅館,常常給人以“家徒四壁”的感覺:樸素吸音的墻壁,一張榻榻米,沒有什么娛樂設施,這樣的布置,簡單得幾乎有了“寒苦”的感覺,除了睡覺、喝茶,似乎也沒有其他事情可以干。
出門,連庭院都是枯山水,人就這樣和自己形影相吊,只有空氣中苦涼的香草氣相伴,所有的生活紋理變得異常清晰,再耐不住寂寞的人也被迫正視生活中的一點一滴。
現代人往往筋疲力竭地追逐眼花繚亂的富足,然后再花大價錢、大把時間去清貧簡陋的環境中體驗,并命名為“修行”,如同追逐吊在自己眼前香蕉的猴子。殊不知,生活才是最好的修行方式。
我們談論金錢、談論社會、談論變革、談論技術、談論未來,卻越來越少地談論生活。當我們談論生活時,我們談論焦慮、談論煩惱、談論不滿、談論他人,而越來越少地談論生活本身。
生活的本質是什么?是人該以怎樣的品相活下去。
(摘自《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