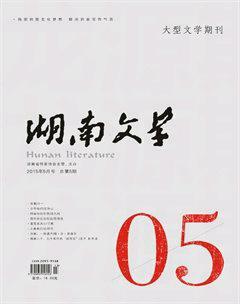排工號子
楊若洲
爺爺年輕時放過排,從十八歲一直放到三十歲,整整放了十二年。
我最喜歡聽爺爺說他放排時的故事,聽他說那些與水爭斗的傳奇,聽他時不時地哼上幾句粗狂但旋律動人的調子,我問他唱什么,“撐排時的號子”,他淡定的回答勾起了我對排工號子的神往。
放排是農耕時代一個獨特的現象。地處“蠻夷”神秘之地的湘西,九百九十九條溪河縱橫如蛛網,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座山峰矗立如箭鏃,一片接一片的原始森林、次森林里,遮蔭蔽日的參天樹木,是經濟發達城市里的稀罕物。宋、元、明、清,至民國,一直到建國后上世紀八十年代,五溪大地上的優質木材和桐油、板栗等土特產一道,通過大小溪流和桀驁不馴的千里沅江,源源不斷地輸往外面的大世界。最多最輝煌的,是清末民初時期,經濟社會的發展、鐵路的興建對木材產生了大量需求,千里沅江“舟楫如林”,應是最生動的寫照。
放排人是舊時代一個獨特的社會群體,當地土話稱放排人為“排估佬”,略略含有一絲鄙夷的意思,大概是餐風露宿、出賣體力、水上討生活的粗活人吧,更多的內涵則是對長年與桀驁不馴的激流斗爭的“硬漢”的一份敬佩。長年在水上行走,“排估佬”自發或不自發地,形成了一套行規,有行話、有暗語、有長幼尊卑、有潛規則,電影《血色湘西》里甚至有“排幫”組織,控制一方水路或碼頭,收取過往行人“過路費”,勢力很大,應是“排估佬”事業發展的極致。如今,放排和“排估佬”已銷聲匿跡,只在歲月深處留一段美麗動人的故事,成為遠去的時光絕唱。
放排一般是水性好的年輕人,由經驗豐富的長者帶著,年輕人體力壯,身手矯健,年長者經驗足,識水路,懂水性,兩者結合,相輔相成。和爺爺一起放排的,是同村的太叔公,還有鄰村的三對叔侄。通常的木排由百余根又直又長的松木、杉木或堅硬的雜木,用馬丁扎成,有的四五層,有的七八層,上面再用木頭搭一個簡易木棚,有床、有碗、有鍋、有鼎罐,有油鹽,或老或少的漢子們就生活在木排上,吃喝拉撒一連幾個月。成了家的,別了妻兒,未成家的,就別了父母,把五溪大地的一脈幽綠、一脈秀麗、一縷粗獷,逶逶迤迤地漂到常德、長沙,或者更遠的武漢、南京、上海。
水上的生活說起來浪漫,像一段十分特別的旅行,但過起來單調,且時時充滿著風險。木排一般早出夜歇,一日可行三五十里,看看天色晚了,便早早地尋一有吊腳樓人家的水邊打樁系錨,生火做飯。漢子們在排上大篙子撐排,大碗喝酒,大聲粗氣地說話。按照迷信,木排是禁忌女人的,但漢子們一連幾個月沒有女人,往往心猿意馬,看見河邊捶衣洗菜的媳婦閨女們便直勾勾地盯著,或出語相逗,遇到性子烈的,便辱罵漢子們一頓,漢子們也不以為意,哈哈一笑了之,若是性子弱的女子,便低頭不做聲。天快黑時,木排上的簡易木棚里就傳出“哥倆好啊”、“四季財啊”的猜拳聲和粗聲粗氣的吆喝,和爺爺一樣的年輕人是沒有資格喝酒猜拳的,只能在一旁觀看,只有年長者才有資格喝酒猜拳,年輕人必得勤快點,輪班看排、洗菜、做飯、撿拾碗筷。等天色漆黑,劃拳聲、吆喝聲便漸漸熄滅在河面的三兩點漁火里。有星有月的晚上,漢子們酒飽飯足后,便上岸與吊腳樓人家說白話,拉家常,天南地北,把自己放排的所見所聞一古腦兒說給人家聽,如實在無事可做,便背靠著背,坐在排邊數星星。無星無月的晚上,漢子們便乘著酒興,稀哩嘩啦搓起麻將,或扳起骨牌,下的注很小。平時漢子們省吃儉用,一文錢要掰開做兩個花,這時候幾個銅板,幾文錢,進進出出很大方,輸贏倒在其次,重要的是過了癮。
在水上放排,不僅要有粗壯結實的身板,矯健的身手,更要有靈活的頭腦。古訓“欺山莫欺水”,千里沅江桀驁不馴,九九八十一灘,灘灘都是鬼門關,無數大大小小的險灘暗礁曾吞沒了許多的木排、船只和水手,其中以青浪灘最長、最惡、最險,暗礁、石頭最大、最多,水流也最急、最猛,“順流而下時,四十里水路不過二十分鐘可完事,上行有時得一整天”,這是沈從文《湘西》中對青浪灘的描繪。放排人靠水為生,浪里來水里去,水性好是必然,更要識得水、懂得水,明白水的喜怒哀樂和可怕。上灘下灘之際,木排鉆進激流、漩水里,需要年長和年輕者一齊巧妙而有力地不停抽篙、換篙,方能把木排撐出白浪里,抽篙和換篙要不間斷地交替,稍一疏忽,木排就會被激流沖退百余米,或偏離航道,撞向巨礁暗石,落個排毀人亡的下場。爺爺告訴我,鄰村一同放排的張四爺就在一次排難中腦袋撞上了礁石,當場喪了命,他侄子在青浪灘邊收拾了叔父的遺體,雇了一個小舢板把叔父送回辰州府,然后一步一步背回老家,面對沅江的方向埋葬,留下一個淚眼漣漣的寡婦和三個未成年子女。這,就是運程不好的“排估佬”卑微的生活和凄慘的命運。
最美麗最動人最讓人難忘的時刻是木排下行擱了灘或不小心卡入激流亂石中,不論冬夏,和爺爺一樣的年輕漢子便三下兩下扒掉衣褲,精赤著身子,縱進齊腰深的激流里,盡肩背之力把木排往前推。一兩個漢子不夠,就三五個;三五個不夠,就七八個,年長的便在排頭死勁用竹篙頂住石頭,撐好方向,直到同心協力把木排推出險灘礁石為止。我想象著這樣的場景,那是怎樣的一幅驚心動魄的場面呀:站在水中的漢子們全都弓著腰俯著背,一任急流狂濤野獸一般噬咬著他們黑紅的肩膀、脊背和胸膛,稍有不慎便會有被激流吞沒的危險。他們的腳是腳,他們的手也變成腳了,十雙趾頭艱難地摳進礁石里,用肩撐著木排前進,根根木頭的尖角深深嵌進他們肩頭的皮肉里,血把排邊的木頭都染紅了,但他們依然鐵鑄般地屹立著,一邊撐排一邊喊著山一般低沉的號子。他們似乎把一生的能量都聚集在嗓子眼里,用一種嘶啞的、不連貫的原始聲音喊著、吐著、掙扎著。他們喊出吐出的已經不是歌了,是生與死的掙扎,是人與自然的搏斗、人與命運的抗爭。我起初是感到靈魂的強烈一震,似乎這號子聲漫過肌膚,正以排山倒海般的力量向我的心靈撞來,接著便覺得有一雙淋漓的手在撕扯著我的心,使人熱血沸騰,令人不由自主地被這原始粗獷的調子所吸引,體會到這號子聲里蘊涵的人生重負,并且從心底里升騰起一股股生之欲望,仿佛那號子聲里凝聚著生之斑斕死之絢麗。號子的內容或雅或俗、或文或武,但通常最能激發漢子們力量的往往是那些粗狂野蠻、通俗易懂、熱切奔放的男女情歌。
“一根木頭那個光溜溜喲,嗨喲!嗨喲!
順著大河下南京喲,嗨喲!嗨喲!
南京愛我那個好木頭喲,嗨喲!嗨喲!
我愛南京那個花妞妞喲,嗨喲!嗨喲喲!”
這樣的號子往往由年長的漢子帶頭領腔唱,撐排的年輕漢子跟著一齊有節律地呼應。前面唱的調子輕緩、悠長而高亢,后面吼的調子急重、短促而低沉,木排便在這一輕一重、一緩一急、一高一低的起伏跌宕中緩緩移動。號子聲旋在河面上,后面的聲音追逐著前面的聲音,在兩岸高聳的石壁間回鳴,重重疊疊后漸次變得悠長高亢且綿綿不絕,形成粗獷絕美至極的排工號子,年年月月,縈響在沅江河畔,成為沅水一絕。
這號子,伴了爺爺一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