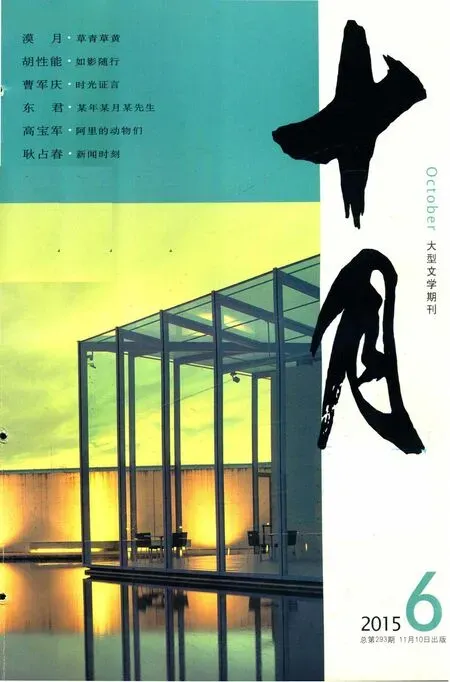我們從中認出自己
夜子
說實話,我最怕談創作,就好比我暗戀著一個人,而我絲毫不知這個人是否會愛上我。如果念念不忘必有回響不能應驗,我不知該如何表達我那贏得了世界卻贏不到一個人的一廂情愿。
真正的接觸寫作得從2004年說起,當時我在電視臺負責一個文化欄目,自此采訪和結識了一些從事文學藝術的人,在這里我就不說其中著名作家對我的影響,我只說其中五個和我身處一地的同齡人。他們有寫詩作畫的也有搞書法拉二胡的。我們因為志趣相投而一見如故,從此成為朋友。某個深夜,沉睡在我心底的文學夢蘇醒了。我打開床頭燈,也打開了掩藏已久的內心,靜靜地趴在床上,寫下了一組詩。它的誕生,讓我大吃一驚。第二天一早,我把上學時寫過和發表過的作品打包封進箱底,它的稚嫩讓我害羞。晚上我把那組詩拿給朋友,朋友說,我們從中認出自己。
那個階段以及后來很長時期,我們六個人幾乎同時迷上了創作,迷上瘋狂購書,迷上貪婪閱讀。在一本好書中我們認出自己,這可以幫我們換一種達觀的態度看待自身的困境。業余時間我們用來交流讀書心得,以及自己的新作品。現在想來,我們其實是在無意中形成了一個小沙龍。六個人會不約而同去其中一個朋友家聚會,他租了一個小二樓,下面賣瓷器,上面是臥室兼書房。環境樸素而溫馨,尤其冬天,我們圍爐夜話,像生活在童話世界。多少個深夜,世界歸于一片寂靜,我們還在那里亮著燈,聊得熱火朝天,外面下著雪花。
當然,這些人都很個性,也很犀利,無論是對我們自己的作品還是對所讀的書籍,常常為堅持的觀點不同,爭論得面紅耳赤,甚至拍案而起。負責給我們泡茶的那位,有兩次拍案拍碎了他自己珍愛的小茶杯,引來我們一片歡呼。正如你所料,這只能增加我們的友誼,而不是破壞。我們是有些偏激,也有些自負,但我們都很欣賞對方,我們的尖銳批評就是為了讓對方的作品更有擔當,都認為對方的才華應該配得上更高的期許。想來,也很可笑,當時的我們,正值年少輕狂,野心勃勃,我們希望自己像某個已故的大師那樣,多少年后還有人愿意讀我們的作品。記得當時我們有一句只有我們自己能夠領會的戲言:我的世紀還沒有到來。
很普通的牛皮紙日記本在我們之間來回傳閱,上面是我們用靈魂寫下的字。不投稿,不參加比賽,只在我們六個和另外的幾個老師之間交流。我們自成一個小宇宙。保留這樣的封閉,確實對我們有好處,避免了剛剛打開的內心被外界浮躁氣息所浸染。心門一打開,發現有那么多東西要去表達。寫作,無限靠近未知。歡天喜地地迎接未知,迎接那迷人的不確定性,使生命的流動過程變成突然而至的陶醉和幸福。我希望這樣的生命就像太陽的一天,從升起到落下,沉淀著豐富的光芒。
實際上我是一個常常陷入悲觀情緒的人,但一旦進入創作狀態,內心就充盈著喜悅。我覺得灰燼后的希望就是我要的希望。它禁得住灰燼,還有什么不能禁的。是的,除去寫詩,我又于2007年增加了寫小說。我不想把詩和小說分開,它們本來就是一個。我認為真正的好小說就是詩。因為它們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詩意。詩和小說是我認知世界的兩個觸角,相對而言,詩是從我身上蹦下來的,它來時,只管接住就行。小說則需付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也更有挑戰性,我對它的興趣與日俱增。一方面喜歡完稿后豐盈的喜悅,一方面也愿意接受面對下一個新小說的手足無措。
我愛著寫作。寫作保護了我的孤獨,也使我享受了孤獨。一直以來,我雖然常常一個人發呆,喝茶,看書,但我從來沒有離開人,沒有離開人群。因為,我在寫。我看到,自己和他們時刻在一起。我們一起面對社會,一起面對人類的美好和困境。同時我越來越覺得把小說寫好,就是一種擔當。讓更多的人在看到它時能有所觸動,有所受益,是我努力的方向。毋庸置疑,寫作可以積攢內心的力量。當身邊有了一張寫作的桌子,那么再面對外界不堪的人和事時,基本能從容應對。那張桌子已經讓你認識了人生,人性的幽暗和光輝無處不在,人性的復雜構成了多彩的球體。多角度地去理解就會多一分寬容,多一分愛。愛所取得的勝利永遠比仇恨更著名。
是的,寫作讓我們從中認出自己,讓更多的人認出自己。我曾寫過一個中篇《田園將蕪》,后來有幸上了中國小說排行榜,不知我的一個親戚是在哪里看到的消息,告訴了父親,父親很高興。有一天,父親跟我要了去讀。要知道,父親是第一次讀我的小說。我忐忑不安,好幾天都怕聽到父親的反饋。父親是一個認真的人,我暗暗慶幸,寫這個小說的初衷,是源于一個朋友在飯局上講述他自己的經歷,多多少少,我有意多問了一些細節,比如,那時人們的生活情趣,以及秋末樹上會有殘留的果實嗎,等等。經過問詢,確定后才敢寫進去,生怕不著調。即便這樣,我也知道自己有陌生的區域,所以就很忐忑地等待父親的閱讀。好在父親沒說,見了面也沒提這事。只是后來,突然有一天他不經意地對我說,他在那個小說里看到了我。
當然不是職業,不是那個故事,而是故事背后的那些微妙,是不能舉例說明的那種種不確定。什么也不用說,慢慢寫,慢慢讀,慢慢迎候文字中那些神秘的我們。這種感覺讓我喜悅,也讓我對生活保持著新鮮感和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