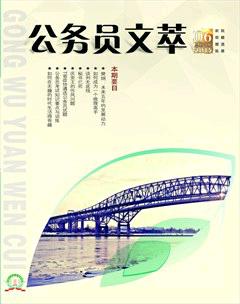先后之間看智慧
張慶松
“視先后之稱,知禍福之門。”這是《管子·霸言》中廣為人知的一句話。先與后,這對詞語語義相反,大部分情況下代表著對行動時機(jī)的兩種截然相反的選擇,而能否妥善處理先后問題,很大程度上關(guān)系到行為者的成敗命運(yùn)。
盡管在漢語中“先”往往代表著積極的意義,例如“先進(jìn)”“先行者”“先見之明”等,但具體到時機(jī)選擇上,卻并不那么簡單。例如,在戰(zhàn)爭中,“察于先后之理,則兵出而不困”,這是兵家公認(rèn)的基本準(zhǔn)則;在棋壇,要想使局勢向自己希望的方向發(fā)展,就要考慮好每一步行棋的先后順序,不能亂了陣腳。
是搶占先機(jī),還是后發(fā)制人?正如《呂氏春秋·決勝》中所言:“智則知時化,知時化則知虛實(shí)盛衰之變,知先后遠(yuǎn)近縱舍之?dāng)?shù)。”解決這個問題,需要以清醒而睿智的頭腦去觀察、應(yīng)對,根據(jù)不同的時機(jī)和變化,作出不同的行為判斷。
先發(fā)制人:出其不意,步步爭先
上甘嶺戰(zhàn)役是抗美援朝戰(zhàn)爭期間的一次著名戰(zhàn)役。其中的一個片段,十分典型地說明了“先發(fā)制人”的道理。
1952年11月3日,上甘嶺上的炮火已經(jīng)持續(xù)了半個多月。經(jīng)過數(shù)天的仔細(xì)觀察,志愿軍第12軍31師第91團(tuán)團(tuán)長李長生發(fā)現(xiàn)了一個現(xiàn)象:敵人每天都是早上八點(diǎn)開始攻擊。他據(jù)此猜測,在這之前,敵人肯定在某處集結(jié)。當(dāng)天夜里,他便派出偵察兵前去搜索。11月4日凌晨四時左右,偵察兵終于發(fā)現(xiàn)了敵攻擊部隊(duì)的蹤影——他們正在597.9高地南側(cè)的一片樹林里集結(jié)。李長生決定先發(fā)制人,對其實(shí)施炮火急襲。四時三十分,“喀秋莎”火箭炮團(tuán)的二十四門火箭炮按照偵察兵所報告的目標(biāo)方位進(jìn)行了全團(tuán)齊射,數(shù)百發(fā)炮彈頃刻間覆蓋了敵人的集結(jié)位置。敵攻擊部隊(duì)傷亡慘重,只得重新組織兵力。這天,敵軍的進(jìn)攻直到中午十二時才開始,而且攻擊強(qiáng)度明顯減弱。
從這次成功的軍事行動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先發(fā)制人”的威力,也能發(fā)現(xiàn)其發(fā)揮效用的關(guān)鍵點(diǎn)。“先發(fā)制人”,不是盲目搶先、一味求快,而是在摸清實(shí)情的基礎(chǔ)上準(zhǔn)確判斷、搶占先機(jī)。上甘嶺戰(zhàn)役中的這次成功,關(guān)鍵便在于乘敵人尚末準(zhǔn)備就緒之際,先發(fā)動進(jìn)攻,打亂對方節(jié)奏。如果敵人已經(jīng)有了防備,先發(fā)制人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所以說,只有出其不意,方能立下奇功。“先發(fā)制人”的原理在棋類運(yùn)動中更為明顯。所謂“棋高一著,步步爭先”,高手對弈,先手后手的轉(zhuǎn)變,往往是判定圍棋中盤形勢優(yōu)劣的依據(jù)。
與此對應(yīng),古人也曾說過,“先發(fā)制人,后發(fā)制于人”(《漢書·陳勝項(xiàng)籍傳》)。可見,在很多情況下,錯失先機(jī)容易使自己陷于被動應(yīng)付、受人牽制的不利處境。
后發(fā)制人:相機(jī)而行,以靜制動
但,“后發(fā)”就一定會導(dǎo)致失敗嗎?也不盡然。
在歷史上,確實(shí)也存在著為數(shù)不少的“后發(fā)制人”的事例。同樣以軍事為例。
公元前632年,晉文公與楚成王為爭奪中原霸權(quán)展開了激戰(zhàn)。由于楚國軍事實(shí)力更勝一籌,晉國始終難以取勝。四月初四日,兩軍再次交戰(zhàn)。為避楚軍鋒芒,晉文公以兌現(xiàn)當(dāng)年流亡楚國時許下的“退避三舍”之諾為名,下令晉軍后退,退至預(yù)定的戰(zhàn)場——城濮一帶。楚國令尹子玉見狀更為驕縱,率軍冒進(jìn),結(jié)果正中晉軍“誘敵深入”之計,陷入重圍,最終大敗。此役之后,時局扭轉(zhuǎn),晉國最終實(shí)現(xiàn)了“取威定霸”的政治目標(biāo)。這就是被后世廣為稱道的“城濮之戰(zhàn)”。
在抗日戰(zhàn)爭中,“后發(fā)制人”的戰(zhàn)略思想更是深入人心。每當(dāng)日軍發(fā)起進(jìn)攻時,八路軍指揮員總是要求戰(zhàn)士們沉住氣,把敵人放近些,到二三十米的距離才開火。按常理判斷,這么近距離開火是很危險的,一槍打不中,幾個箭步,敵人就會沖進(jìn)我方戰(zhàn)壕。為什么不先發(fā)制人,在敵人進(jìn)入一兩百米的機(jī)步槍有效射程內(nèi)時就開始壓制射擊呢?
其實(shí),這一戰(zhàn)略是根據(jù)敵我裝備、戰(zhàn)斗能力等實(shí)際情況的對比而精心制定的。當(dāng)時敵軍裝備精良,我軍在火力上不占優(yōu)勢。離得遠(yuǎn)開火,打準(zhǔn)的概率小,容易浪費(fèi)寶貴的子彈;推遲開火,距離近,敵人的目標(biāo)大,射殺的機(jī)率就大,更可以用手榴彈進(jìn)行殺傷;而且,雙方短兵相接,日軍的炮火優(yōu)勢就不能發(fā)揮。這一策略被后來的解放軍和志愿軍繼承了下來。所以,“后發(fā)制人”也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戰(zhàn)術(shù)策略。
《荀子·議兵》指出:“后之發(fā),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shù)也。”冷靜觀察、引而不發(fā),等對方先動手后,再抓住有利時機(jī)反擊,制服對方。這正應(yīng)了古人“先唱者,窮之路也”的名言。
“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
《淮南子·原道訓(xùn)》指出:“夫執(zhí)道理以耦變,先亦制后,后亦制先。”這就是說,只要掌握了原理,隨機(jī)應(yīng)變,可以先發(fā)制人,也可以后發(fā)制人,關(guān)鍵在于如何掌握最恰當(dāng)?shù)臅r機(jī),選擇最佳方式。故曰:“時之反側(cè),間不容息,先之則太過,后之則不逮……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
處理先發(fā)后發(fā)矛盾,須權(quán)衡形勢,看清利弊。先發(fā)和后發(fā)沒有絕對優(yōu)劣之分,各有利弊。先發(fā)制人可以爭取主動,使敵人未戰(zhàn)先損兵折將;但是,當(dāng)我方行動后,意圖容易暴露,運(yùn)動中也難免產(chǎn)生可供敵人利用的空當(dāng),如果后力不繼,有可能轉(zhuǎn)為被動。正如古人所言:“先者難為知,而后者易為攻也。先者上高,則后者攀之;先者逾下,則后者蹶之;先者頹陷,則后者以謀;先者敗績,則后者違之。”而后發(fā)制人雖然可以以靜制動,以逸待勞,乘敵之虛,反守為攻,但若把握不好,亦會面臨陷入被動、回天乏力的形勢。因此,到底使用哪種策略,一定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值得指出的是,不論先發(fā)還是后發(fā),要想有力地抵御外來挑戰(zhàn),錘煉出堅(jiān)強(qiáng)的自身實(shí)力始終不可忽視。只有自身強(qiáng)大,才能做到“遭變應(yīng)卒,排患捍難,力無不勝,敵無不淩,應(yīng)化揆時,莫能害之”。
上文中我們多以軍事策略論證先發(fā)、后發(fā)之道,其實(shí),在和平年代,這些策略也同樣適用。不論是在商業(yè)運(yùn)籌、政治外交等領(lǐng)域,掌握好“先發(fā)”“后發(fā)”之道,都能夠產(chǎn)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先發(fā)、后發(fā),兩相比較,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對于后者似乎更為欣賞。這一點(diǎn),從老子提倡的“無為而治”便可一窺端倪。
“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所謂無不為者,因物之所為。”這就是說,“無為”的一個原則是,在形勢沒有成熟時,不要盲動;只有能夠善于因應(yīng)形勢變化,才能實(shí)現(xiàn)自己的目標(biāo)。“是故圣人守清道而抱雌節(jié),因循應(yīng)變,常后而不先。柔弱以靜,舒安以定,攻大靡堅(jiān),莫能與之爭。”因此,要想達(dá)到大智慧的境界,就必須要領(lǐng)悟“先后”之間的奧秘,掌握并善用“常后不先”的道理。
(摘自《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