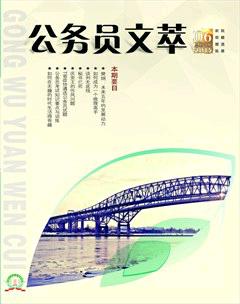官卑民尊的日本
李永晶
一
常有人說,日本有世界上最出色的官僚制度與行政官員。在世人的一般觀念中,日本的公務員被認為是出類拔萃。這個說法可能源于兩本關于日本的著作:一本是大約三十余年前出版的《日本第一》,作者是一位美國的學者,名叫VOGEL(傅高義)。在這部名噪一時的著作中,作者系統地總結了戰后日本經濟的奇跡與日本精神的關系。另外一本是《通產省與日本奇跡》,作者是查莫斯·約翰遜,他細致地分析了日本“通商產業省”官僚制度及其運作。
進入一九九年代,日本經濟泡沫崩潰,進入了經濟低增長乃至零增長的時代。這十年被日本的一些憂國之士稱為“失去的十年”。成亦蕭何,敗亦蕭何。日本的官僚制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對象——在日本國內,主流的看法是僵化的官僚制度要為經濟的低迷狀況負責,人們開始批評日本的行政制度。
要理解這種批評聲音,還要回到日本社會的現場。日本學者決不會論述說自己的政府是如何好,更不會對自己的政府取得的一些成果夸夸其談。這是民主社會的本性使然,因為民主社會的首要特征是國民監督政府及其人員。包括學者在內的國民為政府唱頌歌,那是專制社會的性格。因此,我們要在這一背景下理解日本學者對自己的官僚制度、對自己的官員的批評。
在眾多的批評中,主流看法認為官僚——主要指由高級公務員構成的官員群體——權力過大,形成了獨特的利益集團,并且與執政黨的中央政府形成了權力上不分伯仲的關系,因而不符合民主主義的精神要義。結果,最近數年,日本朝野上下出現了一片“敲打官僚”的聲音。
我曾經對國民與政治家展開的這場“敲打官僚”運動不是很理解,有一次就向研究室的一位叫松本的老師請教:“日本的公務員廉潔,工作效率高,為什么還有那么多人批評他們?”時隔多年,我已記不得當時松本老師做了怎樣的回答。不過,他一定沒有對我解釋說,在日本沒有比批評政府、批評體制更常見的話題了。或許,松本老師認為那是人們常識中的常識,并不需要特別指出吧。
其實,日本的公務員制度有長達一個世紀以上的歷史與實踐。在明治時期,有報效國家之志的青年,大學畢業后通常會選擇做公務員。在當時的觀念中,公務員是與政治家對立的概念;與后者通常陷入黨派私利而不能自拔不同,公務員被認為是國民的公仆,不追求自己的私利。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各級政府迅速網羅了大批精英——真正的服務于國家與國民利益的精英。上面提到的《通產省與日本奇跡》所描述的戰后負責制定通商產業的官員形象,正是日本官僚制傳統的一個側影。
日本公務員留給人們的印象,并非僅僅是他在日本民主政治、經濟發展中的卓越的角色。生活中的日本公務員,首先給人以一種極為樸素的形象。那種形象簡單地說,也就是上面提到的“公仆”。那是一種名至實歸的作為“公眾的仆人”、“國民的仆人”的形象。
二
由于留學生活的局限,我與日本地方政府公務員的交往,幾乎僅限于負責“國民健康保險”部門的人員。日本在20世紀60年代初實現了醫療保險的全民覆蓋,制度比較成熟。長期居住在日本的外國人,一般也都選擇加入這一保險。參加保險人員,可以享受醫療費用70%的減免,即實際上只需支付醫療費用的30%。因看病不再成為經濟負擔,日本國民只要健康上出現問題,都會首先選擇去醫院或醫療診所尋求治療。
回國工作后,有一次談到這一現象時,我對友人說:“我發現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日本人都是病人,而中國人都是醫生。”
那時我正染感冒,從藥房買回了幾種藥片、口服液,其中一部分是自己拿定主意選購的,另外一部分則源于藥房售貨員的推薦。這幾乎是新奇的體驗。日本國民對自己的健康狀況感到不安時,事無巨細,都會去醫院咨詢、尋求幫助,因而國民動輒成了病人。從科學的角度來看,與自己診療相比,日本國民的做法顯然是最佳選擇。
由此我回憶起自己在日本初次去醫院就診時的經歷。
留學日本的第一年夏天不意感冒后,我連吃了兩日的藥物,因未見好轉,就外出尋找藥店買藥。出乎意料,大半天時間我竟然未找到藥房。不得已,我決定去醫院尋求醫生的幫助。
主治的醫生詢問過病狀后,問我有沒有在吃什么藥。我取出從國內帶來的一種常見的感冒藥,對醫生說:“正在吃這一種,但不見起色……”
那位醫生取出附在藥盒里面的說明書,看過之后,說:“今后不要吃這種藥了,藥劑量太大。我給你開一點藥。記住要多喝水,好好休息。”有了第一次看病的經歷后,自己對去日本醫院就醫也就沒有了抵觸。也正是在那時,我才知道,感冒基本上是“不治之癥”,并沒有特效藥。
日本國民個體的生活樣式與行為方式,其實與社會制度息息相關。卓有成效的醫療保障制度,保證了國民可以放心地去醫院求醫問藥,而不是盲目地自我診治。
享受醫療保險的保障,要付出必要的代價。在日本,參加保險的人員自然要繳納保險費。保險費有減額與減免制度——對于一般的低收入者,只需交納一定比例的保險費即可;具體減額程度與減免條件,則因地方政府的不同而不同。留學期間,由于我沒有正式收入,每年都要到政府部門申請利用這項制度。
記憶中,負責該制度的人員會詢問自己上一個年度的收入情況,并取出一份“稅收申告表”,告訴我即使沒有收入,也要填寫這張表。按照要求,每年需要提前填寫好。實際上,每年年末,我都會收到政府寄來的表格以及回信用的信封。由于信封郵資已付,自己只要填好表格,裝入信封寄出即可。雖然便利,但出于惰性,我從來沒有提前填寫這類的表格。于是,每年自己申請保險費減額時,都會發生類似的一幕:現場填寫。
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政府的工作人員從未問過我為什么當時沒有及時申告,更無半點責怪之意,盡管申告乃是一項義務。
我曾經對此做過一種解釋:雖然當事者應該承擔不及時申告所帶來的相應后果,諸如保險費無法減額,等等;然而,如果當事者因無能力全額繳納,進而導致保險資格喪失,那么一旦發生意外,該當事者就無法享受醫療保險,他的生活也就無法得到國家的保障了。一個具體的個體生活無法獲得保障,盡管他自己要承擔一部分責任,但從實質的意義上說,那意味著這個制度也就出現了問題。這是日本社會政策的邏輯,是一種以國民個體的利益為至上的政策邏輯。不管原因如何,若特定個體的利益沒有得到善待,那么政策甚至政府自身的正當性就要受到質疑。
或者從政府的角度來說,政府提供的這項公共服務,就是要涵蓋每一個具體的個體,無論最終責任應該由誰承擔。如若說日本政府的目標是“以人為本”,那么這個“人”只能是具體的、單個的國民,而非任何意義上的集合概念。
認識到這一點,是因為我發現,自己每一次申告收入情況時,政府工作人員對申告內容從不提出異議。換句話說,他們相信我的申告屬實。當然我也知道,若申告內容有虛假,自己可就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了。當時我曾經想過,政府對國民的信任,是因為國民有法律意識,還是國民具有誠實的人格?當然,這是一個虛擬的問題,沒有實際意義。其實,一個好制度可能同時造就這兩者。
三
記憶中,最后一次與日本公務員打交道發生在妻子懷孕期間。當時來到我們所居住的文京區區政府負責的部門,想申請出產費用減免的“助產士制度”。到那里后,看到前面的人在排隊,就坐到后面的沙發上。
剛坐下不久,只見一位男性工作人員從敞開式的辦公大廳里走了過來,詢問我們的目的,我站起來簡要地說明了情況。他聽后,走回了辦公室大廳里。日本的政府機構采用大辦公室,相近的科室集中在一個類似大廳的大房間里辦公。前來辦事的國民對整個辦公室的情況,可一覽無遺。
正在我們再次開始等候時,從里面又走出來一位公務員,是一位三十歲前后的女性,手里拿著許多資料。看到她走過來,我就要起身站起來。就在這時,她急忙對我說:“請坐下來。”緊接著,她就屈身蹲到了我和妻子的面前,把手中的資料一份一份地翻閱給我們,幫我們解釋涉及生育補助的各項制度,并告訴我們如何填寫申請表格。
讓政府的工作人員蹲著給自己介紹情況,雖然我知道這是因為妻子有身孕的緣故,但還是有些不適應。不適應的原因也僅僅在于,在迄今為止的人生中,我還沒有受到如此的待遇。當然,我還是有些大驚小怪了。其實,想到日本的各級官員與國民處于正常的、而非顛倒的“主仆”秩序當中,他們的行為很容易理解。國民是主人,官員是仆人。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原理,就如此簡單。
有了這些生活經驗后,再閱讀日本學者對日本政府行政體制及公務員的批評,自己就有了鑒別的依據。有一次我讀到一位日本學者說,日本歷史上也有過“官尊民卑”的現象。我非常敏感地注意到了他的用詞,并試圖從其文中找到依據。
令人失望的是,那位作者是在泛泛指陳,并沒有實際的事例佐證。不過,轉念一想,我也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借助國民對“官尊民卑”這個字眼可能產生的嫌惡感,日本學者似乎時刻不忘對官員進行職業教育,進行官員的“公仆”意識教育。當然,這同時也是國民的政治教育。
這種教育有意義嗎?回想一下自己的生活經歷,我突然發現,接受啟蒙教育的并非是日本的官員,而是我自己。知道了什么是正常的主仆秩序,其實也就知道了什么是有體面的、有尊嚴的生活。沒有這個基本的秩序,國民真正的“尊嚴”無從談起。
(摘自《東京留學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