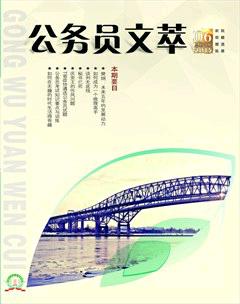王若飛在法國勤工儉學
馬連儒+++袁鐘秀
1919年11月25日,王若飛等遠渡重洋到達法國馬賽港。
從上海出發的時候,王若飛向蔡衡武借了四百元錢,船票花去了一百四十元,連添置行李、衣物和途中花費,盡管百般節衣縮食,到法國時他手上也只有一百元錢了,而這一百元錢僅能兌換八百法郎。于是,他來到了接待勤工儉學生的華法教育會和華僑協社。
將自己手上的一百元錢交給了華法教育會代為保存,以便分期節約取用。1920年初,他到離巴黎不遠的楓丹白露公學補習法語。
在楓丹白露公學里,王若飛性格灑脫,不拘形跡,言談動作都別有一種性情。他常常穿一件寬大的外套,戴一頂高高的帽子,夾著一個大書夾子。從裝束看,他很像一個大學教授,同學們開玩笑地給他起了一個“博士”的綽號。平時,他專心致志地鉆研法文,拼命讀書。他喜歡讀修養方面的書和古代英雄的傳記。他的見解經常與眾不同,有一種進取的精神。他涉獵較廣,目的不是為的沉潛深入,而是想了解自己尚不大熟悉的領域。他善于獨立思考,不時對書中所講的內容提出一些疑問,總要弄出個究竟。他的這些作為,有時遭到一些人的譏誚和議論,但他都不以為意。他并不認為自己什么都好,但也不把自己看得一切都壞。他認為自己身上還有許多毛病需要克服,特別需要“朋友匡救”。他對周圍的事物有些看不慣,最看不起那些僅會吹幾句“新思想”的時髦青年。
對于王若飛這樣的勤工儉學生,當年的有識之士就已看出他們將來對中國的意義。在當時的《旅歐周刊》的一篇社論里這樣寫道:
“留法勤工儉學生,暫不論思想、學識如何,專就形式及精神而論,確是中國未來的勞動階級的中心人物。……請看他日國中,竟是誰的世界。”
當年這篇評論,為今天的現實所證明。在赴法勤工儉學運動中確實涌現出一大批像王若飛這樣的無產階級的革命家。
王若飛在楓丹白露公學補習了三個月的法文。他的錢便花完了,還欠了法華教育會三百法郎。他不能繼續學習下去了,必須找到工作,才能維持生活和償還債務。于是,他請華法教育會代覓工作。
1920年3月27日,楓丹白露公學放春假。春假后,王若飛和他的同學必須離開這里。而華法教育會通知他們去工廠工作的消息又遲遲不來。4月8日好容易得到了可以去圣泰田工作的通知,并發來了每人一百五十法郎的暫借款。當第二天他們一行三十五人興高采烈準備動身的時候,不知何故又突然有變,叫他們先不要去報到,再補發每人五十法郎暫住校外旅館,以等待安排工作。有八個同學實在等不及了,在圣泰田工廠方面沒有通知他們報到的情況下,單獨組成一組貿然先去了。向來比較穩重的王若飛沒有這樣做,他自告奮勇,只身前往巴黎華法教育會詢問實情。他了解到的是因為招工工廠的工種多與同學自報工種不對口,有的同學不愿前往,有的同學甚至拒絕報到。于是,他返回了楓丹白露。
直到4月14日,他們才終于得到正式通知,到法國南部里昂附近諾瓦省的圣夏門鋼鐵廠去做工。他們乘車從楓丹白露出發,經過蒙達尼,在圣泰田轉車,來到圣夏門。
一下火車,舉目望去,黃塵滿地,黑煙四起,天昏地暗,河水污濁。街市并不繁華,房屋也多簡陋。往來的人盡是濃眉大眼、衣衫檻褸的勞動者。
在未正式進工廠之前,王若飛身邊的旅費僅有三十法郎。為了留出買套工作服的錢和臨時必要的開銷,他第一天的午飯便實行了“節食主義”。當他餓著肚子去商店的時候,店員們出于對華工的歧視,對他表現出一種嬉笑輕慢的樣子,當天下午,盡管他和同學們是拿著工廠開的介紹信到街上住旅館的,出于對華工的歧視,一連三家旅館都推說沒有房間而把他們拒之門外。到了第四家旅館才接待了他們,總算沒有使他們露宿街頭。
直到第二天清早,王若飛才買了一塊面包和冷水豆餅,算是進了到圣夏門一天一夜以來的第一頓飽餐。他覺得這頓飯異常香甜,體會到“饑者易為食”的滋味。第二天正逢星期日,他們到附近公園一游,在那里遇到在圣夏門人造絲廠工作的五位華工。這五位同胞,遠遠見了他們就主動脫帽,打招呼。這時,有個別同學遠遠地避開了。王若飛卻上前向他們問好。他對個別同學輕視華工、不愿與華工接近的態度是不以為然的。在廠外候工的三天時間雖短,但王若飛卻受到了許多教育。
圣夏門鋼鐵廠是一個規模宏大的工廠,有一萬五千工人,廠內煙囪林立,鐵軌縱橫,4月15日這天,他們去報到上班了。
首先遇到的一個問題是選擇工種。王若飛事先不了解鋼鐵廠有哪些工種和每個工種的勞動強度。一開始王若飛與許多同學選報的是翻砂制模工。當大家聽先來的同學介紹說這個工種又累又臟時,一些人便調換了別的工種,而王若飛卻沒有更換,仍然選了翻砂制模工。沒有幾天,他便經受了翻砂制模工的辛苦:“天氣苦熱,廠中尤為干燥,遍地都是泥沙,大風吹進,砂即騰起,著于面上,為汗水所粘凝,偶一拂拭,其狀越怪丑可笑。鼻為灰沙窒塞,呼吸因之迫促,時時仰面噓氣以自蘇;口時苦渴,吸冷水稍覺清爽。下工時仿如初出監獄的囚犯,覺天地異色,形狀很是憔悴。”經過實際操作,他知道了翻砂各道工序的嚴格、精細的程度,深有感觸地說:“翻砂這項工作,普通聽去,以為是很粗的工作,實在卻非常細致,我還嫌我性情粗莽,不配做呢!”
王若飛雖然工作十分勞累,但始終沒有忘記學習。在王若飛看來“認真研究學問,每天讀書的時間并不在多,果能做到心不外馳,讀書一點鐘,可以比別人讀三點鐘,一天讀五點鐘的書,已經是很多的了”。
王若飛認為,入學校讀書自然是“理想的事”,但他非常注重和提倡“進天然的社會學校”。他說:“若要抱取幾本講義,在課堂上鬼混幾點鐘,然后為學,那么在中國、日本都很好研究,不必遠來法國。”他特別指出,“我說這句話,并不是反對人不當進學校,就是我以后也要進學校,是說吾人當求學(下轉第110頁)(上接第104頁)求智,不可注重文憑,專讀死書”。
對于“社會大學”的重要意義,黃齊生后來在抗戰期間寫的一篇《社會大學之我見》的文章中,說:“許多老師宿儒,名人碩彥,固然是我的老師,難道販夫走卒、婦人孺子,如我計算,所得教訓,又豈少嗎?”他尖銳地指出:“可笑自資本主義的教育制度輸入吾國以來,什九以領講義、領憑照為教育正宗,如我今茲所說,認為教育實效之一種,或不免要嗤之以鼻。”他以龐德公培養諸葛亮為例,說他們師生之間是“一邊生產,一邊施教”,“自修自習,互修互習,相與有成”。他在文章最后高呼“社會大學萬歲”。應該說,這篇文章是用他的親身經歷和感受說明了所謂正統教育的弊病和社會教育的重要。可貴的是王若飛早在1920年便從自己實際體驗中得出了這種見解。
(摘自《王若飛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