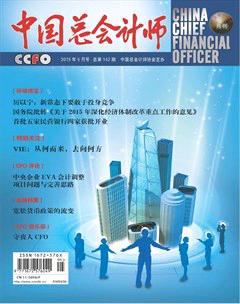中國古代詩文中的稅與稅吏
詩歌——這個在漫長的文學藝術進化史中發育最完美、生命力最強的藝術,不僅言志,言物,也表情懷。很多詩歌,特別是現實主義的詩歌,都體現著同情勞苦大眾、關心民瘼的濃濃的人文主義情懷。
古代散文——這個發端于春秋戰國、成熟于唐宋、大放異彩于明清的文種,同樣承載了幾千年來歷代圣賢們對天下蒼生的憂心和對人民疾苦的關切。而在所有這些作品傳達的主題中,有一個特殊的視角,那就是稅收。在封建社會的漫漫長河中,稅收是封建政權得以生存和運作的血液,稅收也往往是老百姓最具切膚之感的生活關節。有抱負的統治者一般比較關注稅負問題,并且我們經常可以在《史記》等作品中看到帝王同臣子討論稅負問題的片段。稅負是隨著王朝更替動態變化的,在王朝沒落的時候,往往稅負加重,老百姓不堪忍受,于是發生如《捕蛇者說》所描述的怪相。
雖然作為文學作品的詩歌、散文,不能作為稅負輕重的判斷依據,但卻可以提供一種視角,一種思考。
輕徭薄賦的呼聲
在我國關于稅賦的詩文中,以反映官府強征暴斂、人民負擔沉重和生活艱難的居多,一些古詩對當時官府的“殺雞取卵”、“竭澤而漁”,不注意發展經濟的收稅作法表示了不滿,有的詩人還直接提出要減免人民沉重的稅收負擔。也有一些寫稅的古詩文頗具特色,除了傳統賦稅詩的沉重和壓抑,更多了一份意味深長、一絲弦外之音。
明朝開國功臣劉基曾寫過一首叫《田家》的詩,詩云:“租稅從何來,官府宜愛惜。如何恣刻剝,滲漉盡涓滴。”劉基雖然是屬于統治階級的一員,但整體上來講屬于士大夫階層,施德政、得民心是劉基治國思想的核心。民本思想在其政治觀點和文學作品中多有體現,上面這首詩無疑是一個極好的體現。全詩勸誡的口吻,表達了對稅收負擔的關切。
清康熙年代的查慎行隨清軍進入貴州,目睹人民經過戰亂后的慘狀,禁不住呼吁寬減百姓的租稅:“馀生民革逃難穩,絕塞田野瘠可憐。好報長官蠲賦斂,獼猿家室久如懸。”
查慎行是滿人入關后成長起來的著名詩人,雖然他的名氣似乎沒有劉基等文豪響亮,但其在當時的影響力為世人稱道。而這位先賢的子孫中便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小說家查良鏞,沒錯,就是享譽華人世界的金庸。
納稅人的心酸
除了對稅負沉重的責難和呼吁之外,一些詩歌還描繪了納稅人的酸甜苦辣。只要有國家,就有稅收,但稅收的征收如果無視百姓的承受能力,不能隨著豐收與兼收的交替而調整的話,只能適得其反。縱觀中國古代史,歷次農民起義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沉重的稅負。
我國古代對于稅收的設立、征收還是有一整套法律的,整個稅負也并不是直觀上的那么重,事實上一些開明君主和有識大臣,是經常權衡稅負的。中國古代稅負的問題可能更多的在于,稅收的豁免方面不太完整,缺乏人性化,對一些在生活中暫時遇到困難的人關注不夠。下面的幾首小詩可以為筆者的這一觀點提供一些佐證。
宋代詩人宋伯仁在《村姑》中寫道:“底事磋跎二八年,嫁時裝著未周旋。年年織得新絲娟,又被家翁作稅錢。”典型的宋代生活情境,宋代商業比較發達,生活比較小資,人們的生活品味較高,對嫁妝之類的東西比較在意。這首詩中描繪的淳樸、勤勞的村姑對自己的嫁妝錢被父親挪用一事是有意見的,但問題不在于自己的父親對自己的女兒不愛,而在于父親為應付家里的開支不得不挪用自己女兒嫁妝的無奈,從此我們也可以看出,當時的稅法對生活苦難者的忽視。
《苦旱行》是明代張細孫的詩,其詩中云:“安得昊天降靈雨,童兒歡笑父老賀。高田低回薄有收,比里稍可完國課。不然官吏猛如虎,終朝鞭撲疇能那?”以通俗易懂的語言抒寫了農民盼望天降霖雨,使莊稼薄有收成可稍完“國課”的卑微而善良的心理,同時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時的稅法未考慮農業生產周期性波動的特殊性,征收方式簡單粗暴。
無處不在的稅目
在我國古代,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形成的稅收體系也相當完備,但因為稅法發展尚在襁褓之中,有的稅目顯得有些巧立名目,有的甚至荒唐可笑。
自號“石湖居士”的范成大在《四時田園雜興》中的一首詩道:“采菱辛苦廢犁鋤,血指流丹鬼質枯。無力買回聊種水,近來湖面亦收租。”農民已瘦得不成人形,官府連水面都要收稅,形成強烈的對比,也說明部分農民的稅負著實不輕。
明朝湯顯祖有一首《聞都城渴雨,時苦攤稅》,詩云:“五風十雨亦為褒,薄夜焚香沾御袍。當知雨亦愁抽稅,笑說江南申漸高。”申漸高是五代時吳國的樂工,當時吳都城干旱,中書令徐知誥(即后來的南唐開國皇帝李昪)問:“近郊有雨,都城為何不下?”申漸高詼諧地進言:“國為雨怕抽稅,不敢進京。”詩人借此典故,無情地揭露了當時稅賦的苛重。
清代宋琬的《飯鳳凰山下》詩云:“茅茨深處隔煙霞,雞犬寥寥有數家。寄語武陵仙吏道,莫將征稅及桃花。”也諷刺了無所不至的征稅之災。
近代著名學者郭沫若曾做過一副妙對,橫批“民國萬稅”,聯語“自古未聞糞有稅,而今只剩屁無捐”,可謂極盡嘲諷。
形形色色的稅吏
如果要對古代的稅收做一個概括,恐怕很多人都會選“苛政猛于虎”這句名言,但遺憾的是這樣并不公允,人們總是夸大自己所受的苦難。但這句話也確實從一個側面展現了某些極端現象。在極端情況下,苛酷的賦役及四處搜括民財的稅吏比虎還毒,因為稅收制度和懲罰很嚴厲,這種扭曲的稅收制度造就了一批酷吏型的稅吏。
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王安石,曾對稅吏的貪酷感嘆萬千。他在《感事》一詩中說:“特愁吏之為,十室災八九。原田敗粟麥,欲訴嗟無賕。間關幸見省,笞撲隨其后。況是交冬春,老弱就僵仆。州家閉倉庾,縣吏鞭租負。鄉鄰銖兩征,坐逮空南畝。取貲官一毫,奸桀已云富。”他認為,老百姓之苦,在于“吏之為”,即官吏的濫用權力。
元代少數民族詩人逎賢在他的《新鄉媼》一詩中這樣記載:“茅櫚雨雪燈半昏,豪家索債頻敲門,囊中無錢甕無粟,眼前只有扶床孫。明朝領孫入城賣,可憐索價旁人怪。骨肉生離豈足論,且圖償卻門前債。數來三日當大年,阿婆墳上無紙錢。涼漿澆濕墳前草,低頭痛哭聲連天。”可見,稅賦之苦,已將百姓逼迫到賣兒賣女,尊嚴盡失的地步。
但實際上,稅吏遭遇了超過他們所限的批評與鞭笞,試想在整個稅收架構下,稅吏只不過是一個執行者而已,上有上司的監督考核,下有養兒育女的家庭重擔。有時恐怕是不得不為之,當然筆者并不反對事實上確實存在少數道德敗壞的酷吏。
除了上文所說的酷吏型稅吏,還有一種文化稅吏。唐代大詩人白居易所作《觀刈麥》等詩,正是他在今陜西省周至縣做基層稅吏時所寫。他在詩中捫心自問:“家田輸稅盡,拾此充饑腸。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馀糧。念此私自愧,盡日不能忘。”其文化稅吏的悲憫情懷盡顯于詩。在《買花》一詩中,白居易則對當時社會貧富差距懸殊現象非常憤怒:“有一田舍翁,偶來買花處。低頭獨長嘆,此嘆無人喻: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
金末元初著名詩人、歷史學家元好問也曾為稅吏。他做稅吏的時候,任勞任怨,一再督促百姓照章納稅。在《內鄉縣齋書事》一詩中,他回顧遠祖次山公(唐代詩人元結)因百姓賦稅繁重而“思欲委符節,引竿自刺船”情境,追憶了遠祖不惜丟掉官職減免賦稅的事跡,進而對照反省,抒發自己“吏散公庭夜已分,寸心牢落百憂薰”的憂稅之心。他不忍用強硬的手段向百姓征收租稅,使得“催科無政堪書考,出粟何人與佐軍”,夜半時分仍寢室難安。他同情民眾疾苦,心懷經世之心,于是告誡屬下切莫擾民:“教汝子若孫,努力逃寒饑。軍租星火急,期會切莫違!期會不可違,鞭撲傷汝肌。傷肌尚云可,夭閼令人悲。”元好問還深情追憶過唐代另外一位在道州擔任過刺史、深受百姓愛戴的官吏劉云卿。在《宛丘嘆》一詩中,他這樣記述其功德:“碑前千人萬人泣,父老夢見如平生。”
此外,在古代稅吏這一非主流群體中,還存在一些狡吏和呆吏。
“狡吏”,即“狡猾之稅吏”。狡猾之吏的特點是想盡辦法利用制度漏洞合法或不合法地獲取私利。
白居易在《杜陵叟》中則這樣描述“狡吏”:“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征求考課。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何如?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惻隱知人弊。白麻紙上書德音,京畿盡放今年稅。昨日里胥方到門,手持敕牒榜鄉村。十家租稅九家畢,虛受吾君蠲免恩。”就是說,在皇帝免稅圣旨下達之前,“狡吏”就已經把賦稅收繳完畢,老百姓根本享受不到“皇恩浩蕩”。
明末清初著名詩人吳嘉紀在《海潮嘆》一詩中對“狡吏”的奸詐與無恥描寫得入木三分,栩栩如生:“斂錢墮淚送總催,代往運司陳此情。總催醉飽入官舍,身作難命泣階下。述異告災誰見憐?體肥反遭官長罵。”就是說,稅吏收了錢、吃飽喝足之后,卻說:“對不起,報告災情的事情很難辦。”
古詩中記載的稅吏還有“俗吏”與“呆吏”之流,他們屬于惟上是從,只顧吃喝拿要,不負責辦事之徒。一些呆吏糊涂顢頇,不懂法度;一些呆吏坐井觀天,目無王法和百姓利益;一些俗吏渾渾噩噩,只顧一己私利。
南宋詩人范成大在《四時田園雜興》中這樣寫道:“黃紙蠲租白紙催,皂衣旁午下鄉來。長官頭腦冬烘甚,乞汝青錢買酒回。”“俗吏”混吃混喝的形象躍然紙上。
事實上稅吏這個群體的生活狀態也是很有意思的,他們雖然職權不大,品級不高,但卻屬于有油水的一類官職,囿于篇幅所限,我們不展開討論,只是擇其一二而窺其貌。
參考文獻:
姚軒鴿.古詩中的稅吏形象[N].中國稅務報,2015-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