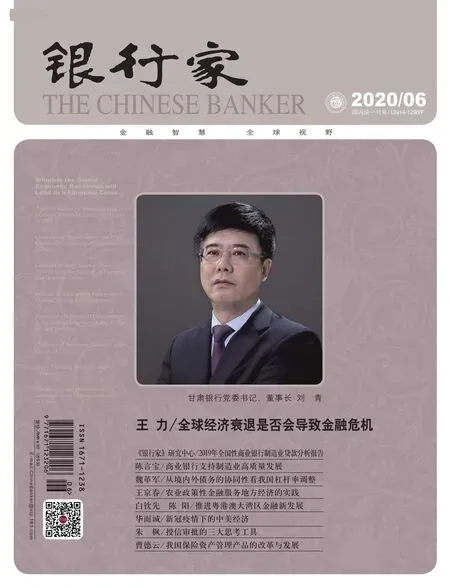深化供銷合作社改革與下放金融自主權
周立
合作金融是農村金融體系的基礎,發展農村合作金融,是解決農民融資難問題的重要途徑,是合作經濟組織增強服務功能、提升服務實力的現實需要。合作金融與政策金融、商業金融一起,是農村金融體系的三駕馬車。
建國以來,我們在合作金融的建設上,進行過多種嘗試。貫穿其中的一條主線,是以農村信用合作為代表的合作金融建設。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我們首先有一個組織化的進程,全國范圍內推動了生產合作、購銷合作、信用合作這三大合作化運動。改革開放后,又經歷了一個去組織化的過程,三大合作要么停止運行(以人民公社為代表的生產合作),要么落入低谷(以供銷社為代表的購銷合作),要么走向變異(以農信社為代表的信用合作)。自2003年農信社下放地方負責,走向商業化改革方向以來,新型合作金融的主體,就處在不確定狀態。2007年放寬農村金融市場準入后,依托農民合作社、供銷合作社的新型農村信用合作被寄予厚望。如今出臺《深化供銷合作社綜合改革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推動供銷合作社發展多種類型的合作金融,對于新型農村金融體系的建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新“三農”的三大關系
習近平指出:“只有工人階級和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的中國共產黨,才是代表先進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力量。”伴隨中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深入,生產力得到極大釋放,需要生產關系隨之調整。換句話說,“蛋糕”(生產力發展帶來的)越做越大,切分“蛋糕”(生產關系變革)變得越來越重要。生產關系不能適應生產力的發展需求,產生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究其本質,是社會總利益與各個群體的利益目的之間的矛盾。當前中國社會的最基本矛盾,在生產力方面已得到極大緩解,但在生產關系調整上,迫切需要深化改革。
農村生產關系的變革,是廣大農民在生產過程中的所有制形式、社會地位及相互關系的變革,突出表現為新“三農”的三大關系。
農民與農民的關系。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的建立過程中,出現了明顯的“統”得不足、“分”得過度的問題。至今,雙層經營只有分戶經營這一層了。在分戶經營基礎上,無論是單家獨戶的原子化生產與交換,還是農村市場化進程中的相互競爭,都無法構建和諧的農民與農民關系。農民需要生產、購銷、消費、信用等方面再組織化,走向互助聯合的綜合合作,才能重構農村新型社會關系。
農民與市場關系。中國兩億多農戶的家庭經營,一直面臨著小生產和大市場的矛盾。是單槍匹馬闖市場,還是聯合互助去交易?應該說,分戶經營曾經極大釋放了農村生產力,但伴隨市場化的深入,單家獨戶干不了、干不好、干起來不劃算的事情日漸增多,必須重構農業生產關系。我們近些年寄希望于種養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龍頭企業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來扮演起重構農業生產關系的重任。但這遠遠不夠,畢竟,以家庭經營為基礎,是世界范圍內,也是中國幾千年農業歷史的基本事實,無法改變。必須在家庭經營的基礎上,推動互助合作等“統”的工作,才能解決“分”帶來的單個農民闖市場帶來的交易地位不對等問題。
農民與政府關系。兩億多分散農戶,對應兩千多個縣級、四萬多個鄉鎮政府的治理,也存在巨額的交易成本過高難題。政府在縣鄉村三級治理上,既有干預之手,也有幫助之手,但這都需要具體可行的抓手。如果政府推動資本下鄉、部門下鄉,可能進一步促使農民分化和原子化,加重農民對市場的依賴關系,這種干預會出現政府失靈。如果政府推動城鄉要素的平等交換,致力于農村再組織化,引導專業合作走向綜合合作,就會發揮幫助之手的作用。
三大關系的改造,決定了“三農”問題的基本走向,改造方向就是再組織化。《決定》供銷社深化改革的部署,推動了以綜合合作為導向的,頂層設計與基層探索的雙向互動。
走向綜合合作的重要嘗試
關于深化供銷合作社綜合改革的決定,應該說是政府伸出幫助之手的重要嘗試。《決定》提出了三個“迫切”和一個方向:“農業生產經營方式深刻變化,適度規模經營穩步發展,迫切要求發展覆蓋全程、綜合配套、便捷高效的農業社會化服務;農民生活需求加快升級,迫切要求提供多層次、多樣化、便利實惠的生活服務。新形勢下加強農業、服務農民,迫切需要打造中國特色為農服務的綜合性組織。”在東亞地區,以小農經濟為主要經濟基礎的社會里,無一不是以鄉村兩級綜合性合作組織,作為生產關系載體。我們經過30多年的去組織化后,重歸再組織化的道路上,是對歷史經驗、國際經驗和現實問題的尊重和回應。
《決定》也對供銷合作社的特殊身份和地位,做了準確的描述:“長期以來,供銷合作社扎根農村、貼近農民,組織體系比較完整,經營網絡比較健全,服務功能比較完備,完全有條件成為黨和政府抓得住、用得上的為農服務骨干力量,要充分用好這支力量。”作為中國最大的合作經濟組織,自1954年以來,供銷社已經形成了國家、省、市、縣、鄉五級組織體系,有聯合社、成員社、基層社。縣和縣以下已有2.5萬家基層社,當前供銷社經營觸角和服務領域已經覆蓋了80%以上的鄉鎮,和接近60%的行政村,是一個組織體系、經營網絡、服務功能最為健全的貼近“三農”的服務組織,有改造為綜合性合作組織的基礎條件。但是,《決定》也指出了相應的問題:“目前供銷合作社與農民合作關系不夠緊密,綜合服務實力不強,層級聯系比較松散,體制沒有完全理順,必須通過深化綜合改革,進一步激發內生動力和發展活力,在發展現代農業、促進農民致富、繁榮城鄉經濟中更好發揮獨特優勢,擔當起更大責任。”考慮到體制機制改革困難,也需要一個日程表。按現有的安排,到2020年,要把供銷合作社系統打造成為與農民聯結更緊密、為農服務功能更完備、市場化運行更高效的合作經濟組織體系,成為服務農民生產生活的生力軍和綜合平臺,成為黨和政府密切聯系農民群眾的橋梁紐帶,切實在農業現代化建設中更好地發揮作用。
實際上,引導農戶走向綜合合作,也是在落實《憲法》的基本要求。《憲法》第八條關于集體經濟的部分,有如下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農村中的生產、供銷、信用、消費等各種形式的合作經濟,是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決定》提出,經濟實力較強的基層社要擴大服務領域,積極發展生產合作、供銷合作、消費合作、信用合作,加快辦成以農民為主體的綜合性合作社。這落實了憲法的綜合合作要求,也有利于解決我們五行八作多種經營的綜合小農,與只有專業合作的不匹配矛盾。《決定》還提出打造城鄉社區綜合服務平臺,讓供銷社發揮提供包括文體娛樂、養老幼教等在內的多樣化服務,發展生態養生、休閑觀光、鄉村旅游等新興服務業功能。可以說,此次供銷社的深化改革,是引導走向綜合合作的重要嘗試。
農村金融自主權的下放
早在1992年,鄧小平同志在南巡上海時,對金融的地位做出闡述:“金融很重要,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著棋活,全盤皆活。”轉到農村的語境,農村金融很重要,是農村發展現代經濟的核心。但長期以來,農村經濟機體如同缺乏心臟一般,沒有金融自主權。金融掌握在誰的手中,就為誰服務,由于缺乏金融自主權,一系列面向農村的金融安排,就常常扮演將農村資金汲取出來的抽水機角色,使得農村經濟常常處在失血狀態。
在農村金融制度上,我們長期以來寄希望于農信社能恢復合作制。這從1984和1996年兩次農村金融改革的安排中,可以看出。1984年國務院105號文要求,農信社要恢復“三性”,即組織上的群眾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經營上的靈活性。明確界定其為合作金融組織性質,不能作為農業銀行的基層機構,將農信社從政社合一的體制下解放了出來。1996年《國務院關于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國發[1996]33號文)也明確提出,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是“建立和完善以合作金融為基礎,商業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分工協作的農村金融體系”。將農村信用社從農行獨立出來,向合作制方向發展。并在信用聯社基礎上,有步驟地組建農村合作銀行。
但在農信社走向官辦,進而又走向商業化之后。深化改革的目光,就有農信社轉移到供銷社了。基層社作為供銷合作社在縣以下直接面向農民的綜合性經營服務組織,被定位為供銷合作社服務“三農”的主要載體。要按照強化合作、農民參與、為農服務的要求,逐步改造為以農民社員為主體的合作社。
主體性的獲得,為農民從供銷社改革中,得到金融自主權,提供了制度前提。《決定》提出了,供銷社獲得七種形式的基層金融探索權利:資金互助合作、互助合作保險、中小型銀行、融資租賃公司、小額貸款公司、融資性擔保公司,與地方財政共同出資設立的擔保公司。
在農村資金互助合作上,有明確的四項要求:社員制、封閉性、不對外吸儲放貸、不支付固定回報,另有一個隱含的要求“社區性”。通過這五項要求的滿足,以資金互助合作為主要體現形式的合作金融自主權,就回歸到農民手中。金融自主權回到農民手中,為合作金融制度真正建立起來,綜合合作真正能夠開展,金融真正實現為農服務,提供了可能性。我們樂見一個農村合作金融新時代的到來。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博士點基金(20110004110003和20120004110001)支持。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