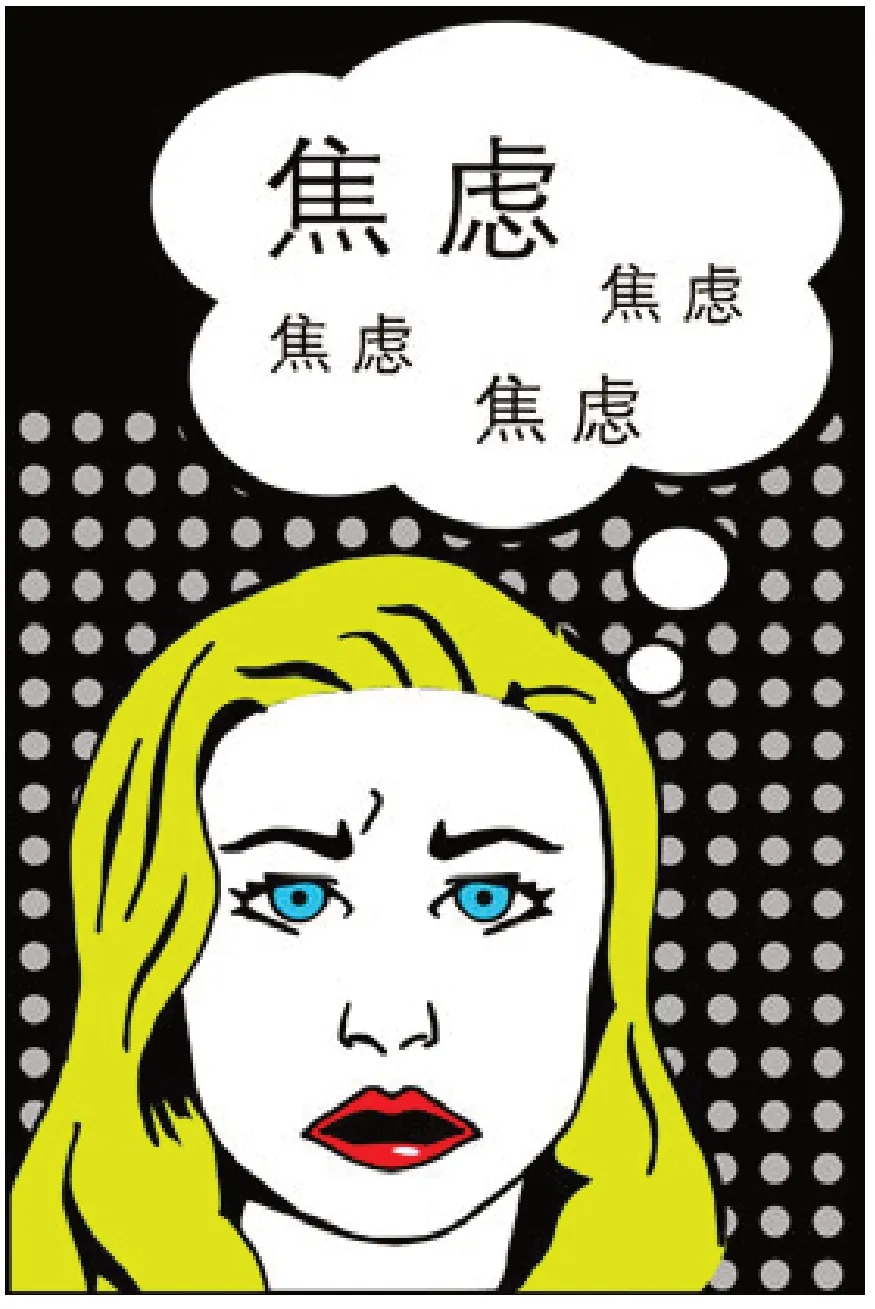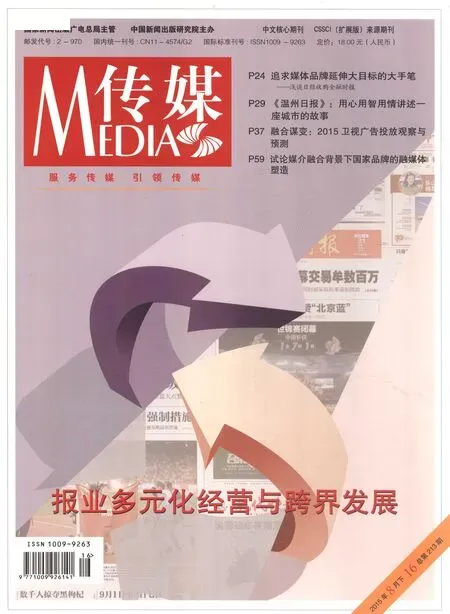如何調適紙媒記者的焦慮情緒
文/蘇麗艷
當前紙媒缺人,確切地說,是缺乏有熱情、有韌性、能獨當一面的人,這是當下諸多紙媒面臨的共同難題。在此背景之下,留住可用人才,激發他們的內在潛力,顯得尤為重要。而無論是留人還是激發潛力,情緒處理都是十分關鍵的一環。
縱觀身邊紙媒記者群體,焦慮是他們普遍的情緒。2010年11月,天津市某知名報社對60名采編記者進行心理測試,結果表明,采編記者的強迫因子分高于國內常模(普通的模式),女記者較男記者更易產生焦慮。筆者分析,當下一線紙媒記者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曾經有過新聞理想,隨著年齡增長逐漸力不從心,因習慣體制而堅守;第二類是懵懂入行,記者只是一個謀生的職業,因生活所需而堅守;第三類是有新聞理想,沒有生存壓力,因興趣選擇當記者。無論以上哪一類記者,都可能在工作過程中產生焦慮情緒:第一類記者容易因新媒體沖擊、紙媒衰落心生焦慮;第二類記者本身缺乏內在動機,容易因生存產生焦慮;第三類記者注重職業規劃,容易因個人發展瓶頸產生焦慮。
值得注意的是,多數記者習慣把壓力悶在心里。與上司溝通的過程中,這些焦慮情緒往往又會以其他形式如不滿、抵制、消極怠工等表現出來。而在我國,鮮有媒體主動建立心理干預機制,從上到下很少有人關心記者的心理健康。
鑒于以上現實情況,筆者認為,一方面,有必要讓記者群體了解一些心理學,嘗試觀照自身、自我傾聽;另一方面,紙媒管理者尤其是中層管理人員,也可通過溝通和傾聽,提高管理效能,提升團隊凝聚力。
焦慮情緒的兩面性
從心理學分析,焦慮是所有形式危險的自然相關物,其成因包括困窘的環境或其威脅。
面對記者群體的焦慮,一種觀點認為屬于“無病呻吟”。受著焦慮與倦怠煎熬的新聞人,不少人抱怨“記者不易,似馬如牛”,“ 無冕之王” 變“新聞民工”了。但三百六十行,憑啥當記者就得“易”?事實上,當記者做新聞是個光榮、平凡而艱苦的差事,在這點上記者與其他職業沒啥不同。要想干好,都得付出應有的努力,經受應有的煎熬,需要耐煩耐辛苦,需要認真專注。
另一種觀點認為,有著職業焦慮的記者會帶著疑問、困惑、思想去采訪,這樣的記者處于最佳心理狀態,往往看得準、想得深、報得快。當然,超過一定水平的職業焦慮也會帶來負面影響,甚至抑制思考力、判斷力,比如成就動機感過強,為求作品轟動效應造成身心焦慮,結果常常欲速不達,有的甚至出現了職業操作上的片面、不公、偽劣等失誤,給自己帶來更多的心理負擔。
嘗試與焦慮和平相處
那么,記者的心理怎樣才算是健康的?根據心理學家的觀點,歸納起來,有幾項重要指標:一是能與他人保持良好的人際關系;二是情緒基本穩定,心境輕松愉快;三是人格完整,能客觀地評價個人及外界;四是熱愛集體,有濃厚的社會交往欲;五是有一定的安全感、信心和自主性;六是個人理想與現實的距離可望可及。
根據以上幾個指標自我檢視,或許,不少一線記者會發現,自己或多或少出現一些心理“不健康”的表現:對環境、自身及他人過多負面評價,長時間感覺緊張,團隊合作有障礙等。這些,又無不與焦慮有關。
而事實上,焦慮作為一種情緒,本身并沒有對錯之分。情緒是生命能量的一種自然流動,它會來,就一定會走。
關鍵在于學會與焦慮和平共處。首先,要悅納自我。著名心理學家武志紅告訴我們,沒有人生來完美的,我們要感謝和接納自己的不完美。當下,紙媒整體環境有所變化,紙媒記者需要調整自己,讓生活目標和理想更切合實際;要能對自己作出客觀評價,對無法補救的缺陷,無法改變的現狀,也要能安然處之。同時,也要能愉悅地接受他人,認可別人存在的重要性和作用。其次,在焦慮情緒產生的當下,可以嘗試讓這股負能量爆發出來,用不批判、不抗拒的態度,在全然的愛和接納中去經歷它,因為“凡是你抗拒的,都會持續”,而當你用心體會和傾聽自己的焦慮,或許還會透過焦慮看到焦慮背后更多更深層次的情緒和需求。
管理者如何傾聽下屬
誠然,觀照自身、自我傾聽是激發潛能的根本途徑,但對個人修養的要求也相對較高。而在具體媒體執業過程中,一線記者亟需團隊關注,即當他們的焦慮情緒通過種種不同形式體現時,如果團隊管理者能夠及時捕捉和傾聽他們,無疑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美國著名人本主義心理學家卡爾·羅杰斯認為,傾聽,尤其是傾聽求助者的情緒問題,有益于求助者個人成長。他相信來訪者本身具有解決問題的智慧,只是被卡住他的情緒所障礙。在此基礎上,另一名美國人本主義心理學家托馬斯·戈登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溝通模式,其中最重要的技巧之一即“積極傾聽”,被譽為“治療性的溝通”。
當一線記者遭遇采訪困難、發展瓶頸以及自身成長困惑主動找團隊管理者傾訴甚至發泄焦慮情緒時,就是展開“積極傾聽”的好時機。積極傾聽的基本理念為:在傾聽他人時,要試著了解對方的感受,然后用自己的話表達(事實+感受),向對方求證,傾聽者絕不可加入自己的意見、分析、評價及勸告等。
筆者曾在一名駐站記者提出辭職時,對這名記者做出“積極傾聽”,實錄如下:
記者:我這次的決定完全是自己做的。迫切想逃離。
筆者:你決定了,你想逃離?
記者:離家3年多來,我已經十分厭倦一個人孤軍奮戰的駐站生活。這樣的生活時常讓我覺得恐慌和孤獨。我也根本感覺不到自己存在的價值是什么。努力了很長時間,已經找不到奮斗的目標。
筆者:嗯,努力了卻沒有相應的價值體現,這讓你覺得無助而且失望。
記者:辭職這件事情已經從去年想到現在了。我覺得自己沒有再堅持下去的理由了。轉不轉正無所謂,離開了也不想再當記者。
筆者:記者這個行業對你不再有吸引力,你想改行?
記者:我覺得我沒有愛過這個職業。如果說曾經有過,那也只是暫時的。每天都是新的開始。
筆者:現在你有了新的想法和目標?
記者:什么都沒有。
筆者:你只想有新的開始,只要不是在本城。
記者:可以這么理解。
從實例中可以看到,當管理者作為傾聽者,只是不帶批判地重復傾訴者所說的事實,并對傾訴者當下的情緒和感受做出反應時,傾訴者比較容易敞開心聲,從而讓焦慮情緒得到流動。而隨著傾訴的深入會發現,傾訴者一開始提出的辭職意愿,并非最根本的訴求,更深入的需求在于——想換一個工作環境,而不是對記者這份職業失去興趣。這也就是積極傾聽所具有的“剝洋蔥”作用,即有時候在焦慮情緒之下的需求,往往和一開始自己提出的風馬牛不相及,連傾訴者自己都不自知。此次交談后,該名記者調整心態,在原崗位繼續堅守了一年,于次年調回總部,算是比較圓滿地兼顧了記者個人(回到家鄉城市)以及報社(留住可用之人)雙方的需求。
而要做好“積極傾聽”,對管理者無疑是巨大挑戰。一個最重要的前提,即積極傾聽時,管理者需清空自己、暫停自己的思考,正確接受下屬傳遞的信息。當下屬說話時,暫停手中的工作,注視下屬,提供讓下屬表達感受的時間和空間。這樣,才能了解下屬話中隱含的意義,才可以幫助下屬真正紓解某些負向情緒,增進關系,協助下屬自己找到解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