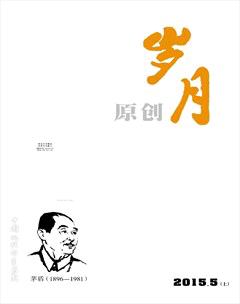然而,很美
閆語
最初的愛情,最后的儀式
如果,波瀾不驚的生活中有一陣風吹過,我相信,其中的一縷一定是從音樂中吹來的,有一些滄桑,有一些悲傷,其中夾雜著觸手可及的現實、過往和內心故事。作為一個遲到的傾聽者,我錯過了收集夢碎花朵的妮娜·西蒙,與歌聲中富有神秘禪意的倫納德·科恩擦肩而過,卻神奇般地闖進了《D大調卡農》的深遠回味中。
初次聽到《D大調卡農》,是在韓國電影《我的野蠻女友》中:當男主角手拿玫瑰,出現在教室,女主角正在演奏的就是由美國鋼琴家喬治·溫斯頓所改編的鋼琴版《卡農》;當兩個人沉浸在陰差陽錯的彼此思念中,大段響起的則是傳統弦樂版《卡農》;當音樂隨著男女主人公一次意外相遇,最終牽手而結束時,那干凈至純的音色,和諧至美的和聲,卻在我的心里升騰起一絲甜蜜寧靜的憂傷。
《D大調卡農》是德國作曲家約翰·帕赫貝爾最著名的作品。簡單不過的曲調一再反復,高低聲部遵守著嚴格的對位法則,各自規律地不斷往前發展,和諧演奏出曼妙的旋律,最后光輝地結束,聽起來卻絲毫沒有單調之感,令人浮想聯翩。或許可以這樣理解:天地一琴,每個人都是游走在琴鍵上的音符,沒有華麗的裝飾,沒有刻意地雕琢,不需要激情、反叛和搖滾,也不需要衰老和死亡,平靜就是生命的高潮,像黑夜里的那一縷幽光。
約翰·帕赫貝爾,是德國巴洛克后期的作曲家兼教堂管風琴師,管風琴和鍵盤音樂是他主要受到肯定的創作領域。然而這個名字被廣為流傳,不僅僅因為他曾是巴赫的老師,還因為那一首不朽的經典旋律——《D大調卡農》。
據考證,《D大調卡農》誕生于1680年,當時27歲的帕赫貝爾正陷于熱戀之中,因此有人猜測,這首曲子是愛情的產物。試想一下:某一個午后,帕赫貝爾穿上燕尾服,戴好頭套,在抒情的曲調中,姑娘的心被慢慢拉近,進而綻開笑容,融進愛情的光輝里。至此,我認為這是一首浪漫至上的曲子,一對年輕的男女渾身閃耀著純美的青春,他們旁若無人地對視著,笑著,依偎著,夕陽很好很溫暖,他們在樂曲聲中盡情地幸福著,旋轉著,他們彼此交叉,照亮,最后在互相輝映中漸漸老去。這就是愛情最初的模樣吧?
還有人說,《D大調卡農》是帕赫貝爾為悼念亡妻而作。他忍受著愛妻孩子死于瘟疫的巨大痛苦(一說死于難產),創作出一組不朽的音樂,以紀念往逝的死者,其中的一首變奏曲,就是《D大調卡農》:一個聲部的曲調自始至終追逐著另一個聲部,直到最后——最后的一個小結,最后的一個和弦,它們融合在一起,永不分離。
我猜,愛,應該是個容易出錯的精靈吧。所以,我想象著這樣的畫面:一天,一對男女被愛神的箭射中,一不小心掉進了河里。也許這兩個人會手拉手一起朝河岸邊游去,上岸后竟然開始相互埋怨,各自憤憤離開;也許是其中一個人奮力游向岸邊而沒有顧及到另一個人,結果上岸的人徑自離去,水中的人暗自傷心。這樣的結果,究竟是時間錯了,地點錯了,還是人錯了呢?答案,帕赫貝爾也許知道,也許不知道。無論知道與否,都已經不重要了。他默默地坐著,陷入回憶,甜蜜開始從痛苦中一點點滲透出來,久違的溫暖漫過心頭。他伸出雙手,手指在鍵盤上游走,輕盈地雕刻著永世隔離的痛,自得其樂且樂此不疲,往日的種種溫馨就一遍又一遍地重現眼前。這樣的儀式,是內斂的滄桑,還是無法忘卻的姻緣呢?
幾百年來,《D大調卡農》的演繹版本多不勝數,無論用何種樂器演奏,都遮蓋不了它原本迷人的氣質。1966年,在維也納音樂節上演出了指揮家卡拉揚改編的《卡農》。1968年,《卡農》第一次被西班牙的一個聲樂組合改編為流行歌曲。《卡農》還曾被作為奧斯卡影片《凡夫俗子》、韓國電影《我的野蠻女友》、泰國經典潘婷廣告的主題配樂,在古典音樂TV動畫《金色琴弦》中,也出現了這首曲子。《卡農》讓更多人忘卻了影片的故事情節,而記住了它的旋律。
現在,我一直循環播放著不同版本的《D大調卡農》,華麗的,簡潔的,恢弘的,小巧的,都完美得令人窒息。低沉的提琴,長笛的柔美,鋼琴的流暢,以及多聲部的吟唱等等,在反復延綿的旋律中,心得到寧靜,靈魂也漸漸平和下來,像是天籟之音縈繞在耳畔。我個人比較喜歡佛拉門戈版,這個版本加入了許多節奏元素,輕松快樂的鼓點,讓人聽了就覺得心情舒暢,有著舊日花園精靈復活的味道。
因為《D大調卡農》契合了我的某一理想,長時間讓我著迷。在一遍遍聆聽《卡農》的時候,我總是會想到那一句“執子之手,與子攜老。”我仿佛看到先秦的一位將士正在征戰的間隙翹首遙望家鄉,而這一眼望出去,乖乖,看到的竟然是帕赫貝爾,兩人目光相遇,就響起了《卡農》的絕美旋律。
也許,音樂就是這樣一種存在。從某個人開始,當多年以后,當我們聽著來自過去的音樂片段,當我們只能通過唱片了解一種旋律和一個人的時候,我相信,一定會有人很愿意喜歡上《卡農》這樣簡單又充滿幸福感的曲子。而對于每個聆聽過這首曲子的人來說,《卡農》應該是時間中的一片光暈,是飄在風里的夢境,是行走在大地上的遐思吧。
母親教我的歌
我多想向克萊斯勒借一雙演奏小提琴的手,這樣,我大抵就可以聽見那個來自德沃夏克的段落旁白,即使面前沒有小提琴,只是用手在空中虛拉,我也能聽見他,聽見一個久久徘徊于指尖之上的,溫情而傷感的德沃夏克。
安東·德沃夏克,是十九世紀捷克最偉大的作曲家之一,捷克民族樂派的主要代表人物。1892年,他在美國任教期間,以美國黑人音樂為素材,創作了著名的《第九交響曲》,即《自新大陸》。人們熟悉和喜愛的那首叫做《念故鄉》的歌曲,就是以《自新大陸》中的一段充滿無限鄉愁的旋律改編成的,一首偉大的曲子帶著離鄉人的血脈和靈魂在天空中徐徐地飛翔,像一塊愁云。
而在這個春天里,我反復傾聽的是德沃夏克的《母親教我的歌》,并且把它當成了我的舊夢重溫,像述說故事般流淌的旋律中,有我對母親最好的回憶——我們坐在窗前,用暮色中飛翔的思緒談談母親的身體我的生活,談談近在咫尺的落日和被落日染紅的江水,談談心靈的戲劇,以及誰將在誰的角色里暗中易手。在這首虔誠低徊的歌曲中,母親的眼神,手勢,語氣,仿佛那些流逝的時光又重新追上了額頭,皺紋里的往事溫暖著我這顆遠游的心。
《母親教我的歌》是德沃夏克1880年創作的一首藝術歌曲,在行板速度上輕輕流動的旋律,帶有搖籃曲的擺動感,曲調溫和親切,猶如一封家書般的喃喃低語。這首歌是德沃夏克為海杜克的詩歌譜的曲子,是德沃夏克歌曲集《吉卜賽之歌》中的第四曲,后來被改編為小提琴、大提琴等樂器的獨奏曲以及管弦樂曲、合唱曲等形式,流傳至今。
初次聽到《母親教我的歌》,是英國女高音夏洛蒂·丘琦的演唱,這位橫跨古典和流行的天才歌手,用她那來自體內一處與情感共鳴的聲音和甜美純真的出色外表,瞬間就吸引了我,仿佛它就是一把鑰匙,打開的是一個封閉了想象的秘密花園。之后,我又看到了由著名小提琴家AraMalikian在美麗浪漫的西班牙一處農場皇宮的夜景里演奏的《母親教我的歌》,夜色溫柔,小提琴如泣如訴,我隱約看見了那個坐在夏日夜晚,指著星空中那把“勺子”給我講故事的母親。如今,故事依然在夜空中閃閃爍爍,而我坐在家里卻滿懷離鄉背井之情。似乎從一開始,母親就和故鄉是渾然一體的,有母親在的地方才是故鄉,才是家。
或許,旋律最深處的母親是聽不見的,但是只要你在聽,你就是母親。漫長的,短暫的,一分鐘或是一小時的母親。每次聽德沃夏克的《母親教我的歌》,那催人淚下的旋律就會在我房間的空氣里藏著,睡著。當歌聲意猶未盡,我分明感到我在這段旋律中走到了母親身旁,躺在她的懷里,靜靜地聽她唱歌,音樂閃成的淚花悄悄地滑落在我的臉上。我知道我可以從那些雜亂的影子里認出母親,認出那雙粗糙的手,我閉著眼睛,顛倒時光里的思念一年深似一年,還有不斷沉下去又不斷浮上來的故鄉的容貌。而一個被賦予了詩歌和音階的母親,通常需要另一雙眼睛去讀,另一顆心臟去跳動,另一段文字去保持和收藏吧。
一百多年來,《母親教我的歌》的演繹版本層出不窮。捷克著名小提琴家約瑟夫·蘇克的演繹,實而不華且充滿溫情,能讓這不朽的旋律繞梁三日。也許是因為蘇克是德沃夏克的學生和女婿,所以對這首曲子的理解才更加入木三分吧。捷克女高音歌唱家瑪格達萊娜·科熱娜用捷克語演唱的《母親教我的歌》,純凈婉轉,風味十足。“倫敦提琴之音”48把小提琴的演奏,氣勢磅礴,耳目一新。被稱為音樂鬼才的范宗沛版,溫情而憂傷的氣氛濃郁到必須用手捂住胸口,而1996年捷克影片《KOLYA》中,盧卡帶著柯利亞躲到鄉下時,也用到了這段旋律,該片奪得當年的金球獎、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和東京國際電影節獎,應該也有《母親教我的歌》的功勞吧。當然,還有很多我們知道或不知道的版本,無論是大氣的交響樂版,鋼琴、小提琴協奏版,美聲詠嘆調版,還是男女聲對唱的通俗版,只要在這段旋律中坐下,聲音的故鄉就會一點點伸進耳朵,沿著世界的軀體游走,然后,母親溫柔的光輝灑落下來,直到把他鄉聽成故鄉,把德沃夏克聽成母親。我個人最喜歡克萊斯勒演奏的小提琴版,小提琴的音色最能把這種細膩的愛表達得絲絲入扣,它如觸電般的揉弦,充滿人情味的滑音,高尚的樂感,是永遠無人替代的。
《母親教我的歌》是德沃夏克藝術歌曲的巔峰之作,這首充滿溫情與緬懷的雋詠小品,簡簡單單的旋律卻把思母之情表達得幽雅逶婉,纏綿悱惻,讓每個聆聽過這段旋律的人都會在心靈深處深情地擁抱母親,而母親一直都在聽,用柔軟的心和舒緩的耳朵。
《母親教我的歌》相對于我,是對母親的思念,是牽掛,是愛。當一種精致、優雅的情感支撐著一個飽滿的聽覺世界,當陰晴不定的天氣在用力撕扯著我對母親的想念,當窗外隱隱的花香也加入春天的暮色,女兒稚氣純美的歌聲像一團光把我照亮——當我幼年的時候,母親教我歌唱,在她慈愛的眼里,音樂閃成淚花……
杰奎琳的眼淚
透過庭院里花葉盛開植物的間隙,杜普蕾看著天色在一場漫不經心的小雨中變暗,變得油膩。她筆直地坐在套著綠色天鵝絨的輪椅上,金黃色的頭發垂肩而下,她的臉龐輪廓鮮明,皮膚粗糙,一雙清澈透明的藍眼睛呢喃著。她那天精神很好,突然很想聽聽自己在1970年和巴倫博伊姆錄制的那張埃爾加的《E小調大提琴協奏曲》,當一個個熟悉的音符響起時,她忽然發現,自己的整個空間其實就是一把大提琴,是斜倚在歲月身上的嗚咽之聲。
埃爾加這部挽歌式的作品,她曾經無數次演奏過,但這一次,更像一個飽含滄桑的老人,從遲暮之年回過頭來,仿佛連夢境都是悲涼的。她和大提琴一起陷入回憶。但大提琴的回憶是什么,它的隱喻部分需要一個精神地理的意象嗎?“這是我的天鵝之歌,可是,那時我并不知道。”她說,“大提琴的音色就像是人在哭泣一樣,每當我聽到這首曲子的慢板樂章時,心總會被撕成碎片……它好像是凝結的淚珠一樣。”然而,1975年以后,她就算想哭,也沒法哭了。
多重硬化癥,窮兇極惡,無從掌握,又無藥可醫。開始的時候,杜普蕾發現自己的手有時候不聽使喚,甚至握不住琴弓,眼睛有時候也會看不清東西。她開始變得敏感、脆弱,常常感覺到莫名的孤獨和無助。終于,病痛使她不得不停止了演奏,就連看書看電視和日常生活都必須有人照料,生活圈子也局限于病床和輪椅。
在這之前,她在倫敦舉行了一場告別演奏會,曲目當然是埃爾加協奏曲:她拉出的每個音符都像被上一個音符嚇了一跳,似乎她的手指在琴弦上每觸碰一下都是在糾正一個錯誤,而這恰恰又變成一個新的錯誤在等待著糾正。準確地說,當時的她已經是個有局限的演奏家了,而她卻比任何人都更加出色更加優美地完成了這場演奏會。對于這次演出,卡度爾爵士這樣寫道:“對于聽眾來說,這的確是一場極為非凡的演出……似乎告訴人們埃爾加已經向生活道別,光輝燦爛的日子已經過去,迎接他的將是黑夜。”匈牙利大提琴家斯塔克有次乘車在廣播里聽到了杜普蕾的演奏,便問身邊的人演奏者是誰,他說,“像這樣演奏,她肯定活不長久。”沒想到,竟一語成讖。
那么,在倫敦皇家節日音樂廳首次登臺演出埃爾加《E小調大提琴協奏曲》的十七歲的杜普蕾呢?那場被英格蘭著名的樂評家那弗·卡特斯描述為“珍貴易逝的美之絕唱”的音樂會,就真的永遠盛放在那一年的春天里了嗎?我知道,音樂從她身上什么都沒拿走。把她掏空的是生活。音樂是生活還給她的,但那還不夠,遠遠不夠。今天,我坐在52年后的這個春天,試圖穿過音樂找到她,找到那個讓世界變得美好,能夠用奇妙的方式觸碰我們心靈深處的女孩——杰奎琳·杜普蕾。
時間在音樂中倒流。看,杜普蕾笑意盈盈地走過來了,穿著碎花圖案的裙子,金色的長發時而披散在肩上時而飄飛在風中。她優雅而堅定地走著,手里的大提琴在熟悉的腳步中找到了一條與別人不同的路。她和朋友們見面,熱情地擁抱,開心地聊著天氣或是講上幾個幽默的小故事。她坐在鋼琴前,能夠把一首歡快的曲子彈得更加歡快,還會煞有介事地把小提琴當作大提琴來拉。對于朋友,她的存在,就是快樂。
一首曲子就是一個在時光中游走的身影吧,等到那個身影停住腳步,轉過身,就如同我們和她一起坐在房間里,喝咖啡,說話,就像這首《杰奎琳的眼淚》。據說,杜普蕾曾經演奏過雅克·奧芬巴赫的大提琴曲《杰奎琳的眼淚》,在手頭有限的唱片目錄中我并沒有找到它,但也并非不存在意外,許多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在我們的注視或不經意間早已發生了。所以,我聽到的錄音是另一個杜普蕾嗎?如果她演奏過(我愿意相信她演奏過),我想知道,她在拉那首嵌有自己名字的曲子時的心情是怎樣的?是不是她聽到曲名的瞬間就喜歡上了這首曲子?是不是她看到樂譜的那一刻就看到了自己眼中隱蔽的憂傷?是不是她拉出第一個音符的時候就已經迷失于無邊的淚海?
2014年的這個春天,我是坐在夜色里聽著這首《杰奎琳的眼淚》的。夜已經深了,城市里剛剛下起了這一年的第一場春雨,大提琴的旋律就在淅淅瀝瀝的雨聲中回蕩著。在這個晚上,雨是來自音樂中的啟示嗎?一切都始于某種情緒,某種印象,某種所見所聞,然后再將其轉化成文字嗎?也許,就是那樣吧,人生中有些事早已注定,它們埋伏在那兒,等著你經過,就像這場春雨一樣耐心。在這個晚上,在這首《杰奎琳的眼淚》的最后一個音符溶入雨水,留下一個關于淚水的憂傷、凄婉的夢的時候,我坐在書桌前,聽著收音機里同樣的旋律,寫下了這些句子。
事情是這樣的嗎?是我想象的那樣嗎?也許都錯了,但我已經盡力。我沒有太多的資料。我找到了克里斯托弗·努本拍攝的紀錄片《回憶杜普蕾》,我讀到了那本《狂戀大提琴》的最后一個字,除此之外,只有唱片和照片:那便是杜普蕾留下的所有。
以及,我耳朵里的淚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