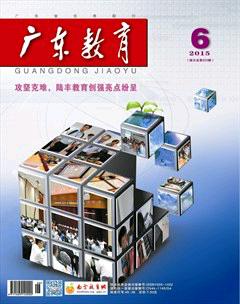理解與融合
周杰
科學(xué)世界的教育管理,即教育管理的科學(xué)化,其特征是理性、實(shí)證、本質(zhì)和客觀。它外在于學(xué)科、專業(yè)、課堂、知識(shí),卻統(tǒng)籌著教育運(yùn)行走向。但它確實(shí)是一種工具化、技術(shù)化、方法化、觀念化了的模式,它排斥偏見,迷信權(quán)威,衍生的制度和秩序掩蓋了人的價(jià)值。哲學(xué)詮釋學(xué)試圖從對視域、前理解、視域融合概念的闡明,重構(gòu)并達(dá)成教育管理的理解與融合,以圖從根本上為解決當(dāng)代教育管理危機(jī)打下基礎(chǔ)。
一、科學(xué)世界及其特征
當(dāng)代是一個(gè)科學(xué)映射下的世界,科學(xué)從一種方法裝扮成存在的真理社會(huì),依靠的是將自然觀念化、形式化甚至哲學(xué)化,并不斷追求其精確和驗(yàn)證的過程。在A·孔德(Auguste Comte)那里,一切科學(xué)知識(shí)都可以概括在“實(shí)證”一詞當(dāng)中,它們必須建立在來自觀察和實(shí)驗(yàn)的經(jīng)驗(yàn)事實(shí)基礎(chǔ)上。而在T·S·庫恩(Thomas Samuel Kuhn)看來,它首先需具備一個(gè)科學(xué)范式(paradigm),即一種公認(rèn)的模型或模式。庫恩認(rèn)為,依據(jù)有無“范式”,科學(xué)的發(fā)展可劃分為前科學(xué)時(shí)期和常規(guī)科學(xué)時(shí)期,二者的發(fā)展圖景是:前科學(xué)——常規(guī)科學(xué)——危機(jī)——科學(xué)革命——新的常規(guī)科學(xué)。范式一旦確立,意味著一套實(shí)際的科學(xué)習(xí)慣和科學(xué)傳統(tǒng)得以產(chǎn)生、一個(gè)科學(xué)解決問題的圖像和模型得以構(gòu)造、一個(gè)概念化了的體系得以形成。在這個(gè)體系中,世界的規(guī)則性被認(rèn)為是確定無疑的,世界被預(yù)設(shè)成完美、客觀和規(guī)范的統(tǒng)一體,人和事物表征為工具化、技術(shù)化、方法化、觀念化了的東西。在面對問題時(shí),人們第一個(gè)要尋找的不是問題本身,而是如何從問題的外部尋找到一條科學(xué)規(guī)律或者方式,以圖套用并解決這個(gè)問題。換言之,問題的關(guān)鍵不是對事物或人本身的關(guān)注,而是對工具理性和技術(shù)理性的推崇。即它是一種以工具崇拜和技術(shù)主義為生存目標(biāo)的價(jià)值觀,它內(nèi)在的思維模式便是要先設(shè)定對象的本質(zhì),然后用本質(zhì)來解釋、用實(shí)證來說明對象的存在和發(fā)展。它純客觀地、不變形地用來反映客觀存在。因此,理性主義、實(shí)證主義、本質(zhì)主義和客觀主義成為科學(xué)世界的幾個(gè)公認(rèn)的特征。
二、制度僵化——科學(xué)世界教育管理困境
科學(xué)世界下的教育管理,包括理論和實(shí)踐的一切知識(shí)和行為,致力實(shí)現(xiàn)的是促使教育管理行為的科學(xué)化。在邏輯經(jīng)驗(yàn)(實(shí)證)主義者看來,如果教育管理行為是科學(xué)的,那么它們必須用一種確定的方式來建構(gòu),并認(rèn)為所謂的科學(xué)管理,必須有一種客觀的觀點(diǎn)能使人對管理從事價(jià)值中立的研究,有一種科學(xué)的知識(shí)能使人去控制組織和改善組織,有一種為人類決策所共同起作用的理性基礎(chǔ)和為提高組織的效率和效益的技術(shù)的管理觀。與此同時(shí),一些學(xué)者(格里菲斯(Griffiths),霍伊(Hoy)和米斯凱爾(Miskel)等)進(jìn)一步提出科學(xué)管理理論應(yīng)滿足的三個(gè)條件:1.理論應(yīng)是可測的;2.所有的理論術(shù)語應(yīng)是可操作性定義的;3.教育管理的行為科學(xué)理論將會(huì)排除倫理化。由此,教育管理理念、制度、關(guān)系和行為被打下深刻的科學(xué)烙印,逐漸形成崇尚客觀、規(guī)范,套用規(guī)則、規(guī)律、方法等思維,并以實(shí)證的數(shù)據(jù)和技術(shù)的支撐來解讀和管理教育,這樣,教育管理就朝著科學(xué)化、規(guī)范化、去倫理化的路子不斷前行。
但它的困境也隨之而來。首當(dāng)其沖的是教育管理制度僵化帶來的疑難。作為科學(xué)世界一個(gè)明證,當(dāng)代教育制度化管理日趨成熟,它把教育看作是一個(gè)嚴(yán)密的、正規(guī)的、封閉的體系,每種制度以一套標(biāo)準(zhǔn),規(guī)范其適用范圍內(nèi)的所有活動(dòng),以杜絕教育管理失范。為此,它總傾向于使制度中所包含的規(guī)則、規(guī)范更為精密,并使制度配套。在教育系統(tǒng)中,各級(jí)各類學(xué)校、社會(huì)教育機(jī)構(gòu)及教育實(shí)體內(nèi)部的教育活動(dòng)、教育過程,都形成一定標(biāo)準(zhǔn),在教育系統(tǒng)、教育實(shí)體與教育過程中,按標(biāo)準(zhǔn)和規(guī)則、規(guī)范操作,并逐級(jí)實(shí)行規(guī)范管理,從而盡可能排除教育系統(tǒng)、教育實(shí)體、教育過程以外的干擾,盡可能排除人為因素干擾,使教育活動(dòng)有序地開展。這個(gè)過程中,制度化管理可以使教育逐步擺脫松散狀態(tài),轉(zhuǎn)化為組織化利益集體,并以一定方式挑選最大利益者進(jìn)入該體系,繼而排斥最少利益者。在美國社會(huì)學(xué)家奧爾森(M·L·Olson,Jr)看來,這種集體的組織行動(dòng)——制度,容易供給他人搭便車的機(jī)會(huì),這種機(jī)會(huì)將導(dǎo)致集體行動(dòng)困境——“奧爾森困境”。當(dāng)他從個(gè)人的利益與理性出發(fā)來解釋個(gè)體利益與集體利益之間的關(guān)系問題時(shí),發(fā)現(xiàn)當(dāng)個(gè)人從自己的私利出發(fā)考慮問題時(shí),往往不是致力于集體的公共利益,因?yàn)閭€(gè)人的理性不會(huì)促進(jìn)集體的公共利益。這樣,個(gè)人所采取的行動(dòng),是在分割社會(huì)資源,起到的是消極作用。這種利益集團(tuán)的分利行為增強(qiáng)了市場壟斷性,使制度的公共性萎縮,最終導(dǎo)致社會(huì)活力喪失和經(jīng)濟(jì)增長緩慢,出現(xiàn)“制度僵化”現(xiàn)象。
制度僵化向來是科學(xué)世界的詬病,教育管理領(lǐng)域也未能幸免,它最終導(dǎo)致教育管理走向等級(jí)化、科層化、集權(quán)化等境地。它造就那些居于不同社會(huì)層次的人有了不同的教育權(quán)利和捕捉教育機(jī)會(huì)的不同能力,使得某些教育只對某些人開放,同時(shí)導(dǎo)致在教育組織中盛行一種照章辦事的形式主義、追求實(shí)效的功利主義和注重專業(yè)技能的精英主義的管理,并使得教育日益集中在權(quán)力中心的控制之下,形成部分人所有的話語體系。
三、人性旁失——教育管理困境的根源
如果說對制度僵化批判,僅是從教育管理組織結(jié)構(gòu)的整體層次上著手,那么,對科學(xué)世界里對事不對人的純理性主義特征的批駁,則將教育管理推向倍遭譴責(zé)的漩渦。
科學(xué)世界中造就的教育管理最大的特征便是對事不對人。在教育管理的事務(wù)中,人們總認(rèn)為有一套管理原則和規(guī)律,適用于其中的任何環(huán)節(jié),包括里面的人。當(dāng)面臨問題時(shí),只需要將這套原則體系搬弄出來,便萬事大吉了。因?yàn)榭茖W(xué)原則體系注重的是事實(shí)與方法,認(rèn)為唯有科學(xué)的方法才能對管理事實(shí)產(chǎn)生可靠的解釋,它不屑也無法言說與價(jià)值和倫理有關(guān)的內(nèi)容。然而生存于其中的人卻是倫理的存在,需要情感價(jià)值來維系。這樣一來,科學(xué)理念建構(gòu)下的教育管理,勢必是一種排除倫理、崇尚方法、技術(shù)的工具理性管理觀:它本質(zhì)上把人當(dāng)作物來看待,它的一切決策不是以具有價(jià)值和倫理意義的正確或錯(cuò)誤來對它進(jìn)行客觀的判斷。因此,在一些學(xué)者看來(哈雷( Haller)和那普(Knapp)),科學(xué)世界下的教育管理,需要研究的不是作為參與管理關(guān)系中的人,而是組織中的關(guān)系,需要重視的僅是組織的關(guān)系和結(jié)構(gòu),人只是組織的附屬品。
20世紀(jì)初期,這種科學(xué)理性的分析和運(yùn)作遭到來自以胡塞爾(E·Husserl)為主的一大批思想家們的激烈批判。胡塞爾說:“在19世紀(jì)后半葉,現(xiàn)代人的整個(gè)世界觀唯一受實(shí)證科學(xué)的支配,并且唯一被科學(xué)所造成的‘繁榮所迷惑,這種唯一性意味著人們以冷漠的態(tài)度避開了對真正的人性具有決定意義的問題。單純注重事實(shí)的科學(xué),造就單純注重事實(shí)的人。”他用“觀念化”(Idealisierung)一詞來解構(gòu)這種困境的起源。在胡塞爾看來,近代科學(xué)給那些關(guān)于生活世界中的事件的原初現(xiàn)象被披上一件觀念的外衣(Ideenkleid),觀念化了的自然開始不知覺地取代了前科學(xué)直觀的自然。這恰恰遮蔽了那些原初現(xiàn)象,以及最初生活世界的自明性。胡塞爾直斥:在最直接顯現(xiàn)的東西沒有得到澄清之前,不得設(shè)定任何間接的東西,這些東西都可以或暫時(shí)標(biāo)上無效的標(biāo)志,并且理應(yīng)懸置起來存而不論,直到通過現(xiàn)象學(xué)還原回到事情本身,回到具體的、豐富多彩的、變動(dòng)不居的生活世界中去。作為科學(xué)哲學(xué)的奠基人物,庫恩也意識(shí)到,傳統(tǒng)的關(guān)于科學(xué)本質(zhì)的進(jìn)步性質(zhì)以及知識(shí)的不斷積累增長的觀點(diǎn),不管怎樣的言之成理,也不能完整說明歷史研究中所呈現(xiàn)出來的實(shí)際情況。
事實(shí)上,科學(xué)世界中最大的困境就在于,對人只強(qiáng)調(diào)人的理性因素而忽視人的非理性因素,在人的理性因素中注重人的認(rèn)知理性而忽視價(jià)值理性。在教育管理中,人與物的關(guān)系、人與人的關(guān)系,完全成了統(tǒng)治與被統(tǒng)治、操縱與被操縱、占有與被占有的關(guān)系。人徹底被外在化、功利化,完全陷入了他者的控制,人自身已被架空懸置。
四、理解與融合——哲學(xué)詮釋學(xué)之于教育管理的可能性
在哲學(xué)詮釋學(xué)看來,上述的困境及其根源,最本質(zhì)的問題在于科學(xué)世界的外衣遮蔽了對教育管理現(xiàn)象作出完滿理解的訴求。因?yàn)檫@個(gè)世界里的教育管理,強(qiáng)調(diào)的是主體之于對象的客觀把握,或是對象之于主體的主觀適應(yīng),割裂了二者的共存性,具有內(nèi)在的局限性,忽略了對人和物的價(jià)值作進(jìn)一步解釋的意義,只享受實(shí)際管理應(yīng)用過程中,因規(guī)則、規(guī)律和方法所帶來的直接高效的快感。所以有必要重構(gòu)對一切教育管理現(xiàn)象的理解,尤其是對管理理念、管理對象、管理行為等要素。
哲學(xué)詮釋學(xué)認(rèn)為,在達(dá)到這種完滿理解之前,至少需闡明三個(gè)概念:視域(Horizont)、前理解(Vorverstandnis)、視域融合(The fusion of horizons)。所謂視域,其本義是指個(gè)體視野范圍內(nèi)的區(qū)域,因而它是一種與主體有關(guān)的能力,是有限的。但因?yàn)樗茈S著主體的運(yùn)動(dòng)隨意地延伸,對于主體來說,它的邊界是永遠(yuǎn)無法達(dá)到的,又可以說是開放無限的。當(dāng)“視域”一詞被作為哲學(xué)概念運(yùn)用時(shí),這兩層含義都被保留了下來并且其意義還得到了擴(kuò)充。哲學(xué)意義上的視域不僅僅與生理和物理的“看”的范圍有關(guān),而且與精神的“觀”的場所有關(guān)。在這個(gè)意義上,感知、想象、感受、直觀、本質(zhì)直觀、判斷等意識(shí)行為都具有自己的“視域”。伽達(dá)默爾就說:“視域就是看視的區(qū)域(Gesichtskreis),這個(gè)區(qū)域囊括和包容了從某個(gè)立足點(diǎn)出發(fā)所能看到的一切。把這運(yùn)用于思維著的意識(shí),我們可以講到視域的狹窄、視域的可能擴(kuò)展以及新視域的開辟,等等。”所謂前理解,就是相對于某種理解以前的理解,或者說,在具體的理解開始之前,我們對要理解的對象有自己的某種觀點(diǎn)、看法或把握,它主要表現(xiàn)為成見或偏見。前理解包括了理解主體一切精神要素的總和,即價(jià)值觀念、知識(shí)經(jīng)驗(yàn)和情感因素等,也就是知、情、意的統(tǒng)一。前理解構(gòu)成了理解者雙方的特殊視域,而實(shí)際管理過程中,總是含有二者依照既定傳統(tǒng)形成的原初視域與面對事實(shí)形成的現(xiàn)今視域,即兩種不同的理解,它們之間必然存在著各種差距,這是任何人都無法消除的。我們對它的處理,就是在這種既包含過去歷史的概念和對它領(lǐng)悟的現(xiàn)實(shí)概念之間產(chǎn)生,這是兩種視域的交融。這個(gè)過程,就是視域融合的過程,也是真正理解出現(xiàn)的過程。
前理解規(guī)定了理解的視域,理解總是不同視域之間的融合過程。通常,我們認(rèn)為成見或偏見是不好的東西,應(yīng)盡量避免。但與科學(xué)管理力圖達(dá)到無偏見的理想化狀況不同的是,哲學(xué)詮釋學(xué)公開承認(rèn)偏見的合理性,并將之作為所有理解活動(dòng)中一種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力量來審視。它認(rèn)為,由前理解表現(xiàn)出來的偏見,并非達(dá)到完滿理解所必須加以克服的障礙,相反它是理解的條件,是理解的一種積極的可能性。伽達(dá)默爾就說:“并非是我們的判斷而是我們的偏見構(gòu)成了我們的存在。”而由于視域是一個(gè)變動(dòng)不居的過程,它開放而不封閉,這就要求我們在實(shí)際的管理過程中必須不斷檢驗(yàn)彼此的偏見,但這種檢驗(yàn)不是對固有模式在理解上的趨同或是改進(jìn),而是講究對固有模式進(jìn)行創(chuàng)造性的“不同理解”。“理解不只是一種復(fù)制的行為,而始終是一種創(chuàng)造性的行為。把理解中存在的這種創(chuàng)造性的環(huán)節(jié)稱之為‘更好理解,這未必是正確的……實(shí)際上,理解并不是更好的理解,不管這種理解是由于有更清楚的概念因而有更完善的知識(shí)這種意思,還是因?yàn)橛幸庾R(shí)性對于創(chuàng)造的無意識(shí)性具有基本優(yōu)越性這個(gè)意思。我們只消說:如果我們一般有所理解,那么我們總是以不同的方式在理解,這就夠了。”
對傳統(tǒng)的教育管理者來說,已有的管理理念和思維奠基于科學(xué)和理性思考之下,它們的意義早已是固定且明白無誤,無需我們重新加以探究。管理的任務(wù)不過只是把這種意義內(nèi)容應(yīng)用于我們當(dāng)前的現(xiàn)實(shí)問題——規(guī)章、制度的照搬和套用是其典型表征。正如我們閱讀字典一樣,不是為了研究意義,而是為了證實(shí)意義,也就是只把這種意義應(yīng)用于當(dāng)前的具體情況,解決現(xiàn)實(shí)的問題,其他的事情都被有意遺忘和忽略。這是典型的排斥偏見的管理理念,哲學(xué)詮釋學(xué)將之稱為“獨(dú)斷型詮釋”。在獨(dú)斷型詮釋里,任何解釋不是真與假的問題,而是好與壞的問題,它是實(shí)踐性的,而不是理論性的,它徹底拋棄了前理解構(gòu)造的特殊視域,忽略了偏見的意義。這種理念方式下的制度或規(guī)則的意義永遠(yuǎn)固定不變和惟一客觀,極易導(dǎo)致對權(quán)威的迷信和制度的盲從,消蝕主體的意義和積極性,滋生個(gè)體惰性和私利之心,長期以往,釀就制度僵化和人性旁失后果。一如伽達(dá)默爾所說:“一個(gè)根本沒有視域的人,就是一個(gè)不能充分登高遠(yuǎn)望的人,從而就是過高估價(jià)近在咫尺的東西的人。”
因此,哲學(xué)詮釋學(xué)意義下的教育管理,不會(huì)偏袒任何一方,它要求我們正式偏見和權(quán)威,承認(rèn)自身知識(shí)的有限性,改變那種有關(guān)教育管理現(xiàn)象的凝固、僵化的傳統(tǒng)觀念,適時(shí)更新原有的組織、領(lǐng)導(dǎo)概念,特別是要看到在行政體制、政治體制改革中人自身的社會(huì)背景、社會(huì)經(jīng)驗(yàn)、社會(huì)閱歷、人生信念、生存期望、發(fā)展需要等情況所具有的巨大推動(dòng)或限制作用。并且需明白,如果要達(dá)到切實(shí)的教育管理,必須試圖對管理現(xiàn)象達(dá)成完滿的理解,必須將教育管理現(xiàn)象看成是一個(gè)個(gè)體間主動(dòng)性的過程,必須意識(shí)到教育管理現(xiàn)象要受到個(gè)體的歷史和現(xiàn)實(shí)處境的影響,是個(gè)體視域不斷改變的存在,也是一個(gè)不斷生成、發(fā)展變動(dòng)的過程。因?yàn)椋瑯?gòu)成和理解教育管理現(xiàn)象的個(gè)體本身就是一個(gè)不斷生成、變化發(fā)展的主題,是一個(gè)在不斷重新構(gòu)造的世界,是一個(gè)在不斷改變著的存在。它擺脫了對話者的主體意識(shí),擺脫了客觀預(yù)設(shè)的規(guī)范、規(guī)則和制度,展現(xiàn)了彼此自身的邏輯。這樣就從根本上為解決當(dāng)代教育管理危機(jī)打下深刻基礎(ch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