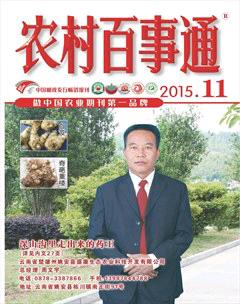村委會收回承包地有“四不能”
當下,一些村委會干部因缺乏依法治村的法律意識或為私利,隨意找個理由剝奪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殊不知法律是公正的,村委會收回承包地至少有“四不能”。
一、不能在過了“除斥期間”時效后解除合同
案例:1984年3月,經村里研究同意上報,胡某獲得了縣人民政府頒發的《自留山使用證》。2005年冬,村委會決定將無償承包使用改為有償承包,并重新與胡某簽訂了承包合同。約定:承包期限30年,一次性交承包費3000元,“不得開荒、建房,否則村委會有權解除合同”。2008年期間,胡某違約開荒。2013年春,新任村書記、主任經提議召開村民代表會議研究通過,決定與胡某解除荒山承包,以示懲戒。
說法:《合同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雖然規定了“當事人可以約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條件。解除合同的條件成就時,解除權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因胡某違約,村委會依約定獲得了合同解除權。但合同法規定的解除權受“除斥期間為一年”的約束,若在此合理期限內未行使解除權,即表明其不愿意解除或放棄解除權。而村委會在胡某違約5年之后主張權利,早已過了“除斥期間為一年”的解除權。
二、不能以未綠化或者綠化不佳收回荒山承包地
案例:遼西某地的劉某一家于2000年秋獲得縣頒發的《荒山使用權證》。證書約定:承包方要按政府要求綠化,若違約不綠化,村委會有權收回荒山。2013年秋,村委會以劉某承包的荒山綠化效果差,構成違約,經村民代表會超過半數同意,村委會將劉某承包的荒山收回,并另行發包給一名村干部的親屬。
說法:《合同法》第九十四條、九十六條規定:當事人一方遲延履行主要債務,經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內仍未履行,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解除合同應當通知對方,合同自通知到達對方時解除。《遼寧省集體林權有關政策解答》規定對“幾年內造林,對不造林、不經營管護、不治理的”限期收回。本案村委會既未催告,也未通知,更未限期栽樹,給劉某一定的挽救期限,若在限定的期限內仍不綠化的,方可收回。村委會、縣鄉政府從未對劉某下達過“限期令”,其擅自單方解除合同的做法不具有法律效力。
三、不能以未換證為由另行發包
案例:呂某獲得所在縣政府頒發的《自留山使用證》上載明:地權公有,林權已有,長期使用,鼓勵綠化。不準開荒、出租和買賣。2005年春,縣、鄉兩級政府集中組織人員對呂某的自留山集中造林。2009年秋,村委會與本村村民何某協商訂立荒山林木轉讓合同,將呂某自留山范圍內的林地林木一并轉讓給何某經營管理。并向呂某解釋說,他的《自留山使用證》根據文件規定早已換發新證,且在換發新證時對幾年不造林的,按文件規定可以收回合同。他持有的《自留山使用證》已經失效作廢。即使沒收回,也不具有法律效力。
說法:《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證管理辦法》(2003年實施)第二十七條規定:本辦法實施以前頒發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證,符合《農村土地承包法》有關規定,并已加蓋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印章的,繼續有效。各省也有相類似的規定。如《遼寧省林權登記換發工作方案》中也明確規定:林業三定時劃給農民的自留山,應予以承認,并登記發證。這次登記發證前,已經調整的自留山,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確認后,予以登記發證。今后自留山不得調整。呂某的《自留山使用證》長期有效,在未被依法撤銷或注銷的情況下,即使未換新證,村委會也無權隨意收回或轉包。
四、不能借口“顯失公平”,主張合同無效
案例:2005年春,佟某與所在的興隆屯村委會簽訂了《荒山承包經營協議書》,約定村委會將村南山老牛嶺西約30畝荒山以每年每畝5元的價格發包給佟某,期限為30年。合同簽訂后佟某當即繳納了兩年的承包費,并開始在山上種植槐樹、棗樹、杏樹等樹苗1萬多棵。到了2013年秋,他種的杏樹、棗樹等收成大好,便出現了“山綠了,農民眼紅了”的不正常現象,一些村民以佟某在承包的荒山上拉鐵絲網阻礙了村民進山之路等理由,紛紛要求村委會解除雙方承包合同。新任村主任也認為承包費過低,顯失公平,向佟某發出中止雙方承包合同通知。
說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七十二條規定:一方當事人利用優勢或者利用對方沒有經驗,致使雙方的權利與義務明顯違反公平、等價有償原則的,可以認定為顯失公平。佟某作為普通村民,在與村委會簽訂承包合同時,根本談不上他“利用優勢”,更談不上利用“村委會沒有經驗”。至于伴隨農產品物價上漲,導致當初承包價格低,屬于商業風險性質,不能視為“顯失公平”情形。據此,佟某可以上述法律規定與村委會說明,若村委會不接受,強行收回佟某的承包地,佟某可通過仲裁或者起訴維權,其訴求應當會得到法律的支持。
(遼寧省錦州市人民檢察院 楊學友 郵編:12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