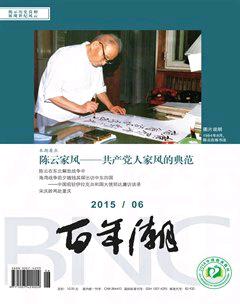中共第一位新聞發言人
喬松都
編者按:龔澎(1914—1970),安徽合肥人。1935年參加一二九運動,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次年畢業于燕京大學歷史系。前外交部部長喬冠華夫人。曾任八路軍總司令部秘書、中共駐重慶代表團秘書、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方面新聞組組長等職。新中國成立后,歷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部長助理。在重慶時,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她成為中共第一位新聞發言人。
1940年9月,我母親龔澎從太行山調往重慶工作。根據南方局領導的安排,我母親被分配到周恩來身邊工作。
我母親在山城有一項必做的工作:每天下午準時來到兩路口附近巴縣中學內的外國記者站,在這里,她將要向來自世界各地的外國記者發布來自中共南方局和解放區的新聞和消息。此時,周恩來已經開始著手培養我們黨自己的新聞發言人了。在他的直接領導下,外事組的同事們以邏輯嚴密、真實可信的發言表達了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人的鮮明立場和觀點。
1941年至1942年間,日軍飛機不停地在重慶上空轟炸,曾家巖50號的部分樓房也被炸壞了,我母親與部分工作人員臨時搬到了紅巖村。為了開展外聯工作,我母親每天冒著酷暑從郊區步行數里,先在化龍橋坐馬車到上清寺,然后再換乘公交車趕往鬧市區。那時,她經常穿一件簡樸而合身的旗袍,隨身的手包里放滿了來自解放區最新的廣播稿副本,她已經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當時南方局可以經常接收到延安的消息和來自抗日前線的戰地新聞,我母親和同事們總是及時將有關內容編寫翻譯成英文,然后編印為若干份材料,并將它們很快分送到外國記者手中。
為了及時將《解放日報》《新華日報》上發表的重要文章和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對局勢的講話翻譯成英文,我母親承擔了大量的筆譯工作,很多重要文章都是她在打印機上翻譯成英文的。我母親要求自己精益求精地譯好每一次談話,校準每一份稿件。后來上級專門抽調了兩位同志負責編譯對外宣傳的英文小冊子。
最初他們出的是油印本,后來改進為鉛印。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重慶已成為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各種力量的聚合地。這里設有40多個國家的外交代表機構,此外還有各種國際性反法西斯組織與10多個中外文化協會。據1943年10月底重慶官方統計,常駐渝的外籍人士達1192人,其中英國人329名、美國人168名、蘇聯人163名,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商業、外交等各個領域。
駐重慶的上百名外國記者來自合眾社、塔斯社、路透社、美聯社、德新社、哈瓦斯社、海通社、國際新聞社、北美聯合通訊社、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等著名國際新聞通訊機構;美國的《時代》《生活》《讀者文摘》《紐約時報》《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紐約先驅論壇報》,英國的《每日郵報》《每日快報》《泰晤士報》,以及《悉尼晨報》《巴黎晚報》《莫斯科世界新聞》等著名報刊在重慶都派駐有記者。
兩路口的記者站實際是國民政府為外國記者辦的新聞招待所。舊址原有的磚樓成為國民黨國際宣傳處的辦公室,操場上建了一批棚屋式簡易房,里面居住著世界各地的新聞工作者,他們來自美、英、法等國各大新聞媒體,左、中、右各派勢力都有。這是一批極為活躍的人群。
記者們以俱樂部的形式聚在一起,每天都要交流最新的戰時消息和發布當日的重要新聞,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把這些信息搶先發到世界各地。按照外國人起床時間比較晚的習慣,他們的新聞活動大都選擇在午后進行。在記者站可以會到各方熟人,還能結識新的朋友,我母親的到來和她所發布的最新消息受到了矚目和歡迎。尤其是她帶來的那些已經翻譯成英文的印刷品,上面登載的內容引起了外國記者的極大興趣。
駐重慶的西方記者每天都在跟國民黨當局的新聞檢查機構展開斗爭,他們對國民黨當局封鎖新聞消息和獨家專政的做法極為不滿,自然更加關注來自反對黨方面的消息與報告。
“宣傳出去,爭取過來”是抗戰期間南方局外事工作的方針。來到山城后,我母親陸續結交了幾乎所有駐重慶的外國記者。無論是美聯社、法新社還是各國大報刊的記者她都認識,與美國新聞處也時有來往。我母親還與在外國新聞機構中的中國雇員廣交朋友,從他們那里得到了許多寶貴的信息。后來有些記者時常主動代我母親傳遞宣傳材料,給她以多方支持。
我母親認為,與西方記者打交道就要了解他們在想什么,是如何看待問題的,要做到隨時準備與他們打交道。當時美聯社的記者是個出名的右翼分子,但我母親并沒有疏遠他,不理他,而是耐心地向他介紹中共的政策和事實真相,后來這個記者發回的稿子盡管態度不怎么友好,可其中的很多內容仍是引自我母親的手筆。
記者站也是許多國民黨特務經常光顧的地方,他們常混雜在其中盯梢和監視進步人士。中統特務更有陰險的一套,他們不但分區搜集情報,還會蓄意制造事端,挑起激化矛盾。每天出入這里隨時都會遭到綁架和不測。
可這些并沒有嚇倒我母親,在朋友和同事們的眼里,她既是一個熱情善良的女記者,又是一個頑強不屈的勇士。我母親大膽機敏地周旋在各國記者中間,不管遇到什么樣的難題,她總會化險為夷,把最新的消息迅速發布出去。“橫下一條心!”“要做事就不要前怕狼后怕虎!”這是她的口頭禪。
我母親臨危不懼、忠誠事業的精神和她從事外交的才智贏得了外國記者的欽佩,他們稱她是消息非常靈通而又富有吸引力的“中共外交發言人”,一些朋友主動幫助她傳送消息。我母親也與許多外國記者和外交官成了朋友,他們也時常在周末去看望她。
哈佛大學終身教授費正清先生潛心研究中國問題幾十年,是西方最具權威的中國問題專家之一。1943年,他以美國國務院文化司對華關系處文官的身份來到重慶。經過美國《時代》雜志記者白修德先生的引見,他見到了我母親。他曾回憶說:
沒幾天后,就有一位聰明的、富有魅力的名叫龔澎的年輕女子來看我。那時,她剛剛走上作為周恩來新聞發言員的輝煌歷程。(1970年她因病早逝時,已是環球新聞界一個出類拔萃的女士了。)
我母親答應定期來訪并輔導費正清學習中文會話。
費正清在日記中記錄了他在1943年10月25日去曾家巖50號拜訪我母親的經歷:
一步一滑地沿街去看望我們那位信奉共產主義的女朋友龔澎。她立即拿出一本政論小冊子,里面共產黨扮演了痛斥國民黨的高貴角色。此書印刷精美,紙張潔白,真是鬼神莫測,他們竟能搞出這么漂亮的小冊子,其中一半已經由她譯成英文。當遞給我這些書時,這位非常令人欽佩的傳教士解釋道,國民黨機關認為她散發了過多的宣傳品,正打算在某一天對她進行綁架,因此,她不能過多地離開這所庇護所。我向她保證,她的追隨者馬上就會訂出一種護送制度……由于史迪威將軍的一位隨從武官來接她去吃午飯,我便離開了這位年輕小姐所在的老鼠橫行的堡壘。
1940年底,中共中央在對美籍記者態度的一份文件中指出,為了加強對外宣傳,提高我們的外交地位,我們應當自動有計劃地供給各種適當的情況材料,以形成“與英美之間一定程度的外交關系”。
為了打開對外宣傳的局面,我母親與各國記者和國際友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她與對方聊天、談家常,從不把自己的觀點強加于人,而是盡量尋求共同點。我母親總是興趣盎然地傾聽別人的談話,并且友好地提出一些忠告,她善于接受每個人的獨特個性,對意見不同者不抱有成見。記者們與她很談得來,也因此愿意接近她。這種氛圍不知不覺地影響著周圍的人們。一位美國記者曾說,他也知道龔澎是為共產黨說話的,但她的話不但說來令人信服,日后也能得到時間的考驗。也有被反動宣傳所蒙蔽的外國記者,常常說些帶有侮辱中國人民的語言,我母親對此極為冷靜,她采用擺事實、講道理的辦法來說服對方。所以外國記者對她都十分敬重、欽佩。
我母親在重慶涉外新聞界中贏得了廣泛的歡迎和信任。許多外國記者不愿意到重慶新聞局那里獲取資料,卻更愿意聽取來自解放區的聲音。國民黨行政院新聞發言人張平群學識淵博,通曉中、英、德幾國文字,與周恩來是南開時期的同學。盡管是政治上的對手,但他很敬重我母親,說龔澎很能干,對待工作一絲不茍,與記者打交道時非常靈活,能夠隨機應變處理問題。
我母親對現實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她認為自己還很膚淺,還有很多沒有讀懂的理論,不能僅僅成為一個宣傳家,因而她經常對自己進行嚴格的剖析。
(摘自《喬冠華與龔澎:我的父親母親(修訂版)》,世界知識出版社2014年版,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