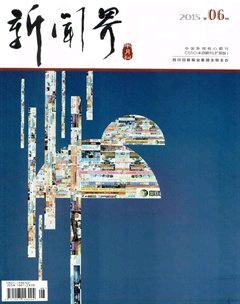災難性事件:對遇難者媒體呈現的反思
李朗++朱鵬
摘要 《新京報》與《南方周末》對上海外灘踩踏事件遇難者杜宜駿的報道,激起了復旦學子與新聞媒體的爭議,也引發了我們對于災難性事件遇難者媒體呈現的反思:為何報道遇難者?對于遇難者,我們應該報道什么?如何報道遇難者?對于這些問題的思考,終將促使媒體理性、克制地報道逝者,促進媒體與遇難者親屬之間的體諒與溝通,使報道獲得遇難者親屬的理解與公眾的認同,并在實踐層面完善并發展災難性事件遇難者的報道。
關鍵詞 災難性事件;遇難者;媒體呈現
中圖分類號G212 文獻標識碼A
一、緣起:復旦學子與新聞媒體對于上海外灘踩踏遇難者杜宜駿報道的爭議
2014年12月31日23時35分,因參加跨年活動的群眾過量聚集,上海市黃埔區外灘陳毅廣場發生擁擠踩踏事件,造成36人死亡,49人受傷的慘痛后果。2015年1月1日,《新京報》與《南方周末》各自刊發了一篇外灘踩踏事件遇難者之一——復旦大學學生杜宜駿的人物特寫。《新京報》以《復旦“才女”外灘踩踏事件中遇難》為標題,文中引用了杜宜駿生前曾在百度貼吧、微博和人人網等社交媒體寫下的內容,力圖展現這位逝者生前的興趣愛好、性格、戀情等;《南方周末》則以《遇難者杜宜駿》為標題,試圖以同去外灘參加跨年活動的杜宜駿的同學、男友的回憶還原踩踏事件的現場情況,文中涉及逝者杜宜駿的年齡、生源地、專業、性格與愛好等。兩篇特寫都采用了杜宜駿男友在踩踏事件發生后在社交媒體上發布的面對杜宜駿生命逝去的悲痛欲絕的文字,網絡媒體“網易新聞”則轉載了《新京報》的報道,并配發了杜宜駿的真實頭像。
正是《新京報》《南方周末》對于踩踏事件中遇難者杜宜駿的人物特寫報道,“網易新聞”對《新京報》報道的轉載,以及杜宜駿生前肖像的發布,引發了杜宜駿生前就讀學校——復旦大學部分學生與新聞媒體之間的激烈爭議:復旦大學官方微博、官方微信發帖呼吁“望媒體尊重逝者隱私,不要再挖掘她的隱私,不要再刊登她的照片,讓逝者安寧”,“復旦易班”微信公共號的帖子《今夜無眠:復旦學生致部分媒體的公開信》則強烈指責媒體大量引用杜宜駿的私人資料甚至其男友發布于社交媒體的話語,質疑其目的“是為了要哀痛一個生命的逝去,還是僅僅為了博得關注度的手段?”微信公共號“微觀者說”則轉發一名廣州媒體人題為《媒體人就外灘踩踏事件致復旦學生公開信:別太矯情了》的文章,認為“個人網上信息不具有隱私性質,有關報道無技術或倫理上的瑕疵”,并指責“復旦學生既沒有證明記者操守有問題,也無權替死者親人做決定”。
復旦學子與傳媒人士就上海踩踏事件中遇難者杜宜駿報道的爭議,引發了我們對于災難性事件遇難者媒介呈現的實踐反思:即為何報道遇難者?對于遇難者,我們應該報道什么而規避什么?
二、為何報道
我們為什么要報道一個災難性事件中的遇難者?即報道這個遇難者的意義何在?
如同斯大林的名言“一千萬人的死亡只是個統計數字!一個人的死亡卻可以寫成悲劇!”和美國著名訃聞記者古姆·尼克爾森所說的“你要記述的不是死亡,而是生命”,對災難性事件中逝去生命的個體關注和報道,所帶來的打動人心的巨大力量,遠遠超越那些以固定口徑、固定模式和固定語言所呈現的冰冷的死亡數據,也更具情感與溫度。此外,對災難性事件中的遇難者進行報道,能夠喚起人們對于其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對逝去生命的哀痛與追思,引發民眾對事件原因和事件責任的深層追問。因而,對災難性事件遇難者的個體進行報道是可行的。
就上海外灘踩踏事件而言,媒體挑選杜宜駿作為重點報道對象,有著新聞價值方面的考慮。根據媒體公布的踩踏事件中36位遇難者名單,逝者平均年齡不到23歲,大多處于花樣年華并多為女性。在眾多逝者中,杜宜駿有著一定的顯著性與代表性:她正處于21歲的青春年華,有著知名度高的名校背景,代表了逝者中的年輕女性學生。并且,她與戀愛中的男友共同到外灘參加跨年活動,由慶祝新年到遭遇不幸,經歷了從大喜到大悲、由生到死的急劇轉折。男友與她在踩踏事件中的經歷,能夠還原踩踏事件的事發現場,符合新聞價值中的接近性與故事性原理。
但是,是否應該采用人物特寫方式,以全部篇幅重點報道逝者杜宜駿?《新京報》與《南方周末》對杜宜駿的報道引發了我們對于災難性報道人物特寫的反思:
(一)是否應當用特寫方式專門報道遇難者范宜駿
作為上海外灘踩踏事件中的遇難者,杜宜駿具有一定新聞價值,有一定的顯著性、代表性,并且具有豐富的故事性,但是否需要人物特寫并采用整個篇幅進行報道還有待商榷。
逝者中還有來自其他行業來上海學習或打拼的外地人,諸如“馬來西亞女留學生”、“在新年將成為新娘的打工女孩”和“第一次到上海出差并在踩踏中遇難的臺灣女孩”,還有其他男性逝者。他們同杜宜駿一樣,鮮活的生命也因踩踏事件而在跨年之夜冰冷逝去。就新聞價值層面而言,他們同樣具有被關注、被報道的新聞價值。然而,他們的“死亡”沒有獲得媒體的足夠關注,杜宜駿則成為更為“理想”的報道對象而被過度關注與過度報道。因而,《新京報》與《南方周末》對杜宜駿的集中報道引發了復旦學子對其報道動機的質疑。
《復旦學生公開信與那個面目模糊的媒體人》一文對《新京報》采用特寫方式報道杜宜駿提出了更強烈的質疑:“《新京報》沒有給出足夠的理由讓讀者信服,給杜宜駿專門撰寫特稿是否對外灘踩踏事件的真相還原和未來預防有所助益?她是踩踏事件的導火索嗎?她是踩踏事件中第一個死亡的受害者嗎?踩踏的悲劇因為她的死亡而停止了嗎?"雖然《南方周末》上刊載的《遇難者杜宜駿》一文試圖通過逝者的經歷還原、再現踩踏事件第一現場的情節,能夠激起人們對于逝者年輕生命消逝的惋惜與哀嘆,產生對于逝者的哀悼之情,但同樣不能說明專門撰寫特寫重點報道杜宜駿對災難性事件的歸因、追責與預防有何更多的啟示價值與更為深層的反思意義。因此,對于遇難者杜宜駿并不是不可以報道,但不應當用人物特寫的形式并集中整個篇幅對其進行報道。
(二)報道遇難者杜宜駿反映了什么主題
拋開遇難者報道作為敏感報道本身所具有的爭議性,就人物特寫寫作而言,《新京報》與《南方周末》對于杜宜駿的寫作非常成功。《新京報》展現了杜宜駿的年齡、外貌、教育、喜好、命運等豐富的故事要素,《南方周末》也完整再現了踩踏事件發生前杜宜駿與男友同去參加跨年活動時的興奮、踩踏事件發生時杜宜駿與男友的遭遇、現場情況以及踩踏事件發生后其男友對杜宜駿生命逝去的傷痛,細節描寫也非常逼真,特別具有故事性和引人同情、痛惜的情感性。
但是,人物特寫的意義在于并非僅僅停留于“非虛構的短故事”,更重要的是能夠在故事之外發掘更為深刻的主題。對于災難性事件遇難者的特寫報道而言,同樣需要通過特定的逝者、災難性事件或折射相關的社會問題,或弘揚其高尚的道德情操,或吸取其經驗與教訓,或對人生的意義與價值進行重新審視……關于逝者的言語、故事、情節都應該緊緊圍繞更深層次的主題展開并反映、揭示其主題。按照這個要求來衡量《新京報》與《南方周末》對于踩踏事件遇難者杜宜駿的報道,除了新聞敘事的成功與表現媒體對年輕生命非正常死亡的悲痛之外,不能夠從逝者個案中提煉出更具有普遍性和更為深刻的主題。
綜上所述,對于災難性事件中的逝者,并非不可以報道。但在報道之前,我們需要對報道主題、報道逝者的意義和報道逝者可能引發的爭議有充分的考慮與權衡,在此基礎上選擇恰當的報道類型與報道篇幅。災難性事件中的人物特寫具有事件特寫與人物特寫的共同特性,既具有故事性的重要性,也具有人物的重要性。因此,在運用人物特寫方式報道某位特定的災難性事件中的遇難者時應該尤其慎重:他(她)是否是災難性事件中的引發人物?是否是災難性事件中的關鍵人物?是否代表了災難性事件中的特定群體?是否決定著災難性事件的發展走向?是否反映了普遍性的社會問題?此外,災難新聞中的遇難者報道并非專門報道人物逝世信息的“訃聞報道”,應以報道“災難性事件”而非“災難性事件中的人物”為中心,集中于個體普通人物的災難性報道容易引發逝者親屬的反感、抗拒與公眾的誤解和批評。
三、報道什么
對于災難性事件中的遇難者,并非完全不可以報道和呈現。但展現與遇難者相關的哪些內容,卻是媒體在采寫時必須反復斟酌與仔細推敲的問題。記者在采訪中收集到的逝者信息,需要小心謹慎地甄選與把關,從而確定逝者的哪些信息可以報道,哪些信息無需報道,哪些領域是報道的禁區而絕對不能觸及,最終,對受眾傳播適宜報道的逝者信息。《新京報》《南方周末》對于逝者杜宜駿的報道之所以受到復旦學子的強烈質疑,其報道內容的不當正是一大重要原因。
就上海外灘踩踏事件而言,《新京報》與《南方周末》對于逝者杜宜駿的報道引發了我們對于災難性事件遇難者報道內容層面的反思:
(一)報道內容不能隨意利用逝者個人隱私
隱私是“個人、群體或組織自己決定其信息在何時、以何種方式、到何種程度傳播給他人的主張”。隨著網絡媒體與社交媒體的興起,隱私的邊界更為模糊、隱私空間被大大壓縮,隱私的內涵也有了變化,從而衍生出網絡隱私、社交媒體(社交網絡)隱私等全新的概念。雖然《新京報》與《南方周末》關于杜宜駿的個人資料與個人信息均來自于她生前主動發布于百度貼吧、微博和人人網等社交媒體上的內容,但這些內容仍然具有隱私性質。因為,個人在社交媒體上的自我披露行為與媒體對個體的信息披露有著巨大的差別;在社交媒體上,個人有能力自主決定其信息在何時、以何種方式和何種程度進行傳播;而在大眾傳媒中,個人則無力對這些因素進行控制。社交媒體上的傳播對象通常局限于親屬、朋友、同學等群體中的小圈子,傳播內容更為隨意化與情緒化,個人信息局限于人際傳播與群體傳播;而大眾傳媒的傳播對象則擴展為普通大眾,傳播內容“去語境化”并通過大眾傳播的形式廣泛擴散。因此,個人主動發布于社交媒體的個人信息仍然具有隱私性質,媒體不能夠隨意加以引用或轉載。
雖然災難式報道會有公布遇難者名字、性別、年齡、死亡原因的傳統做法,以表達媒體與社會對于遇難者的哀悼,并讓公眾牢記災難的無情。但在這些逝者信息之外,有著悲憫情懷的媒體不會再深挖并報道逝者更為詳細的信息。《南方周末》的《遇難者杜宜駿》一文,則在這些信息之外標明了逝者杜宜駿的生源地、教育背景、學習專業等更加細化的身份識別信息,這些信息明顯具有個人隱私的性質,媒體明顯不應報道。《新京報》的《復旦“才女”外灘踩踏事件中遇難》一文,提及“身為復旦大學燕曦漢服協會會長的杜宜駿,鐘愛漢文化,喜愛古詩詞,尤其喜歡紅樓夢”,這些逝者生前相關的身份信息、興趣愛好雖然都由杜宜駿生前在百度貼吧、微博和人人網主頁等社交媒體上主動發布,但仍舊涉及逝者個人隱私。《新京報》與《南方周末》特寫都引用了杜宜駿生前男友在踩踏事件發生后發布在社交媒體上的文字內容,透露出逝者生前具有隱私性質的戀情。雖然國家現行法律、法規對于網絡個人信息在媒體上的使用并未有明文(明確)規定,《新京報》記者也并非采用竊聽死者親友的電話、攻破死者的電子郵箱、人肉搜索死者信息等卑劣而非法的手段獲得相關信息,但這些信息的發布并非逝者親屬及男友主動授權,也未征求逝者親屬及男友的意見和未征得他們的同意,同樣觸及了逝者杜宜駿及其男友的網上隱私。
(二)報道內容應遵循新聞道德與社會倫理
從法律層面而言,媒體公布逝者杜宜駿的個人信息雖然涉及逝者生前隱私,但并沒有侵害其隱私權。因為,隱私權屬于私人生活與人身權利范疇,始于人的出生并終于人的死亡。已經去世的人,生命已經消亡,不能成為隱私權的主體。然而,對于災難性事件遇難者的個人信息進行大量公開報道,并不符合新聞道德與社會倫理。
災難性新聞報道,涉及民眾的知情、對社會的警示、死者的尊嚴與親屬的感受等方面。對于逝者杜宜駿的報道與否,并不影響公眾對于災難性事件的知情,并沒有侵犯民眾的知情權。相反,對于逝者個人信息的大量報道,卻侵犯了死者的尊嚴。因為,逝者杜宜駿并非社會名流、政府官員、影視明星等公眾人物,也非違法人物、犯罪分子或違背社會公德之人,雖然她的生命已經逝去,但她的尊嚴理應得到尊重與維護,她的個人信息不應該被媒體詳盡披露。網絡媒體“網易新聞”為了博得更多的受眾關注度而轉載《新京報》的報道并刊登杜宜駿生前肖像的行為,更是有違新聞職業操守并突破行業底線。
此外,出于對逝者親屬感受的考慮,災難性事件遇難者的新聞報道通常也不會清晰地呈現逝者的詳細個人信息,以免對逝者親屬形成心理與情感上的傷害。而《新京報》與《南方周末》在踩踏事件發生還未滿一天(2015年1月1日)的情況下就發布逝者的詳盡個人信息,顯然有違新聞職業倫理。《新京報》在請求采訪逝者杜宜駿戀人遭到拒絕之后,還在報道中寫下了“《新京報》記者通過私信等多種方式聯系王某,均未得到回復”的話語。這種報道句式一般只出現在批評性報道中,用于災難性事件遇難者的報道,足以見到傳媒對于災難性逝者個人故事挖掘的狂熱和對于災難性事件中逝者及逝者親屬、戀人的冷血,既有違新聞道德,更有違社會倫理。
(三)報道內容具有公共性
《新京報》于2005年就開辟了“逝者”專版,《南方周末》也有大量“訃聞報道”的傳統,積累了相當豐富的對逝者進行報道的經驗,其中不乏眾多優秀的“訃聞報道”;它們的報道對象涉及大量普通民眾,都力求生動、真實、客觀、樸實地講述逝者的生前故事,發掘逝者的精神價值,以緬懷逝者、寄托哀思。《新京報》與《南方周末》對杜宜駿的報道若單從“訃聞報道”寫作的標準衡量,不失為兩篇有生命質感的報道。但是,遇難者杜宜駿,僅僅是踩踏事件中的受害者,不是上海踩踏事件的引發人物、決定踩踏事件發展進程的關鍵人物或應對這起公共安全責任事件負責的管理人物,其個人信息、興趣愛好純屬個人隱私,與公共事務無關,更與公共利益無關。因而,媒體無權也不應肆意挖掘其個人信息,以滿足受眾對死者的好奇心與窺視欲。從這個角度衡量,《新京報》與《南方周末》對逝者杜宜駿的人物特寫報道并不恰當。
災難性事件中的遇難者如果事關公共利益或遇難者的個案具有公共意義、公共價值,媒體則理應報道。1987年12月10日清晨,上海陸家嘴輪渡站發生大規模踩踏事件,共死亡66人。由于悲劇的產生是濃霧,以及人們趕著上班、上學的心理和“職工遲到一次,不但要扣除當月的獎金、引起連鎖反應的是還要扣除季度獎、年度獎的資金制度”所釀成,因此,對于代表遇難者各個群體中的個體進行報道,具有公共意義。《新民晚報》刊發的長篇特稿《陸家嘴輪渡站發生重大傷亡事故》涉及了企業職工、中小學生、職員等群體,以及老人、孕婦與孩子。記者對這些群體中的個體進行了報道,以揭示事故發生的直接原因和背后更為深層的社會原因——住房問題、交通問題與通訊問題,以及當時上海浦東地區與浦西地區地域發展的巨大差異。所以,當災難性事件中的逝者報道具有公共性時,媒體應進行報道。在報道之中,應對逝者信息進行技術性處理,既展現逝者的“死亡”,又不停留于悲情的場景,而是從還原現場、故事呈現升華到反思原因、問責責任和防范應對,從而使個體的逝者死亡展現具有更深層與更廣泛的意義與價值。
四、如何報道
即使為何報道的理由非常充分,報道內容已經經過反復斟酌,假若報道方式不當,災難性事件中的逝者報道仍然易于引發爭議。如何報道、呈現災難性事件中的遇難者,雖然新聞媒體以往沒有明確的標準,但同樣有基本的原則可以遵循,從而使報道獲得逝者親屬的理解與公眾的認可。這些原則可概括為:
(一)最大程度地減少傷害
傳統新聞傳播時代,對于災難性事件的遇難者,有良知的記者與嚴肅的新聞媒體不會立刻采訪逝者親屬,而是選擇“先以遇難者親屬的身份去安撫當事人,而不是以記者的身份,來冷靜甚至冷血地去記錄他們的痛苦狀態”,或“因為怕勾起死難者家屬的傷感”而放棄對逝者親屬的采訪,在不接觸逝者家屬的情況下去還原災難現場與報道新聞。如果有媒體記者直接去逝者親屬那里挖掘新聞,往往被斥為冷血和缺乏人性。隨著新媒體技術的發展與“后新聞傳播時代”的來臨,災難性事件遇難者的報道越來越多。追求獨家新聞的欲望經常驅使記者打破曾經嚴格遵循的規則,即使逝者親屬拒絕采訪,逝者信息也能夠通過網絡媒體合法搜集。雖然有些時候對災難性事件中的遇難者進行報道不可避免,但記者必須尊重逝者相關信息和與逝者有關的采訪對象,并在采訪與報道過程中盡量減少對他們的傷害:
不能為了追求獨家新聞而在逝者親屬還未得知逝者死亡消息或逝者家屬剛得知逝者遇難消息悲痛欲絕的情況下即對其進行采訪;采訪逝者親屬需要征得同意并提前預約,避免不請自來的突擊式采訪對采訪對象心理的沖擊;在采訪時,如果親屬還沒有心理準備接受采訪或不愿意回憶過去、展示悲痛,媒體應先安撫親屬或自覺撤銷采訪;對于采訪對象不愿回答或刻意回避的問題不要窮追不舍,以避免激發采訪對象不安、難過與悲痛的情緒,從而造成第二次傷害;不可深挖逝者和采訪對象的隱私,新聞采寫不可違反法律規定、新聞道德與社會倫理。
(二)以有尊嚴的方式呈現死亡
如何展現災難性事件中的遇難者?雖然各媒體所采用的方式不同,但以有尊嚴的方式展現逝者的死亡,卻是它們應該共同遵守的報道原則。
為了顧及遇難者的尊嚴,媒體不應涉及遇難者過多的個人信息,從而使遇難者成為人們隨意談論與品評的新聞談資。從這個角度看,《新京報》與《南方周末》直接在新聞中大量批露遇難者杜宜駿的個人生活與私人信息,而這些信息與公共事務、公共利益無關,缺乏對逝者的尊敬與尊嚴的維護。
媒體對于死亡的展現通常采用“不展現的展現”策略,即“不用語言細致描摹死亡的可怕和殘忍,但是又要給受眾足夠的暗示和線索,讓他們能充分意識到這是在談論‘死亡”。對于災難性事件中的遇難者,可隱匿能夠直接辨識逝者身份的個人信息,以逝者化名而非真名進行報道;對于遇難者的報道不要集中于遇難者及其親屬的個人生活與私人信息,不應大肆渲染災難發生時的細節與場景,以體現對于逝者尊嚴的尊重和對逝者親人情感的尊重;對于逝者的死亡不渲染,不以煽情性的、夸大性的語言來描寫死亡,不對逝者死亡的慘狀進行細節描繪,不以懸念化、戲劇化與娛樂化的方式展現死亡,而是秉持同情、善意的態度,理性、克制地展現死亡;不直接刊發能夠辨認出遇難者的生前照片或表現遇難者死亡慘狀的照片。通過合法途徑從社交媒體上獲得的遇難者信息,記者在使用前要征得遇難者親屬及相關人物的許可;同時,顧及遇難者及親屬在網上發布信息時的傳播情景與傳播范圍,不可“去語境化”并斷章取義地加以使用,顧及逝者及親屬的尊嚴。
(三)升華遇難者死亡的意義與價值
災難性事件中的遇難者報道并非不可以采用特寫的形式,但關于遇難者的特寫寫作與專門寫逝者的“訃聞報道”有所區別:在報道主題上,前者應注重災難性事件本身,以及與災難性事件相關的監督、批評與問責,遇難者的悲慘遭遇與生前生活以個體故事呈現,但不是報道的重點主題;后者注重于展現逝者本身,以及逝者生前獨特的人生經歷、閃光的人性光輝與高尚的道德情操。在報道模式上,前者以事為主,緊密圍繞災難性事件及災難性事件相關的事實要素進行報道,從遇難者個體故事延伸到反映災難性事件的深層問題;而后者以人為主,緊密圍繞逝者本身的生前故事、功績貢獻與他人評價等進行報道。《新京報》《南方周末》對于遇難者杜宜駿的報道采取了“訃聞報道”的形式,糾纏于個體的悲劇,圍繞她的生前故事與在災難性事件中的不幸經歷與死亡過程進行報道,過度報道了災難性事件中的人。
展現災難性事件遇難者的新聞報道,其目的并非僅僅向我們呈現遇難者個體的悲慘遭遇與悲劇結局,更重要的是通過逝者死亡的展示,在激發我們的悲憫、同情之心之余反思災難性事件本身。因此,在關于災難性逝者的特寫報道中,可借鑒“華爾街日報體”的報道形式,展現逝者的個體故事,讓逝者的生前生活與災難現場形成了前后鮮明的對比,在人們被故事所震撼、因故事而激發悲痛情緒之時,進而進入事件調查、原因分析、監督追責、預防自救、防災體系等更深層的公共主題,讓政府與民眾銘記災難性事件中遇難者所付出的生命代價。遇難者死亡的意義與價值因而得以升華。
五、結語
在對災難性事件遇難者進行報道之前,記者必須反復思考為何報道、報道什么、如何報道等問題。并且,在報道過程中,記者必須設身處地為遇難者及遇難者親屬考慮,對報道行為進行自律,以令人尊敬的報道方式體現對遇難者的深切哀悼和對遇難者親屬的人文關懷,從逝者的特殊性中挖掘其公共性,在自覺、自律與自省中完善并發展災難性事件遇難者的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