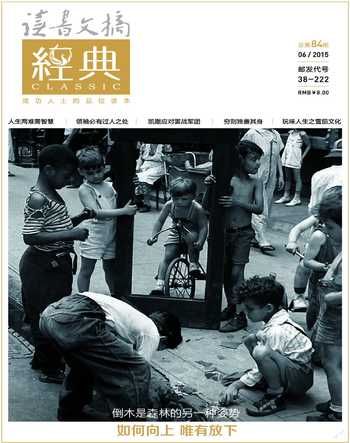“諸葛亮情結”患者
王開林
以“某某圣人在世”自詡的人,通常病得不輕。
經過《三國演義》濃墨重彩的渲染,諸葛亮算度精準,智慧高超,已近乎神,近乎妖,甚至神妖也望塵莫及。諸葛亮高臥南陽時,“自比管仲、樂毅”,沒有誰懷疑他吹牛。他死后,以“今亮”自詡,以“老亮”自居的,不止一個兩個,隨手就可拎起一大串“螃蟹”。劉伯溫自吹法螺,大家確實有幾分相信,但貨色可疑的宋獻策(李自成的軍師)也給自己臉上貼金,就該貽笑大方了。
說到底,“諸葛亮情結”是那些好以謀略驕人傲物的高手共有的心結。可是他們自詡歸自詡,自居歸自居,總還得時人和后人肯承認才行。否則,掉價落入低仿的贗品之列,只會令識貨者嗤之以鼻。
“諸葛亮情結”最嚴重的“患者”非左宗棠莫屬。他有一副對聯廣為流傳,那就是“文章西漢兩司馬,經世南陽一臥龍”,貌似夸贊司馬相如、司馬遷和諸葛亮,骨子里卻滿是洋洋得意的自況。牛皮不是吹的,他執掌戎機三十年,東成西就,罕逢敗績。
咸豐四年(1854),曾國藩率領湘軍克服岳州,左宗棠參贊軍事有功,卻謝絕朝廷的褒獎,這是為何?他在致劉蓉的書信中談到自己的抱負,口氣大得驚人:“……唯(總)督、(巡)撫握一省之權,殊可展布,此又非一蹴而能得者。以藍頂尊武侯而奪其綸巾,以花翎尊武侯而褫其羽扇,既不當武侯之意,而令此武侯為世訕笑,進退均無所可。……若真以藍頂加于綸巾之上者,吾當披發入山,誓不復出矣!”左一個“武侯”,右一個“武侯”,他自居不疑。說白了,他不愿接受知府的職務,是嫌棄官職小,不足以施展他經天緯地的才干;要當官,就得當總督、巡撫那樣的封疆大吏。信中,他自比為武鄉侯諸葛亮,倒是有幾分類似。孔明高臥南陽,羽扇綸巾,縱論天下大勢,不就是要釣一條“鯨魚”嗎?
尚未發跡時,左宗棠自比諸葛亮,難免遭人哂笑;一旦得勢,馬屁精就爭先恐后,投其所好。他擔任陜甘總督時,甘肅學政吳大澂召集士子,采風賦詩,命題為杜甫現成的詩句“諸葛大名垂宇宙”。消息傳到左宗棠耳中,他掀髯大笑。
左宗棠的諸葛亮情結根深蒂固,既有一門心思逢迎拍馬的,也有明里捧場、暗里拆臺的。某日,左宗棠與藩司林壽圖聊天,說起智者料事如神,他自詡能明見萬里之外。林壽圖適時地給他一個甜頭:“此‘諸葛之所以為‘亮也。”左公大樂,兩撇濃眉立刻飛揚。隨后,左宗棠又談到古往今來自比為孔明的人很多,林壽圖給他的卻是一個苦頭:“此‘葛亮之所以為‘諸也。”顛倒一字,譏誚的“餡仁”破皮而出。“諸”字不僅有“多”的意思,而且與“豬”字諧音。林壽圖玩弄文字游戲,話中有刺,綿里藏針,左公頓時氣得臉色漲紅,既難受,又難堪,卻不宜發作。
與其說諸葛亮是神算子,還不如說他是苦長工,給先帝劉備打工多年,他不嫌活兒累,又繼續給那位智商不在服務區的阿斗打工,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但我們稍加梳理,就會發現,諸葛亮的神機妙算——草船借箭、借東風、空城計、死諸葛嚇走生仲達,乃是小說家羅貫中渲染夸張的成分為多,失街亭不算大敗,六出祁山,無功而返,元氣大傷,則是鐵的事實。《三國志》的作者陳壽對諸葛亮的評價是:“……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這就是說,諸葛亮的長處是治國,短板是用兵。
如此看來,左宗棠的諸葛亮情結就有點不倫不類,因為他的長處恰恰是韜略,至于治國的功夫如何,在這方面,由于他沒有機會顯露身手,我們不得而知。
梁啟超研究中國近代史,功力不凡,他格外高看左宗棠,對于左公的諸葛亮情結,他的評論堪稱公允:“說到左宗棠和諸葛亮才華的高下,人們可能還有爭議,但說到對國家的貢獻,諸葛亮就得甘拜下風了。”梁啟超稱贊左宗棠為“五百年來第一偉人”,也就順理成章。
所以說,左宗棠自稱“老亮”,別人以為他給自己加了分,其實是他給諸葛亮掙了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