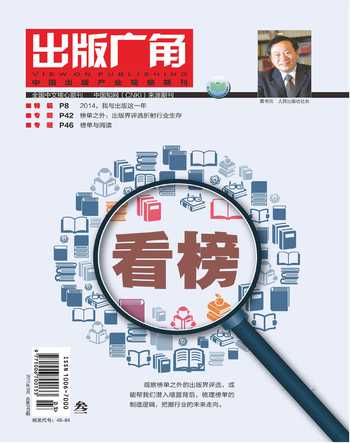榜單之外:出版界評選折射行業生存
楊愛新
歲末年初,行業盤點已成慣例,蔚為大觀。在讀書界,各類好書評選和年度榜單也令人目不暇接。榜單的紅火吸引的多是愛書人,而在榜單之外,出版界評選因聚焦行業熱點,呈現從業者真實的生存實踐,近年來影響力攀升,引發業內外關注。
觀察榜單之外的這些出版界評選,或能幫我們潛入喧囂背后,梳理榜單的制造邏輯,把握行業的未來走向。
一、榜單之外的評選
國內出版界行業評選歷史不長,與國際上一些有數十年、近百年歷史的出版獎評選相比,顯得十分年輕。“中國出版政府獎”是我國新聞出版領域的最高獎,初次評選始于2007年,獎項包括出版物獎和先進出版單位獎、優秀出版人物獎等。這個政府大獎三年評選一次,迄今舉辦了三屆,獲獎作品和獲獎人物、機構都有著鮮明的政府色彩。相比之下,另一重要獎項“中國韜奮出版獎”則行業色彩更濃。該獎由中國出版協會主辦,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主持評選,每三年一次,每次評選出20位獲獎者,定位于表彰和鼓勵對出版事業做出重大貢獻的出版工作者——按照行業內的說法,獲得“中國韜奮出版獎”,就可以稱出版家了。“中國韜奮出版獎”1987年設立,迄今舉辦了12屆。其他重要的國字頭出版行業獎還有:“全國優秀中青年編輯(圖書)獎”(1994年設立,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中國編輯學會主辦)、“全國百佳出版工作者獎”(1996年設立,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主辦)等。
由主管機構或行業協會主辦的上述評選名聲赫赫,政府色彩濃厚,評選標準突出國家意識形態導向和主流價值觀,且獎項設置單一(主要是人物獎和機構獎),評選周期較長(多為三年一次),得獎者范圍和數量有較大限制。或有感于此,一些更富民間色彩、更接地氣的行業評選漸成氣候。它們大都由行業媒體或行業協會組織發起,聘請業內大家擔任評委,綜合運用讀者評選、業內投票與專家評議等多種段,獎項設置也更貼近出版實踐和當下熱點,體現了與“高大上”的政府獎不同的路線與風格。這類行業評選雖然歷史不長,有些評選還不很規范,但因其緊扣行業發展脈搏,精準呈現行業快速變化特征,贏得越來越多的行業內關注和認可。
此外,一些由大眾媒體發起、主要進行圖書評選的年度榜單,也開始將關注視角擴展至圖書背后的制作環節,體現出讀者與書業互動關系的變化,其中以《新京報·讀書周刊》的“年度致敬”較有代表性。本文選取“中國書業年度評選”“全國民營書業評選”“中國好編輯評選”作為樣本,來分析出版業評選折射的行業走勢。具體獎項設置見下表。
二、誰在榜外榜上
“中國書業年度評選”是一個綜合性評選,有中國“出版界奧斯卡”之稱,2004年由《出版人》雜志發起,迄今已舉辦9屆,獎項設置涉及行業鏈條各個方面,體現全行業視角。其中人物獎占據大半江山,計有年度出版人、年度編輯、年度作者、年度民營出版人、年度創新人物、年度閱讀推廣人、年度數字出版人七種,機構獎有三種,為年度出版社、年度分銷商、年度圖書館,另有圖書獎兩種,年度圖書和年度暢銷書(見上表)。從中不難看出,評選整體上傾向表彰行業內領先人物,突出個人貢獻。
最近十年,是中國出版業經歷劇烈變化和震蕩的十年,出版業格局因為市場變化、國際交流、技術革命而發生劇變,從業者也經歷著陣痛和沖擊。業界原有格局被打破,一些曾經聲名顯赫的傳統出版企業,因為不能適應新的形勢變化而迅速萎縮,失去市場和影響力;那些守住陣腳并積極順應變化者和準確把握行業機會的新進入者,反而脫穎而出,贏得發展機會。在劇變的行業格局中,領先人物的影響力常常超越歷史悠久的龐大機構,并以其實踐標示行業的發展方向。因此,業界尤其關注在變革中能夠搶占先機者。“中國書業年度評選”在獎項設置中突出人物獎,正是這種行業心態的反映。
在評選內容大體穩定的框架下,該評選因不同年份行業熱點的轉換而呈現細節上的變化。例如2007年度的評選中首次出現了“年度新媒體”和“年度策劃人”獎項——其時,國內新媒體正蓬勃發展,且迅速展現其對出版業的滲透力。僅僅數年之后,微博、微信公眾號已成為業內普遍使用的營銷手段,該獎項也不再單獨出現。同樣,在2007年,“策劃人”還是出版業內的一個新生事物,在大多數業者還停留在單兵作戰狀態,大多數出版社的產品線還“小、散、亂”,精品多為單品的時候,策劃人的出現打開了行業發展新的窗口,如今回頭看,更是帶動了全行業運營水平的提升,因而得到彼時行業內的高度關注。2010年,數字出版呈現爆發式增長態勢,該評選特別增設了“年度數字出版獎”;針對行業創新層出不窮、創新日益成為出版企業發展新引擎的趨勢,該年度開始設立“年度出版創新人物”和“年度新銳”獎。
可以看出,“中國書業年度評選”及其變化生動記錄的行業發展的軌跡,也成為觀察行業趨勢的重要風向標,同時,其評選結果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動了行業創新和發展。更重要的是,這一評選一開始就形成傳統出版企業與民營出版公司同臺切磋、分享榮譽的格局。在這里,行業景象的呈現是相對完整和及時的,因此得到行業內的重視。
“中國民營書業評選”最初由出版商務周報社與中國書刊發行業協會非國有書業工作委員會共同發起,始于2006年,體現出民營出版方陣的鮮明特點。此評選主打機構獎項,包括年度出版商、年度書店、年度最佳館配商、最佳批發商和最佳服務商,另外,還有營銷獎、閱讀推廣獎、國際交流獎、綠色出版獎等,機構獎多達20余種;相比之下,其人物獎項不多,僅年度出版人、年度人物獎、年度經理獎和年度新人獎4種。
機構獎遠遠多于人物獎,反映出當下出版管理體制下民營出版的生存狀態。盡管近年來民營出版已是重要的行業板塊,且在某些領域——如兒童繪本、青春讀物、大眾暢銷讀物等領域已經處于領先地位,在一些傳統出版企業中,民營板塊亦占據了重要位置,但總體上仍未獲得完全經營權利,因此仍處于相對弱勢地位。在這種情況下,保障機構生存安全、謀求整體實力壯大顯然優先于突出領軍人物,因此其評選更關注機構。
除了表彰各專業出版領域的標桿式企業,民營書業評選設立的“年度營銷獎”獨樹一幟,突顯民營書業對行業發展的整體性思考——書好也怕巷子深,做出版,僅選好書,編好書還不夠,還要會賣書。將營銷概念引入出版業,引領行業潮流,是民營出版公司的重要貢獻,如今已經在全行業蔚然成風氣,亦成為中國出版業轉型和發展的標志性實踐。當然,書業營銷,特別是近一兩年新媒體營銷大行其道,硬幣的另一面也逐漸顯現——文題不符之書屢見不鮮,營銷內容夸大其詞,一定程度上損害了民營書業甚至全行業的聲譽。設置年度營銷獎,一方面可彰顯書業營銷理念,另一方面亦可推動書業營銷健康發展。此外,該獎項還將產業鏈的下游——流通商和書店囊括進來,凸顯民營書業全產業鏈經營意識。民營出版起步于書業流通領域,對該環節,他們有著深刻的認識,也積累了豐富的資源,強調下游經營的重要性,出自其生存經驗,也對全行業有著重要啟示。
民營書業評選獎項設置的變化清晰地勾勒出這一板塊的發展歷程。下表列出的是首屆評選的獎項設置與最近一屆(2014年)評選獎項設置的變化情況。可以看出,2006年評選最初展開的時候,民營書業還未占據出版行業的重要位置,批發企業獎、零售企業獎占據獎項大半,即使在行業人物獎中,也有一半獎項是為行業經理人設置的,例如年度書業經理人、年度書業店長、年度最佳采購等,而涉及出版核心環節的獎項只有選題策劃人、圖書設計等寥寥幾項。但到了2014年,該評選中涉及出版核心環節的獎項比例明顯提高,7大類獎項中,針對個人的書業最佳策劃人獎、創新人物獎以及針對機構的最佳數字出版機構獎、最具潛力機構獎和最具影響力機構獎均涉及出版核心業務。顯然,通過近十年的發展,民營書業已經從行業輔助角色升格為中堅力量,從下游開拓至全產業鏈,從行業邊緣走到舞臺中央,與傳統出版企業比肩并坐,分享市場。
與前兩種評選活動關注行業產業鏈不同,剛剛舉辦了兩屆的“中國好編輯評選”聚焦行業核心環節——編輯活動。該評選強調“以書為證”:凡是策劃或編輯過有內容價值或市場價值圖書的編輯都可以參評——編輯好不好,拿書說話。在行業經歷巨變的當下,這一評選顯得別有深意。
近年來,自媒體、自出版風起云涌,借力網絡技術的突飛猛進,互聯網企業正在以令人瞠目的速度蠶食傳統行業,出版業也未能幸免。亞馬遜甚至宣布:“出版商的倒閉是大勢所趨,出版過程中只有作者和讀者是真正必要的角色。” 國內電商巨頭京東等也紛紛涉足自出版,編輯的職業價值受到空前挑戰。
網絡出版和移動閱讀來勢洶洶,但出版業并沒有如預言那樣迅速沒落。據尼爾森圖書監測公司的統計顯示,在剛剛過去的2014年,全球多個重要市場電子書都出現增長放緩跡象,而紙質書則有不同程度的復蘇。2014年,英國電子書市場占比僅增長了3個百分點至23%,2014年上半年美國電子書銷量占比為23%,而同期精裝本和平裝本圖書市場占比分別為25%和42%。而另一家國際出版顧問公司的報告稱,2014年,中國以187億美元排名全球書業市場第二位;未來5~10年,中國將成為規模最大的圖書市場。
在這個巨大的市場中,編輯是否仍然占據行業主導地位,具有核心價值?2014年百道“中國好編輯評選”從一個側面給出了自己的回答。在不久前舉行的第二屆評選頒獎中我們看到,鄔書林、董秀玉、聶震寧、胡守文、蘇拾平等行業領袖人物和大碗云集,體現出整個行業對編輯這一核心環節的重視與期待。在評選中,鳳凰傳媒集團董事長陳海燕表示,越是“去編輯化”和“去出版人化”的數字閱讀時代,越要強化編輯的核心能力,創造更多高質量的精品,以吸引更廣泛的讀者;商務印書館總經理于殿利更是重提出版人使命:用思想推動社會進步——編輯選取好的內容、有價值的思想,讓這些思想推動中國社會的進步,乃至人類社會的進步。
當然,今日“好編輯”之標準較傳統已經有了很多改變。在評選活動中,業界關注點已經不僅僅是傳統的編輯技術,更關注新的出版形勢下編輯的學習與適應能力,包括策劃、制作、協調甚至營銷等能力。獲獎者大都是身懷多種絕技者,拿出來的自家好書也鮮有單品,不少是知名出版品牌的開創者和運營者,體現當下好編輯新的特質和內涵。
在行業格局經歷震蕩的當下,“中國好編輯評選”發聲重提編輯價值,張揚行業核心理念,雖然僅舉辦了兩屆,卻已收獲一定的行業影響力。
與前三種業內評選相比,《新京報》的“年度致敬”凸顯的是“外部視角”。《新京報》的年度好書評選已進行了十余年,是媒體好書榜單中比較有代表性的一個。有意思的是,在2014年的評選中,除圖書榜外,還增加了針對出版行業的一系列“致敬”獎項。在其致敬名單中,出版人占據8席中的5席,包括年度作者、年度譯者、年度學者、年度編輯、年度出版人;機構獎項占據1席,是年度出版品牌。
《新京報》的“年度致敬”基于讀者立場和市場視角,體現出其對出版業的期待:挖掘好作者、尋找培植優秀譯者、推動優秀學者和編輯走上前臺。讀者或曰讀書市場已經不滿足于你出我讀的被動狀態,他們關注的不僅是書店里的終端產品,而是將視線投向產品背后的“制造商”,開始具備讀書、選書的品牌意識,呼喚更多好作者,更多好譯者,更多特色鮮明的書業品牌。此視角轉換其實反映了讀者市場的成熟。在細分行業領域,在更多窄眾市場上,他們以投票的方式嘗試參與書業運營,要求出版者做得更好。
讀者的成熟勢必推動行業的發展,而此類大眾參與式評選,也會反過來進一步推動讀者市場向縱深發育,帶動更多讀者認識好書,追逐好書,在選擇、閱讀的時候樹立起品牌意識。如同在其他消費領域,基本需求被滿足后必然進入品牌時代,讀者的成熟與圖書市場的成長互動,也將推動其擺脫低層次制作和閱讀狀態,進入由書業品牌驅動的“悅讀”時代。
從這個角度看,《新京報》的致敬類評選僅僅是一個開始,讀者力量的崛起不容小覷。
中國出版業剛剛踏上市場化之路,就遭遇數字出版、網絡化等一系列沖擊,幸抑或不幸?在我們還沒有把傳統出版玩得純熟的時候,就必須一面修煉,一面與數字網絡世界接軌。但中國出版界或許正因此獲得“跨越式”發展的契機。因著互聯網將世界抹平,我們得以與全球出版高端水平迅速靠近,而我們的優勢如此明顯:我們有著開發潛力巨大的閱讀市場,且沒有成熟產業的慣性甚至資本等包袱,這使我們可以輕裝快步成長。
當然,對行業者而言,再美好的前景,仍是一頁一頁書稿累積起來的,再大的市場,也是一本一本書的利潤開拓出來的。對中國出版業而言,榜單十分美好,現實仍舊嚴峻。除了前行,別無選擇。
(作者單位: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