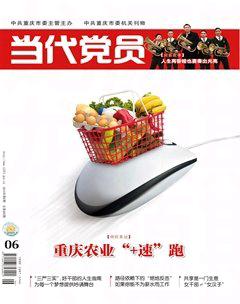農業面源污染治理的開縣之道
韋達韜
“農業已超過工業成為我國最大的污染面源產業。”
2015年4月14日,農業部副部長張桃林的這句話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
農村在逐步告別貧困之同時,農業面源污染正成為一種“幸福的煩惱”。
該如何化解這種“幸福的煩惱”呢?
傳統農業大縣開縣,從2012年開始,打響了“幸福的煩惱”治理之戰。
開縣農工委書記馬新民是釣魚愛好者,休息的時候,喜歡體驗垂釣的快樂。
不過幾年前的一次垂釣經歷,讓他郁悶了很久。
連續幾天,馬新民在一個農村池塘釣魚。
“別吃方便面了,來我家吃熱飯吧。”附近一村民邀請他到家中吃飯。
盛情難卻,馬新民便答應了。
“你這菜很香啊,自家種的吧?”馬新民問。
“對啊,你買也買不到。”有人夸贊,村民很是高興。
“你們不賣么?”馬新民不解。
“我賣的菜用了化肥農藥,留給自己吃的沒有……”話沒說完,這位村民的妻子便狠狠瞪了他一眼。
這位村民意識到自己說漏了嘴,趕緊“剎車”。
“其實,我對農業生產中化肥和農藥過量投入早有耳聞,但以前總覺得離我們生活很遠。”馬新民說。
相較于工業生產過程中造成的點源污染,農業生產過程中產生的面源污染具有隱藏性、長期性和分散性,往往被人們所忽視。
這位村民泄露的“天機”只是農業面源污染的冰山一角——
開縣一項污染源普查顯示,流入當地水體的污染物近75%來自農業生產,其中養殖污染占了總磷總氮的60%。
“作為傳統農業大縣,種植業過度依賴化肥農藥,已嚴重影響了開縣土地的質量安全。”開縣縣委書記李應蘭說。
而身處三峽庫區,開縣養殖業對水體的污染更是牽動人心。
科技之火
——非科學的經管理念和落后的生產方式是造成農業環境面源污染的重要因素,應強化科技支撐,并推進公眾參與。
2012年9月,時任開縣植保植檢站站長雷青山有了一個新稱呼——首席專家。
當年,開縣通過公開遴選,在林業、蔬菜、生豬等14個產業上,評選出該縣農業產業技術體系首席專家。
作為首席專家,雷青山每年可享受縣政府專家津貼0.5萬元,縣財政每年專項安排15萬元左右的科研經費。
“我們接到的任務很明確——改變傳統農業生產方式。”雷青山說。
農業面源污染的重要根源之一就是落后的農業生產方式——農民習慣于過度投放化肥和農藥。
這天,雷青山來到一個村子,正是水稻秧苗移栽大田的日子。
“老鄉,你們來試用一下我們的這個復合藥方,在秧苗移栽后到收割期間,你只需要打兩次農藥。”雷青山喊道。
為了這個復合藥方,雷青山帶領團隊進行了大量試驗。
“我們在金魚缸里放入這種藥,觀察金魚的生命體征。”雷青山說。
要知道,金魚是對環境最敏感的動物之一。
“只有金魚不死,這個方案才算過關。”雷青山說。
雖然雷清山對這個方案很自信,可村民們卻不買賬。
“我以前打五六次藥都不見得能行。”村民們一臉不信。
這個態度在雷青山的意料之中。
“多年來,村民已習慣了加大劑量的施藥方式,一季稻子要打五六次農藥。”雷青山說,“如果是蔬菜的話,就更多了。”
一番勸說下來,沒有幾個村民愿意。
“那這樣,我們簽訂合同,如果出現減產情況,我們負責賠償損失。”雷青山說。
幾個月后,稻田喜獲豐收,這個藥方頓時成了“香餑餑”。
就這樣,14個首席專家團隊在田間地頭開始播種“科技之火”。
斷腕之勇
——農業產業的發展,既要重視生產功能,同時也要確保生態功能,必要時,要以壯士斷腕的精神確保農業生態功能。
漂泊異鄉的張先生一直想回家鄉開縣發展。
“你不如回來開養殖場,掙錢不比你在外地少,還能照顧家里。”2013年春節,朋友為其出主意。
開縣是個養殖大縣,近年來養殖產業風生水起。
張先生的老家位于小江支流附近,很適合搞養殖,這讓張先生動了心。
但一打聽,張先生很郁悶:“縣里為了防止畜禽養殖污染,不再新批養殖場。”
但張先生還是不死心,找到縣畜牧獸醫局咨詢:“我準備采用發酵床技術,保證沒什么污染。”
“你們老家位于禁養區,凡是規模養殖場,都不準新建。”工作人員態度明確。
原來,小江支流屬于一、二級保護區水域,而按照開縣縣政府的規劃,一公里處都屬于禁養區,一律禁止新增規模養殖場。
非但禁止新增,而且以前位于禁養區的規模養殖場都要關閉。
“為此,2014年縣財政補貼了3000多萬元的資金。”馬新民說。
養殖是開縣的支柱產業之一,關閉規模養殖場讓很多人看不懂。
“開縣是貧困縣,財政本就緊張,拿這么多錢去砍支柱產業,不知道怎么想的。”一時間,干部群眾對此議論紛紛。
針對這種言論,李應蘭作出回應:“如果不能把轄區內的水系保護好,就是對開縣人民不負責,也是對整個庫區人民不負責。”
正是基于這種“壯士斷腕”的精神,僅2014年一年,開縣就在禁養區關閉了86家規模養殖場。
2015年,開縣還將繼續拿出超過4000萬元的資金,用以關閉禁養區內的規模養殖場。
制度之手
——農業面源污染長期性的特點,決定了治理上不能求一時之功,需要制度上建立長效機制,久久為功。
2015年3月20日,開縣文峰街道。
街道會議室內,街道領導和各村(社區)負責人齊聚一堂。
“大家一定要認真對待手中的責任書。”街道副主任賀正軍表情嚴肅。
就在剛才,街道與相關村(社區)負責人簽訂了一份責任書——到2019年,農藥、化肥使用量削減30%;畜禽糞便實現全域無害化處理……
賀正軍嚴肅表情的背后,是開縣縣政府出臺《農業生態考核細則》。
在這個《細則》里,農業面源污染治理的幾大工程,都詳細地劃分了年度考核分數——
測土配方施肥工程——0.5分;
綠色防控工程——0.5分;
規模養殖場關閉工程及糞污處理利用工程——1.5分。
…………
“而且‘禁養區新增畜禽規模養殖場的實行一票否決。”雷青山說。
在2014年年度考核中,不少鄉鎮由于工作不到位被扣了分,這讓大家再也不敢怠慢。
“這就像懸在每個鄉鎮負責人頭上的一炳‘達摩克利斯之劍。”雷青山說。
豐樂街道一家柑橘園園主田學美的頭上也懸著一柄“達摩克利斯之劍”。
“現在我基本上不在果園打農藥了。”田學美說。
這源于2014年底開縣出臺的《開縣農產品質量安全聯席會議制度》——明確規定不同類別的鄉鎮每年完成農產品快速檢測任務200、100、50個樣品及以上。
“不小心被抽檢到我的柑橘農藥超標,我的柑橘就不好賣了。”田學美說。
在這個聯系制度中,縣農委、縣畜牧獸醫局和縣食藥監局的監管邊界被厘清,避免了監管盲區及空白。
“這從制度上確保了農業面源污染的治理形成長效機制。”雷青山說。
效益之力
——農業生態不是不要效益,而是要在農業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之間尋找平衡之道,既要生態,也要效益。
2015年4月9日,冒著蒙蒙細雨,李應蘭來到麻柳鄉興坪村核桃基地。
“種植核桃,群眾歡迎嗎?銷路好不好?”李應蘭問。
“投入少,市場風險也小,收益大,劃得來。”興坪村黨支部書記鄧廷章回答。
聞言,李應蘭臉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開縣重要水庫鯉魚塘位于麻柳鄉境內,由于取水方便,當地養殖業一度很火爆。
“雖然養殖業帶來了財富,但卻對環境造成極大破壞。” 麻柳鄉鄉長徐彬說。
在劃為禁養區之后,麻柳鄉果斷關閉了境內所有規模養殖場。
“我們引導養殖大戶往適養區遷移。” 徐彬說。
同時,在首席專家指導下,當地村民依托海拔和土壤優勢打造的1000畝優質核桃基地開始凸顯效益。
“種核桃每畝產值是種莊稼的5—10倍。”徐彬說,“關鍵是還不會造成污染。”
在這條農業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的平衡之道上,開縣正大踏步地前進——
完成配方肥推廣面積30萬畝,增糧243萬公斤,節本增效692萬元;
在推廣示范田內農藥施用平均減少2次、總量減少30%以上;
新建農村戶用沼氣池2000戶,實現“畜—沼—果(糧、菜)”等高效循環農業15萬畝;
2014年,開縣臍橙和錦橙兩個產品獲得農業部認可的有機轉換認證證書。
…………
既治理了污染,又保護了生態,還產生了良好效益——這便是農業面源污染治理的開縣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