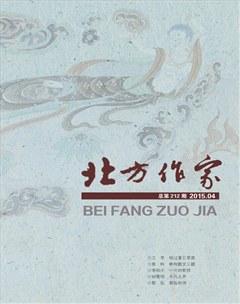吾吉買買提詩歌中的死亡意象
阿卜杜外力·艾薩
摘要:烏魯木齊市文聯主辦的《天爾塔格》雜志是研究維吾爾朦朧詩歌的明亮窗口,從此進來的外來影響和從而挖掘的民族內心沉淀是維吾爾朦朧詩歌創作的內外動力。我在此主要探討研究維吾爾朦朧詩人吾吉買買提詩歌中的死亡意象。
關鍵詞:吾吉買買提;朦朧詩;死亡;意象
當代維吾爾文學作為中國文學必不或缺的一部分,也展現了自己輝煌的發展成績,同時以優秀的現代文學作品迎接了新時期,走向了思想解放和改革創新的新道路。維吾爾朦朧詩歌的獨創新穎,正是新時期維吾爾文學變革的最重要的一個標志。對于以嚴格規范和規則為主的維吾爾傳統詩來說,像朦朧詩這樣,以獨特的形式、深奧的內涵和隱喻的表達為特征的詩歌創作,絕對是絕無僅有的新現象。
1986年,烏魯木齊市文聯主辦的維吾爾文雜志——《天爾塔格》試探性地刊登了朦朧詩歌。維吾爾文學《天爾塔格》雜志是以支持青年、支持新穎文藝思潮為其主要口號。此后三十多以年,維吾爾朦朧詩歌逐漸增多,越來越成熟。可以說《天爾塔格》雜志是研究維吾爾朦朧詩歌的明亮窗口,從此進來的外來影響和從而挖掘的民族內心沉淀是維吾爾朦朧詩歌創作的內外動力。我在此主要探討研究維吾爾朦朧詩人吾吉買買提詩歌中的死亡意象。
一、 死亡意象的基本含義
意象是文學中靈感的產物。意象是詩歌當中組成藝術形象的主要因素之一,大部分詩歌都以意象為審美創作方式。詩人的目的是利用意象,把自己的精神世界表現給讀者。也就是說“意象是詩人精神世界和外部世界的交叉點,是意義和形式的完整結合,是精神化的外部世界與物質化的精神世界的統一。”①意象是一首詩歌最重要的藝術媒介。因此,要享受詩歌的詞句,我們要進入詩人的精神世界,要感知詩人所運用的詩歌的意象。“要找出文學形式和情感的最重要途徑是去發現合適的意象物。換言之,用一系列事物,情景和事件來表達感情;最重要是達到表達內心世界的目的,喚醒內部世界”。②可知,詩人是用意象來給我們表達自己的精神世界。死亡是生命的必然結局,是啟迪詩歌想象的永恒的話題。死亡意象是詩人以對死亡的想象和體會為審美空間創造的手法。
二、 吾吉買買提詩歌中的死亡意象
吾吉買買提·買買提是維吾爾族新世紀詩歌的重要代表詩人之一,在1971年,他出生于新疆和田皮山縣,目前在和田地區長途客運站工作。1990年他在第三期“新玉文藝”上發表了《我的天堂》一詩后,便開始了他的創作生涯。此后,他在各期刊上發表的詩歌作品2000多篇,一些詩歌獲得自治區級文藝獎,其中20多篇詩歌翻譯成漢語并發表。在他的“詩歌中機械和人,城市和自然,人性的本質和倫理之間是一種不可理喻的甜蜜的矛盾。人類城市化過程中的得失,漫無目的恩愛的火焰和沒有愛情的自我破裂作為主要結構因素。”③而且“女人”,“死亡”等意象在他的詩句中的語言應用風格來得以表現。
死亡意象創造的傾向比較多見的吾吉買買提詩歌是我觀察維吾爾朦朧詩歌當中表現的死亡意象的一個觀察點。比較多見的,常用的“死亡”一詞在他的詩歌當中獲得神秘色彩的表現,作為人類對生命結局的神秘思考,在他的詩歌中表現出一種神話意識的意象。
(一) 死亡與孤獨
作為生活在“塔克拉瑪干沙漠周圍綠洲”④的人民的一員,他習慣于“用美妙的語言來安慰自己的內心世界,用一種傾向于大海的干旱心理生存下來”⑤的生命。因而,我們會不知不覺的隨著塔克拉瑪干沙漠的孤獨和詩人的內心孤單進入無際的詩境。在此,我們會想起這么一句話:“人是感悟深刻而孤單的生物,來到世界的孤獨會持續到死亡才能結束。”⑥例如:“我的孤獨是孤獨,比荊棘⑦還孤獨/我的雙唇浸入酒里,卻覺得是誤入/我的悲傷上升到高峰,上升到高峰/沒有情人的消息,我要用死亡來得到拯救。”在維吾爾語言當中荊棘是孤單的象征,是個真正的孤單的標志。但是我們看到,詩人卻在贊揚比荊棘還孤單的自我。但我們還是感受到了美麗的詩境,甜蜜的孤單,純潔的詩人的內心。他為了情人而飲酒,情人雙唇的甜蜜選擇了孤單,走上了為孤單而得到安慰的道路,他的孤獨最后引領到死亡,以死亡而創造審美空間得以實現。他寫到:“別因我在盼望情人的到來,而嘲笑我/我的情人捉弄了我,別為此說我哭喪/行尸從我的眼前走過,眼盈眶里充滿悲傷/我跟著他的棺材,別讓我走到他的跟前/我的內心有個殺手,他會隨時把我殺掉/我是她的一個奴隸,不要說我膽小/主啊,來了,吾吉⑧來了,他是為了燃燒來的/別讓我在地獄的天國里做個無依無靠的孤魂。”他的情人是他的夢想,他在夢想里尋求情人的臉龐、情人的美貌。他想在孤獨的沙漠(塔克拉瑪干)里面哭泣,以眼淚為安慰自己的情欲。他的靈魂也是他的安慰也是他的殺手,他為了靈魂的安慰選擇死亡,因此創造一種又苦澀又傷痛的情歌,內心世界的吶喊。
(二) 死亡為回歸大自然
大自然是文藝創作的刺激來源,永不平淡的文藝體裁。從古至今,不管國內還是國外很多文藝創作家都以獨特的眼光來觀察大自然,從而創造出外在世界和內心空間的契合,給讀者帶來感悟別樣的審美感染力的藝術特色。
從吾吉買買提的很多詩歌中我們可以看到,詩人為了情人返回土壤,用眼睛來贊揚人間的真情,他在情人的腳下融入土壤那刻,才能看到死亡的花朵。死亡滿足他的心靈世界,進而安慰他的苦夢。我們隨著甜蜜的苦夢,走入了詩人折磨自己的道路。在我們眼前浮現的是,跟隨棺架的一群尸體,跟隨這些尸體的是吾吉買買提。這就是他奢望走入的死亡之園,他對死亡的渴望不斷升華,不斷地涌入他的心田。最終對真主的盼望達到高潮。例如他寫到:“我是為了生命,在這條路上遇到悲傷/為了悲傷我在拿筆,對痛苦做了個贊揚/筆下記載的是無邊的沙漠,塵土在荒唐的飄揚/沙漠之中嘴唇苦澀,美人為了美酒上場/美人手里拿著都塔爾,彈著沒有結尾之歌/她的歌聲吸引著著我心,心中涌現著無線的欣賞/情感在不停地死亡,美人注定了我的命運/我是情人,我在孤獨,我在哭訴,我在歌唱。”在這些詩句里,詩人說為了死亡而來世,為了悲傷而愛戀。無邊沙漠之際,詩人看到情人的身影,情人在唱歌的情景。可是,用較強洞察力的眼光來看,我們很容易會發現,詩人不是在看到情人的美貌,他在夢想里創造出情人的形象,也可能是現實的、具體的,也可能是抽象的、夢造出來的。他為了聽到美人的歌聲,選擇走到無極限的道路(死亡的道路;毀滅自己的道路)。從而得到樂意,從而感悟到生命的傷痛和快感。
生命哲學是痛苦的哲學。詩人為了避免生命的痛苦,贊揚悲傷,贊頌為難自己的現實。他在情人手里無邊的沙漠當中渴望戀愛的源泉,渴望跟情人一起拿起都塔爾,唱起木卡姆,情人是他的命運管理,他的命運以情人的歌聲、嘴唇來注定。他在歌唱,在審美的空間里面贊揚著孤單,贊揚著死亡的到來。從而給讀者創造一片深刻的審美空間,聯想動機。
(三) 死亡的審美意義
沒有審美意識的詩歌,不僅不是好的詩歌,而且是失敗的詩歌。雖然他的詩歌是一種非理性的表現,不過他的詩歌還是為我們的審美欣賞創造出一種悲劇之美。當我們讀到詩人在詩歌當中美麗地死去以后,才能感覺到藝術的優美,詩歌的魅力。例如:“我在狂歡,我在設想,我想殺掉我的死亡/生命在狂,花在盛裝,為此歡樂是個夢想/日夜都在想念情人,日夜都行走在這條路上/這是興旺,我要情感都在心中燃燒光/我的陵墓在美人懷里,我也別無所求/她的懷里,她的心里,吾吉要的永恒天堂。”在如此美好的詩句中,我們會意識到詩人的悲痛達到了高潮,因而刺激到我們心靈深處的藝術之美。他在情人黑黝黝的頭發中,眼睛里發出火焰般的光芒,他日夜不停的唱著情歌。他迷醉的身體和靈魂,是我們對詩歌陶醉。
“死亡”首先呈現的是生物學意義。個體生命的死亡,可以看做宇宙有機體能量衰竭或終結的微縮的象征。反過來,個體生命的短暫存在形式又啟發了人類對于宇宙周期命運的擔憂。在這一大一小所形成的張力中間,死亡成了生命存在最美的奧秘,或者說,它是一切生命哲學由此誕生的源點。
當我準備探討“死亡”的時候,影響我思考的另一個重大因素是時間。我想說,時間的本質就是死亡,或者說,時間是由無數個出生和死亡原子構成的直線。在這里,我直接把誕生與死亡畫上了等號,因為它們本來就是一回事。然而奇妙的是,這條直線迅速地被死亡所具有的美學力量所打破,它不再是直線,而成了千回百折的密網;它不再是滑的一根棍子,而是紛亂如麻的一團黑發。只說在死亡的運作時間的枝杈發生了逆轉是不夠的,事實上,時間線上的每一個原子間的縫隙都在發生爆破,并畫出一幅幅生命圖像。
就最直觀的形式看,死亡卻是一種結束,它的宣告是為了給別的生命的存在騰出空間。那些流芳百世的人們,從嚴格意義上講是一種文化,而不是生命。但我們也不能說,一個人死了之后,他的生命證據就立即消失。大多數情況下,他的遺物、他的精神,以及別人關于他的回憶還要留存很久。文學提供了最佳的載體。在文學里,時間是非線性的,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當我們想起作品中某個過去的人物時,我可能想起的是他生命中的任何一個點,這取決于我對他的認識和理解。在此意義上,出生和死亡一樣,隨時都能發生。在這里,形式邏輯完全失效。
三、 結語
總之,詩人吾吉買買提以孤獨、土壤和情人等意象概念將死亡描寫得淋漓盡致,以抒情死亡的方式表達了對人生、世界和生命的意義和含義,這是我們值得思考的一個哲理問題。“在認真地解讀他詩文之時,我們發現除了死亡之外,對死亡的淡然和對幸福的追求滲透在他優美的詩行之中。他詩歌創作體現了所有朦朧詩普遍具有的未確定性、含蓄型和神秘性以及跳躍性等基本特點。”⑨因此,他詩歌內含豐富,意義深奧,如果想要真正地體會和理解他詩歌中的未確定性意義,我們需要從哲學和美學的視野對其加以客觀而科學地觀察和研究。
參考文獻
[1] 艾洛特:《詩歌論文集》,中國國際文化書局,1989年13頁
[2] 吾吉買買提·買買提:《心醉的木卡姆》(詩集),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2月(維文版)序言
[3] 艾塞提·蘇萊曼:《被埋在塔克拉瑪刊的精神》,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維文版)23頁
[4] 同上,58頁
[5] 北京大學哲學系:《西方哲學讀本》,商務印書館,1981年(漢文版),48頁
[6] 孫世軍:《解讀現代詩歌當中的意象》,《深圳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4期
[7] 阿迪力·圖尼亞孜:《圣人之地的夜晚》,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125頁
① 艾洛特:《詩歌論文集》,中國國際文化書局,1989年11頁
② 艾洛特:《詩歌論文集》,中國國際文化書局,1989年13頁
③ 吾吉買買提·買買提:《心醉的木卡姆》(詩集),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2月(維文版)序言
④ 艾塞提·蘇萊曼:《被埋在塔克拉瑪刊的精神》,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維文版)23頁
⑤ 艾塞提·蘇萊曼:《被埋在塔克拉瑪刊的精神》,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維文版)23頁
⑥ 艾塞提·蘇萊曼:《被埋在塔克拉瑪刊的精神》,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維文版)23頁
⑦ 荊棘 —— 維吾爾語里是孤單的、孤獨的象征。
⑧ 格則里 —— 維吾爾文學的一種詩歌創作模式,格則里的最后一段詩人會提起自己的名字或者筆名。
⑨ 阿迪力·圖尼亞孜:《圣人之地的夜晚》,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12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