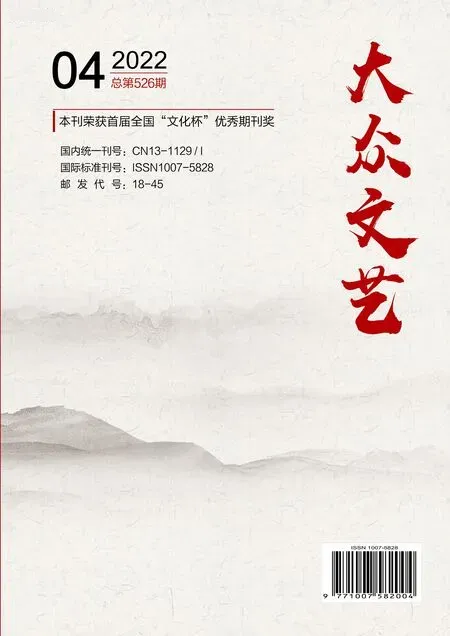論《菉竹山房》中女性的悲劇性命運(yùn)
黃淑菡 (河南大學(xué)文學(xué)院 475000)
論《菉竹山房》中女性的悲劇性命運(yùn)
黃淑菡 (河南大學(xué)文學(xué)院 475000)
本文運(yùn)用文本細(xì)讀的研究方法,對(duì)《菉竹山房》中的二姑姑、蘭花、阿圓這三個(gè)女性形象進(jìn)行分析,探究以節(jié)烈觀為代表的封建倫理綱常制度下,女性命運(yùn)悲劇的根源,并從文本出發(fā)來(lái)探尋小說(shuō)在人物、環(huán)境、意蘊(yùn)三個(gè)層面表現(xiàn)出來(lái)的女性深層悲劇性命運(yùn),表現(xiàn)在封建倫理綱常制度下的女性命運(yùn)的無(wú)奈和困苦,以及在這種倫理制度的重壓下女性命運(yùn)的殘酷和生命的異化。
女性;命運(yùn);生存;意蘊(yùn)
1933年1月發(fā)表在《清華周刊》第38卷12期的《菉竹山房》是吳組緗先生的代表作,這篇作品情節(jié)簡(jiǎn)單、人物不多,但卻短小精悍、字字璣珠,值得我們進(jìn)行多層次的探討研究。小說(shuō)以“我”的敘述視角講述了二姑姑的愛(ài)情故事:二姑姑年輕時(shí)是一個(gè)“人人夸說(shuō)的繡蝴蝶的小姐”,因與其叔叔學(xué)塾中的少年門(mén)生偷偷約會(huì)而被祖母拿住,“一時(shí)連丫頭也要加以鄙夷”。之后,少年在赴考途中船翻身亡,二姑姑就抱著靈牌做了鬼新娘。但故事并沒(méi)有結(jié)束,多年之后,“我”帶著新婚的妻子阿圓去菉竹山房看望二姑姑,在那座陰森的大宅中,二姑姑和丫頭蘭花的種種行為已經(jīng)讓人感到驚慌不安,故事在姑姑“窺房”的行為中戛然而止,給我們留下了無(wú)盡的空白與想象。
一、人物之悲
這篇小說(shuō)從表面上來(lái)看,描寫(xiě)了二姑姑一個(gè)人的愛(ài)情悲劇:人人夸耀的會(huì)繡蝶的小姐與少年門(mén)生相戀而未果,當(dāng)少年門(mén)生死后,失去了愛(ài)人的二姑姑在那個(gè)年代唯一的選擇就是自縊,沒(méi)有死成,只好“麻衣紅繡鞋,抱著靈牌”做了鬼新娘,演繹了一場(chǎng)“人鬼情未了”的愛(ài)情悲劇。然而深入文本,我們看到卻是一個(gè)時(shí)代的女性命運(yùn)悲劇。
“我”和新婚的妻子阿圓去菉竹山房看望二姑姑,那個(gè)曾經(jīng)紅顏的二姑姑變得“陰暗,凄苦,遲鈍”,二姑姑帶我們參觀全宅時(shí),一系列充滿了鬼氣和神秘感的意象,讓這部小說(shuō)進(jìn)入了“聊齋”式的氣氛當(dāng)中,而故事在二姑姑和蘭花“窺房”中結(jié)束時(shí),我們突然間明白,真正的鬼卻是二姑姑和蘭花。無(wú)疑這樣的結(jié)尾是作者經(jīng)過(guò)精心安排的,作為一個(gè)長(zhǎng)輩,這種“窺房”行為顯然是匪夷所思的,然而這卻透露出了二姑姑心中對(duì)正常夫妻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這無(wú)禮的舉動(dòng)表明人的先天需要的滿足是人性中不可能因壓抑而消失的成分,進(jìn)一步反襯出二姑姑命運(yùn)的悲慘,從而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中扼殺生命、扭曲人性的道德至上的價(jià)值觀進(jìn)行形象的批判。”1二姑姑靠著對(duì)“我”和阿圓的窺探來(lái)滿足自己的想象,從而得到一種對(duì)生活的慰藉,正是由于她心中有著對(duì)正常生活的期望,才使得她的種種詭異的行為顯得震撼人心。
伴著二姑姑生活在菉竹山房的蘭花,也是一個(gè)在封建倫理綱常制度重壓下的受害者,但與二姑姑不同的是,蘭花的處境不是被逼的,“她自己說(shuō)不要成家的”。在菉竹山房中生活的這兩個(gè)人,在行為、語(yǔ)言、動(dòng)作等方面表現(xiàn)出了驚人的相似。在打掃邀月廬的時(shí)候,蘭花說(shuō)她也見(jiàn)到姑爹常在院子走,“公子帽,寶藍(lán)衫”,她與二姑姑一起去“偷窺”,這種行為表現(xiàn)出了她的深層心理(想要有正常的夫妻生活)與思想意識(shí)(不要嫁人)的矛盾,這是另一種人生悲劇——蘭花自己囚禁了自己。
在《菉竹山房》中還有一個(gè)位女性形象值得我們注意,即“我”的妻子阿圓,這個(gè)形象的設(shè)置有著特別的意義,可以說(shuō)她是與作品中出現(xiàn)的唯一的男性形象“我”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阿圓是一個(gè)“外鄉(xiāng)生長(zhǎng)的”年輕姑娘,“平日見(jiàn)慣的西式房子,柏油馬路,煙囪,工廠等等”,相較于二姑姑和蘭花,阿圓顯然是生活在正常婚姻中的女性,但她卻是一個(gè)生活在“我”的權(quán)威下的人:阿圓不喜歡大伯娘對(duì)她的種種親昵,然而在“我”的不大在意下就沒(méi)有反抗,她不想去金燕村,卻在“我”編的動(dòng)人故事中變得急于要去,到了菉竹山房之后,阿圓的種種行為動(dòng)作,均是依附著“我”來(lái)完成的,在小說(shuō)中我們幾乎找不到阿圓作為一個(gè)獨(dú)立的個(gè)體而發(fā)出的聲音。
阿圓這個(gè)形象實(shí)際上就代表了現(xiàn)代社會(huì)中,女性命運(yùn)的悲劇,即喪失自我。“女性異化更為深刻的就是她再一次失落了自己,她以男性的異化為異化的標(biāo)準(zhǔn),所以她是雙重的異化。”2在男權(quán)社會(huì)中,女性的幸福實(shí)際上是以喪失獨(dú)立的地位而得到的,一旦脫離了這個(gè)條件,生活給予她們的也就只能是悲劇。
二、環(huán)境之悲
小說(shuō)中的“我”和阿圓是現(xiàn)代社會(huì)的新人,當(dāng)他們以外來(lái)者的身份進(jìn)入到金燕村的時(shí)候,一切都變得不同了。小說(shuō)中最突出的就是它的環(huán)境描寫(xiě),“《菉竹山房》的環(huán)境描寫(xiě)中,滲入了作者強(qiáng)烈的主觀感情色彩,一木一物都被作者蘊(yùn)含了一定的意義。小說(shuō)中,環(huán)境已不是單純的物質(zhì)存在,而變成與人的生存狀態(tài)息息相關(guān)的社會(huì)基礎(chǔ)。”3作品中的金燕村是一個(gè)像原始深林一樣的幽閉的地方,被山巒回環(huán)合抱,兩岸有蔥翠古老而又緊密的槐柳,有被槐柳蔭罩著亂噴白色水沫的響潭,這樣的環(huán)境中一縷陽(yáng)光也照不下來(lái),這里與其說(shuō)是偏遠(yuǎn)幽閉的金燕村,不如說(shuō)是二姑姑凄楚幽冷的內(nèi)心。
走近菉竹山房,首先看到的是疏疏落落的白堊瓦屋,梅花窗上的竹子一半是綠色的,一半已開(kāi)了花,變成槁色。這樣的描寫(xiě)讓我們還沒(méi)有進(jìn)入菉竹山房就有了一個(gè)初步的印象——生命與死亡共存,而這無(wú)疑就象征著即將出場(chǎng)的二姑姑,在命運(yùn)的無(wú)情打壓下,死亡與生機(jī)在矛盾中共生共存。進(jìn)入菉竹山房,屋子高大陰森,板壁上染涂著一層苔塵,甚至連氣味都混合著一種陳腐的霉氣,“每一進(jìn)屋梁上都吊有淡黃色的燕子窩,有的已剝落,只留著痕跡”,這種環(huán)境正和二姑姑給人的印象一樣,“陰暗,凄苦,遲鈍”。而這時(shí)候,幼鳥(niǎo)的叫聲傳來(lái),“有的正孵著雛兒,叫的分外響。”在一片衰敗中新的生命正在孕育,而這正是作者要讓我們看到的,菉竹山房中不可壓制的生命力。
按照這種思維來(lái)看接下來(lái)的敘述,輕易就發(fā)現(xiàn)許多這種怪異和諧之處:在精致的雅房里住著壁虎和蝙蝠,蘭花稱它們是福公公和虎爺爺;新嶄嶄的避月廬中一進(jìn)去就兜了一臉的蜘蛛網(wǎng);屋子里面很整齊,但是卻蒙上了一層薄薄的灰塵;陳設(shè)雖精美,但“西墻上掛著一幅彩色的《鐘馗捉鬼圖》”讓整間屋子鬼氣森森;大廳里,“偌大屋子如一大座古墓,沒(méi)有一絲人聲”,然而廳堂里的燕子卻在啾啾的叫。菉竹山房的環(huán)境在作者刻意描寫(xiě)之下,成為用來(lái)反襯人物內(nèi)心的窗口。
與之相對(duì)應(yīng),生活在這種環(huán)境中的二姑姑,也有著與環(huán)境相吻合的特征:她凄苦陰暗的調(diào)子與她去窺房的行為之間,構(gòu)成了一種另類的生命形式。菉竹山房中的二姑姑是一個(gè)在封建宗法制度壓迫下的悲劇性人物,在她的身上我們看到的是接近于死亡的無(wú)望人生,可是,作者并沒(méi)有在死亡的陰暗氛圍中停筆,而是在一個(gè)風(fēng)雨大作的晚上,為我們呈現(xiàn)出一個(gè)窺房的二姑姑!她在無(wú)望的人生中掙扎,在遇到了一對(duì)新婚男女后,心中不曾熄滅的愛(ài)火又重新燃燒了起來(lái):她正在用別人的生活來(lái)滿足自己的想象,這種在逆境中求生的心理和行為,都在說(shuō)明著二姑姑那顆跳動(dòng)的心在不斷的尋找著新生。
三、意蘊(yùn)之悲
吳組緗先生是一位受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影響很深的作家,他的作品或多或少都有著傳統(tǒng)文化打下的印記,《菉竹山房》作為他的代表作之一,無(wú)疑滲透著中國(guó)古典文學(xué)的因子:其意蘊(yùn)性悲劇的發(fā)現(xiàn)與闡釋。在二姑姑的故事中,其前半段仍延續(xù)了中國(guó)傳統(tǒng)才子佳人小說(shuō)的模式,一個(gè)人人夸說(shuō)的繡蝶小姐與一個(gè)聰明的少年門(mén)生,很自然的就走到了一起,而故事在“祖母因看牡丹花,拿住了一對(duì)倉(cāng)皇失措的系褲帶的頑皮孩子”的時(shí)候出現(xiàn)了轉(zhuǎn)折:少年門(mén)生翻船身亡,繡蝶小姐迎了靈柩,做了新娘,故事的悲劇意蘊(yùn)在此徹底顯現(xiàn)出來(lái)。
一位小姐在未出閣前就有了親密的愛(ài)人,而少年門(mén)生的家人不同意這門(mén)親事原因,應(yīng)該就是因?yàn)檫@位繡蝶的小姐在婚前與人有了私情,盡管這個(gè)對(duì)象就是這個(gè)少年門(mén)生。當(dāng)少年的死訊傳來(lái),這個(gè)曾經(jīng)人人夸說(shuō)的繡蝶小姐除了死亡再也沒(méi)有了出路,可是她就連死的權(quán)力也被剝奪了,最后只能嫁給一個(gè)已死之人。“這嚴(yán)格苛刻的貞潔觀仿佛只為女性設(shè)置,對(duì)男性的所作所為卻無(wú)動(dòng)于衷。少女一心求死,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彌補(bǔ)自己在貞潔上的過(guò)錯(cuò),獲得與少年靈牌結(jié)婚的權(quán)力,從此守節(jié)一生。”4年少的二姑姑就這樣一步步走向了箓竹山房這座大墳?zāi)梗H手葬送了自己的一生。
而這部小說(shuō)真正的悲劇性意蘊(yùn)在于,二姑姑自身對(duì)封建倫理綱常的認(rèn)同感與依附感。在封建倫理綱常制度之下,二姑姑放棄了為自身斗爭(zhēng)的可能性:她本可以為了自己的愛(ài)情而據(jù)理力爭(zhēng),即使這樣的斗爭(zhēng)在當(dāng)時(shí)看起來(lái)似乎蒼白無(wú)力;她也可以在少年死后為自己另謀出路,可是她嫁給了靈牌;甚至,在外面的世界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大變化之后,她可以選擇走出菉竹山房為自己找到新生活,而不是帶著蘭花繼續(xù)躲在菉竹山房里,把自己的人生變得“陰暗,凄苦,遲鈍”。她的種種行為背后,反映出的就是一種普遍異化的心理認(rèn)同,即把自己置于封建倫理綱常制度之下來(lái)約束自己的行為,這就構(gòu)成了那個(gè)時(shí)代女性心理異化的表征。
過(guò)去的很長(zhǎng)一段時(shí)間里封建倫理綱常作為維護(hù)封建統(tǒng)治的工具,在起初的一段時(shí)間內(nèi),它的確發(fā)揮過(guò)一定的積極作用,但之后的大部分歲月中,其充當(dāng)?shù)木褪墙d人的思想、欲望,甚至是生命的鐐銬,有多少像二姑姑,蘭花一樣的人被它斬?cái)嗔松幕盍Γ兂闪艘蛔呢懝?jié)牌坊。文學(xué)悲劇的產(chǎn)生,是為了啟迪后人,讓現(xiàn)實(shí)人生的悲劇不再發(fā)生,它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作于1933年的《菉竹山房》以其深刻的洞察力與現(xiàn)實(shí)的穿透力,迫使我們直面人生的困苦,尋找現(xiàn)實(shí)的出路。
注釋:
1.吳麗芳.《試析〈菉竹山房〉中二姑姑人生悲劇的原因》[J].《嘉應(yīng)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4(10):22.5.
2.荒林,王光明.《兩性對(duì)話——20世紀(jì)中國(guó)女性與文學(xué)》[M],北京:中國(guó)文聯(lián)出版社,2001.6.
3.謝金榮:《試論吳組緗〈菉竹山房〉》[J].《云南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2(5):34.3.
4.陳志浩.《香消玉殞的蝴蝶——〈菉竹山房〉中女性悲劇及其原因探析》[J].《語(yǔ)文學(xué)刊》20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