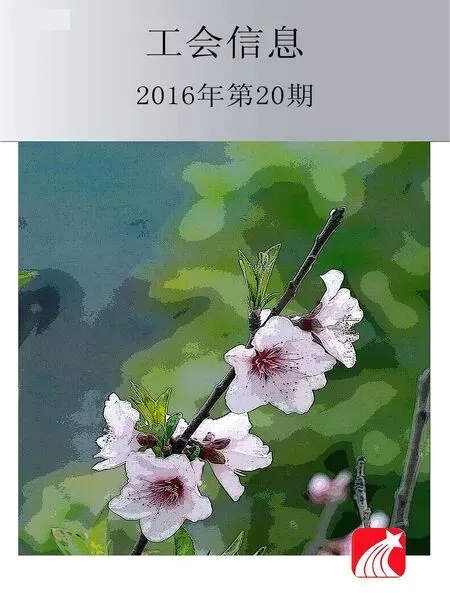金庸的長壽秘笈
文/孫燦金
金庸的長壽秘笈
文/孫燦金

金庸是蜚聲中外的武俠小說大師,他生于1924年,今年是其90華誕。金庸一身江湖俠義之氣,可謂江湖群龍之首。雖已年過九旬,可他仍然精神矍鑠,身板硬朗,到處講學游歷,這與他堅持獨到的長壽秘笈密切相關。
金庸保持了一份順應自然的心態。他說:“我們中國人認為,雖然死不可避免,但生時應該過得好好的,應該去幫助別人,心平氣和的,講究中庸之道。”金庸在創作最輝煌的時刻悄然隱退,還將自己辛苦創辦的《明報》股權出售。對于別人的非議,他進一步指出:“無官一身輕,逍遙自在沒人管是人生一大樂事,過安靜平淡的日子最幸福。”正是這種人生觀指導著金庸,萬事不強求,能有所作為當然好,不能也沒有關系;重要的是尋求內心的閑適,要自己獲得滿足。
曾有人在報上對金庸小說進行了刻薄的嘲諷。對此,人們本以為金庸會大動肝火,在文壇掀起一股“腥風血雨”。可恰恰相反,金庸通過媒體發了一封特別溫和的公開信:“上天待我已經太好了,享受了這么多幸福,偶爾給人罵幾句,命中該有,也不會不開心的。”正是這種豁達、超脫、淡然的心態,讓聲名遠播的金庸,一直沒有被名譽、金錢、地位等世俗之事所勞心費神,而始終保持了身心的協調平衡,使他的身體處于最佳的生理狀態。
品茗綠茶是金庸的養生之道,他對綠茶有一定的研究,他說:“最好的綠茶茶葉是鮮嫩的,清明之前便要采下。飲茶與養生是相通的,茶可以使人怡神健腦,這一功能恰是養生所需要的。”他強調喝茶的分量不要太多,就如他每日的食量亦很少,尤其是淀粉質食品均會“吃少一點”。他寄語城市人:“遇上困難事,愈輕松愈容易應付,愈緊張便愈難應付。”在他看來,這樣的生活就會變得輕松,達到保持健康的目標。
金庸是個極為內向的人,不喜應酬、不善辭令,下圍棋是他最大的興趣,無人對弈時甚至自己和自己下棋。他對圍棋的酷愛,流露在他的武俠小說中,“常有人問起我下圍棋的種種來。就直接的影響和關系而言,下圍棋推理的過程,和創作武俠小說的組織、結構是很密切的。”金庸在黑白棋子攻防征伐的棋局中,尋找心境的平和,鍛煉思維的靈活,客觀上防止了老年癡呆癥的發生。當然,他也喜愛運動,每天都繞圈散步50分鐘左右,散步不是緩緩慢慢,而是快步走,其目的在于出汗。
金庸還專門有一套養生“十二少、十二多”的要訣:“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語、少笑、少愁、少樂、少喜、少怒、少好、少惡。行此十二少, 乃養生之法也。多思則神怠,多念則精散,多欲則智損,多事則形疲,多語則氣促,多笑則肝傷,多愁則心懾,多樂則意溢,多喜則忘錯昏亂,多怒則百腸不定,多好則專迷不治,多惡則焦煎無寧。此十二多不除,喪生之本也。”這些正是他成為長壽者很重要的秘訣。
我們從金庸的長壽養生秘笈中不難看出,養生保健的成功與否,關鍵在于能不能有豁達的心胸。長期保持樂觀的心態,身體上必會得到益處。金庸總結的養生經驗,是值得當代人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