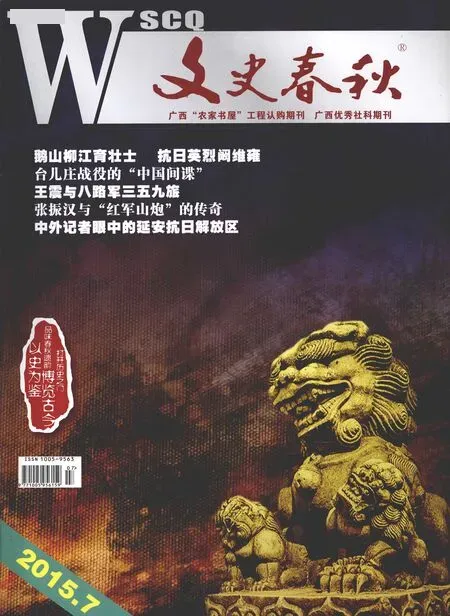彭雪楓將軍的抗戰“三寶”
●徐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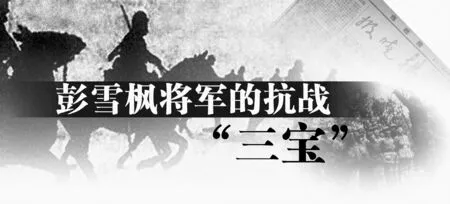
彭雪楓是中共中央軍委確定的33位軍事家之一,抗日戰爭時期他領導抗戰軍民創建了豫皖蘇抗日民主根據地,并且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把新四軍游擊支隊 (即后來的新四軍第四師)不斷發展壯大,成為新四軍的主力部隊之一。在這個過程中,彭雪楓將軍的抗戰“三寶”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當時淮北地區有一首民謠:“彭師長有 ‘三寶’,拂曉劇團、騎兵團還有一張 《拂曉報》。”
鐵馬冰河飛騎兵
新四軍第四師騎兵團是1941年8月1日在淮寶縣(今洪澤縣)岔河鎮成立的。騎兵團成立之前,淮北抗日根據地老百姓深受日偽騎兵的侵擾,特別是到了收糧食的季節,敵人的騎兵總會前來劫掠,新四軍戰士在和敵人騎兵作戰中也是屢屢處于下風。“步利險阻,騎利平地”,淮北平原地形平坦,便于騎兵縱橫沖擊,鑒于這樣的情況,彭雪楓在一次會議上總結戰斗經驗時,第一次提出了“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以騎兵對抗騎兵,這一提議立刻受到了與會同志的一致贊同。
騎兵團成立之初,可謂是困難重重。首先,作為騎兵,馬是最重要的,但是當時根據地的條件很困難,只有個別領導同志為了工作方便才配有坐騎。其次是訓練問題,騎兵相對于步兵來說,對于訓練的要求更高。彭雪楓年輕時在求學期間曾經在內蒙大草原上練過一些馬術,可那畢竟不是戰斗中所要求的騎術。新四軍戰士中只有個別老戰士在長征結束時有過和騎兵交手的經驗,這些對于建立一支正規化的騎兵部隊是遠遠不夠的。這些困難根本難不住彭雪楓,在解決戰馬問題上,他帶頭把跟隨自己多年的“火車頭”送到了騎兵團,并號召配有坐騎的干部把馬捐出來,這樣一來就解決了一部分馬匹的問題。根據地的老百姓聽說了新四軍要組建騎兵團,紛紛把自己家里拉糧食干莊稼活的馬牽到了騎兵團,要求新四軍把馬作為戰馬,好為抗擊日軍出一份力。與此同時,彭雪楓聽說了在新疆受過騎兵訓練的周純麟同志就在第四師駐地附近工作,立刻想辦法把他調到了騎兵團。周純麟是紅四方面軍的同志,當年在西路軍作戰時,跟隨李先念突圍成功到達新疆,當時中共與“新疆王”盛世才關系尚好,周純麟就在盛世才的騎兵部隊里學習騎兵的相關知識。當時的盛世才騎兵部隊有蘇聯騎兵專家指導,因此周純麟學到了不少騎兵作戰理論。
騎兵團從組建之初就立足于建成一支正規化的騎兵部隊,在訓練上,彭雪楓親自給騎兵團的戰士上課,周純麟利用自己以前學習到的騎兵知識和 《騎兵操典》《騎兵教范》的有關內容,組織官兵進行專業訓練。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騎兵團的戰士們的馬術水平有了長足的進步,馬上獨立、蹬里藏身、倒騎馬、偏騎馬等都能熟練掌握,劈刀、馬上射擊、超越障礙等殺敵本領也日益精湛。新四軍首長陳毅、張云逸、譚震林等人看過騎兵團的表演后紛紛表示滿意,新四軍其他兄弟部隊在聽說了騎兵團的訓練成果后,都派所屬的騎兵部隊前來學習經驗。騎兵團形成戰斗力后,曾經多次重創日偽軍。1942年5月,淮北大地正是夏收的繁忙時節,日偽軍為了解決糧食問題,從據點里外出搶糧,騎兵團在泗縣和泗陽縣以北,痛殲了搶糧的日偽軍300多人,給敵人造成了極大震懾,有效地保護了老百姓的夏收。這樣的戰例隨著第四師騎兵團的成長越來越多,騎兵團的威名也在根據地傳開了,敵人對于第四師騎兵團聞風喪膽,不敢再隨便出入據點為非作歹,百姓聽到騎兵團則是喜上眉梢,親切地稱騎兵團為“飛騎兵”。
“部隊之花”盛開豫皖蘇

彭雪楓
“部隊之花”是抗日根據地軍民對拂曉劇團的盛贊。拂曉劇團組建于河南省鹿邑縣,1938年,新四軍游擊支隊正在彭雪楓的帶領下不斷東進,經過鹿邑縣時,當地有幾個十幾歲能唱能跳的中學生要求參軍,于是彭雪楓就因材施用,以這幾個孩子為基礎,組建了一個隨營劇團,命名為“拂曉劇團”。劇團里的演員們歲數很小就離開了家庭,各方面都還需要照顧,彭雪楓就當起了拂曉劇團這個大家庭的家長。生活上,給與小演員無微不至的照顧,經常過問小演員們的生活用品的保障和伙食的供應;學習上,總是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親自給小演員上政治課,幫助他們糾正錯誤的認識,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工作上,劇團很多的劇目彭雪楓都親自參與編排,力爭達到最佳的政治宣傳效果。
古語云:“一張一弛,文武之道。”武的方面第四師官兵英勇善戰,更有騎兵團這支有生力量;那么文的方面,拂曉劇團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劇團每一次演出都對抗戰官兵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拂曉劇團不僅能表演河南墜子、淮北小調、踩高蹺、劃旱船等群眾喜聞樂見的傳統藝術表演形式,更能自編自演京劇和很多話劇。每次劇團演出,部隊官兵和老百姓都特別期待,從演出開始到謝幕,真的是精彩不斷,掌聲不斷。我軍著名將領徐海東有一次經過彭雪楓部隊的駐地,彭雪楓特別囑咐劇團為了歡迎這位著名的將領,趕排了 《徐大將粉碎日寇掃蕩》的京劇。在看完拂曉劇團演出后,徐海東將軍十分感慨,對于在如此艱苦的條件下劇團排出的精彩劇目表示贊嘆,稱贊拂曉劇團這朵“部隊之花”名不虛傳。
拂曉劇團不僅對抗戰軍民起到了很大的鼓舞激勵作用,同時對抗戰友軍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鞏固了抗日統一戰線。一次,東北軍系統的何柱國騎兵軍奉命駐扎在我根據地附近,當時國民黨總體上在執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但是東北軍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對于抗戰的要求比較高,不同于其他國民黨部隊。為了團結抗日統一戰線,彭雪楓就命令拂曉劇團排練了一些反映東北義勇軍抗日題材的節目,到何柱國部某師進行慰問演出。當劇團的小演員們在臺上唱起“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離開了我的家鄉……”這首歌時,臺下的東北軍官兵深受感染,很多戰士都已經泣不成聲。當晚劇團演出了很多抗戰題材的節目,如 《三江好》 《松花江上》 《新編“九·一八”小調》等。當演出結束時,東北軍的官兵紛紛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回老家去!”等口號,演出取得了圓滿成功,從那以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新四軍和東北軍都沒有發生過摩擦,并且能夠并肩戰斗,打擊日本侵略者。
還有一張 《拂曉報》
彭雪楓自幼學習刻苦,文學功底扎實,在長征途中指揮戰斗的閑余,曾寫出過《婁山關前后》這樣受到毛澤東稱贊的文章,在紅軍中有“儒將”的美稱。在擔任紅軍第三軍團第四師政委期間,彭雪楓還主辦過一張油印小報 《猛攻報》,受到了廣大干部戰士的好評,也為后來他主辦《拂曉報》積累了經驗。
《拂曉報》于1938年9月29日創刊于河南確山竹溝,彭雪楓親自為該報提寫報名“拂曉報”,在發刊詞中,彭雪楓寫道:“‘拂曉’代表著朝氣,希望,勇敢,革命,進取,邁進,有為,勝利就要到來的意思。軍人們在拂曉出發,要進攻敵人了。志士們在拂曉奮起,要聞雞起舞了。拂曉催我們斗爭,拂曉迎來了光明。我們的報紙,定名為 ‘拂曉’,是包含著這個嚴肅又偉大的意義的。”在 《拂曉報》創刊后不久,彭雪楓就帶領著新四軍游擊支隊踏上了漫漫征程,《拂曉報》也漸漸的由一張油印小報成長為蜚聲海內外的抗戰報紙,在這個過程中,彭雪楓傾注了大量心血。他對 《拂曉報》的要求非常嚴格,報紙的每一個標題、每一個消息他都親自過目。有一期報紙在一個標題上寫著“這次進軍的任務是打擊消滅漢奸武裝”,彭雪楓認為這個標題很不全面,因為新四軍的首要任務是打擊侵華日軍,對于漢奸武裝,一方面要打擊,一方面也要瓦解、爭取,他要求把這期報紙收回重印。彭雪楓對于一些細節方面的問題要求更加嚴格。有一次,他打電話叫來了一位編輯,上去就問標點符號總共有幾種,你作為編輯用得是否熟練?這位編輯很長時間說不上話來,彭雪楓取出了剛出版的一期報紙,給該編輯指出了上面標點符號的一些錯誤,并語重心長地告訴他:報紙出現差錯影響太大,一個關鍵性的錯別字或標點符號,會使原意改變,就會出大問題。彭雪楓還在工作之余給 《拂曉報》撰寫了大量稿件,特別是每逢重大的事件、活動,他都會親自寫一些文章,如 《抗戰進入相持階段的基本任務和具體工作方針》 《以無產階級戰士的英雄氣概為革命而斗戰到底》《告南陽同鄉書》等,就像黑暗中的一座座燈塔,為根據地的發展和抗戰軍民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拂曉報》開始時只是一張油印小報,后來隨著部隊的東進,報紙的影響越來越大,版面越辦越多,而且開始出現漫畫插圖。報紙圖文并茂,更加受到部隊官兵的歡迎,每一期報紙只要一印出來,官兵們便爭相閱讀,閱讀 《拂曉報》成了第四師官兵戰斗生活的一部分。報紙的發行開始只是限于游擊支隊內部,后來逐漸沖破了根據地的范圍,發行到延安、重慶、西安等城市,國內民眾通過這張小報了解了豫皖蘇抗日軍民的堅持與斗爭,贏得了社會大眾的支持。這樣的一張抗戰小報,引起了著名記者范長江的關注,他主持的“國新社”的記者李洪和任重于1939年和1940年先后來到豫皖蘇根據地采訪。通過“國新社”的宣傳和宋慶齡先生主持的“保衛中國同盟”的支持,《拂曉報》流傳到了新加坡、越南、緬甸等東南亞國家,以及巴黎、倫敦、莫斯科等世界著名城市,還參加了在法國舉行的“萬國新聞報刊博覽會”。
《拂曉報》出版第100期紀念時,毛澤東同志親筆為報紙題詞:“堅持游擊戰爭”,并且給彭雪楓寫來賀信,鼓勵大家繼續努力,把報紙辦得更好。到1943年12月2日,《拂曉報》出版了500期,彭雪楓在座談會上作了 《賀 〈拂曉報〉五百號——五年來之 〈拂曉報〉的檢討》的報告,回顧了報紙一步步發展的過程,他還在自己珍藏的 《拂曉報》合訂本上親題“心血的結晶”,這可謂是他對 《拂曉報》的真情流露。